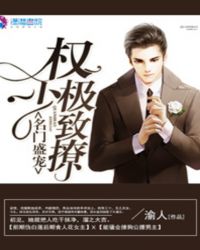§11
如今老秀才的水性相当不错,正打算参加县里的老年人游泳比赛。父亲骂人的根由就是他向我泄露的。老秀才扳着手指才数清,仅他晓得的,我们的父亲在县里工作期间,至少下水替九座水库救过险。老秀才还向我透露一个内幕,“大老板”就因为前些年在另一个县当的“二老板”时,碰巧在河边救了一个因洗手而失足的神秘女人,从此便平步青云。老秀才退休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主要原因是他退休前供职的单位是财政局。我已经回忆起来,在尚未学会游泳的童年时节,有一次我同一帮孩子在一座水塘里光着屁股戏水,从深水区游来一个男人,他远远地瞄着我,在我还不知会发生什么时,一把拖上我游向深水区。我被吓得不知所措,一手抱着这个男人的脖子,一边朝他破口大骂。男人一会儿就被我骂蔫了,乖乖地将我送到水塘边的沙滩上。这个男人就是老秀才。父亲后来听说了此事,他连劝带训地问我,老秀才的水性已经很好了,他让你依靠他,你还怕什么。父亲进一步说,譬如他自己,自从有了组织,他的勇气和能力才变得前所未有的大。
到底是多读了几本书,老秀才的预见更远,退休之前拼老命为自己调了个好单位。
老秀才叹息父亲是好人,好人总也改不了的错误是痴迷不悟。
小时候一到寒假母亲就将我当做她的特务派出去。
刚开始我不大明白,冬天又没有洪水,母亲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还想如果是母亲在心里思念父亲了,那也该自己亲自去。母亲教我说的话是,大姐在家想伯了。实际上这句话我从来没有捎给父亲,有时我将它送给一棵大树,有时又给了一块大石头,这完全看在我出发时与大姐的关系如何。有一次我竟对一头牛说,你好,我大姐想你了。那一次我特别生大姐的气,因为她居然跟在母亲后面指派我,要我告诉父亲,她想要一瓶红药水。父亲所在的水利工地上,红药水紫药水特别多,那是给人搽外伤的,大姐却要用它来涂手指根上的十个小酒窝,还有那偶然被我发现的肚脐眼。我不愿大姐扮得太美,那样我们的父亲就更偏爱她了。
一九九五年春节过后,县里一位要员因经济问题被捕了。要员被关了十个月,才允许探望的人同他见面。结果每个人都在第一时间里认出了他,还实事求是地说,他像从前一样精神。这条消息很是让我悲观了一阵。
一九六五年冬天,我第一次受母亲委派到江家冲水库渠道工地上寻找我们的父亲。父亲像失踪一样四十多天一点音信也没有。三十里只是到达水库的距离,那条渠道还有三十里长。父亲是修筑这条水渠的总指挥。在我到达水渠的起点时,才晓得母亲向我隐瞒了寻找父亲的艰难性。从被我询问的头一个人开始,所有的人都说见过我们的父亲,所有的人又都不晓得他现在哪儿。从中午在水库大坝外见到父亲的那辆自行车开始,我就不断地问刘区长在哪儿,人们总是对我说就在前面。我得不停地躲着沿途一堆堆刚被开挖出来的锋利石头,还要防着那些挥舞铁锤的人不小心将铁锤砸到自己的头上。有时我又得在民工们的哄笑中爬到一处高坡上,喝他们喝剩下的大碗茶解渴。
天近黄昏,终于有一个男人主动放下手中的钢钎,走上来用沙哑的公鸭嗓子问我来干什么。
我依然说,我找刘区长。
男人不高兴地说,别用刘区长来耍威风。
我也生气地说,刘区长是区长,你是什么?
我绕过他继续在乱石中往前走。男人在身后大声叫着我的乳名,问我眼睛是不是有问题,怎么连老子都不认识了。我回过头来努力看了一阵,终于相信这个比民工更像民工的男人的确是我们的父亲。这段亲身经历后来被我写进高二年级的作文。语文老师不相信,他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上朱批,说我内心里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仍没有得到克服,总想美化自己的亲人。我在朱批后面续了一段朱批,说他没有当过区长,不了解区长的生活,就不要乱扣帽子。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老师后来居然谋得一个同父亲当年地位差不多的职务。不过他还算坦白,说这是沾他学生的光。找到父亲的那天傍晚,几个民工替父亲脱下上衣,将碘酒在我们父亲的肩头上搽了三遍,再在上面涂一层厚厚紫药水。最后他们拍了一下父亲的屁股,好了,明天再来帮我们抬石头吧。
我在父亲那里住了一个晚上,我告诉他,母亲在家想他想得很苦。
我们的父亲要我带信回去,说组织上要他在春节之前将这条渠道修好,他必须坚决完成任务。
我们的父亲咧嘴忍受着被磨烂的肩头的疼痛,平静地说,组织让我上工地,我首先是一个民工,要能抡十二磅的大锤,要能抬四个头的石头。
我只有九岁,我假传母亲的话,要父亲用区公所配给他的自行车送我回家。
我们的父亲坚决地表示,不行。
他的理由是,这样的孩子,长大后会像老十一。
这种完全不能算作预言的说法,竟然一语成谶。
将自己与民工混为一谈的说法使我们对父亲大惑不解。
我们的父亲并非真的像母亲说的那样平淡无奇。譬如说,他只读了那么短时间的私塾,却让从大姐到小妹,还有因为婚姻而联系在一起,加起来正好十个的所谓读书人惭愧不已。我们写的字没有哪一个比得上父亲写的字漂亮,如果不是集团作战,单挑的话,也没有哪一个敢说自己比父亲认识的字多。家里别人的经历我不大记得,但父亲在我只有八岁时就逼着我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等一些在我们童年时称为大书的书。父亲还要我在读过之后写上读后感,他对读后感不作评价,但是每篇必看。父亲让我看的最后一本书是《欧阳海之歌》。从那以后他就对我的一切爱好视而不见。父亲在看过我的最后一篇读后感后,终于评说了一句:年轻人就是要像欧阳海那样成长。
如今再来品尝父亲这句话,心里忽然觉得,是不是应该再想想我们的父亲到底是如何成长的,就像我们现在得不断小心,不让自己的孩子吃了添加激素的食物那样。
在我弄清母亲打电话给我的大致背景以后,我曾冲动地打算为此做点什么。不过我还是在平静之后放弃了这样的念头。老十一刘声东挺酸辣地告诫,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就意味着我将被这个时代淘汰了,懂得这个时期的人才不会这么书呆子,哪怕送个小姐去对对方笑一笑,也比那所谓正义实则愚蠢的想法威力强大。
一般来说像父亲这样在区乡干了一辈子的人临近休息时,组织上都会考虑将其调到县城在某个局级单位安排一个让其感到组织温暖的职务。父亲五十六岁那年县里就风传要将他调到县里去,而且说是在县里当个副职。结果却是组织调他去另一个区里当区长。母亲说这下子可了了我们父亲的一宗心愿,全县八区一镇他终于全部工作到了。父亲在家里过完五十六岁生日,一个人先去到任。他走时天上正在落大雨,不过母亲却很放心,现在县里会游泳的人多了,凭什么会轮到一个头发花白的人下水去冒险?
这时候,我们的父亲开始不知不觉地在行为上流露出对母亲和家庭的留恋。这是男人变老态的一种苗头。父亲搭乘县内的公共汽车到达新的任所,立即给母亲来了电话。从母亲脸上温柔的笑容中能判断出,父亲在电话的那一端一定说了些让母亲心满意足的话。所以母亲放下电话后,眼眶比接电话前清亮不少。
母亲说,直到现在我们的父亲才真正将二十几岁的罗甜从心里扔了出去。
母亲的高兴来得太早了,随后一个月,我们的父亲几乎从这个世界里消失了。不过母亲有预感,她心理准备着父亲是去了那个叫柳林畈的村子。母亲没有打电话,那个时期的女人,总是将对丈夫的感情藏得像一潭深不可测的泉水。母亲就在家门前时时注意着那些流落街头的要饭的人,如果不是远道而来的,她就会在施舍之后问他们是哪里的人。刚开始母亲不用费多大的精力就能找出那些从柳林畈来的要饭的人。柳林畈的贫穷太有名了,三个要饭的人里必有一个是这个村的。母亲见到最后一个来自柳林畈的要饭人时,要饭人对她说,自己得回去了,村里来了一个蹲点的刘区长,很厉害。母亲没有再往下问,对她来说晓得父亲的踪影就够了。
大别山区年年夏天都逃不脱暴雨的洗礼,山里的洪水似乎注定了要与我们的父亲过不去。几十年中父亲的级别没变,职务却变个不停。在父亲的眼里,柳林畈面对的那段大河简直就是大别山里的黄河,河床床底的淤沙高出两侧田野近两米,而且几千米长的河堤,都是用头一年垮堤后压在田畈上的沙子堆起来的。我在中学读书时,老师就常将柳林畈的河堤与扶不起来的臭猪肠结合在一起,形容学校里一些不想读书的同学。地理老师在上世界地理课时,也爱结合柳林畈来讲尼罗河三角洲洪水泛滥的利弊。所有人都晓得只要哪一年柳林畈的河堤不垮,那肥沃的田野上,就是插上一根扁担也会开花,结出甜蜜的果实。五十六岁的父亲在组织太久,依照体力的自然法则他干不了太多。就如母亲料定的,河堤假如真的要决口,他跳下去也顶不了多大的用。父亲的体态明显胖了,下到水里别说打桩垒坝,要控制不让洪水冲走恐怕也要别人来帮一把。
柳林畈河堤连续垮了九十九年,但它意欲创下百年纪录的企图硬是被我们的父亲扼杀了。
习惯了肆无忌惮的大洪水第一百次下来时,我们的父亲命令柳林畈的所有成年男人一个不落地集中到河堤上,同时又要所有男人的妻子,就在男人的眼皮底下插秧薅草。夜里男人睡在堤上,女人睡在堤下。县广播站播出的靠不住的天气预报后来总结说,这次的降雨量是百年一遇。那天早上,睡在堤下的女人率先发现沙堤底部出现一股浑水。女人们用自己的美丽身体扑上去,只隔一分钟男人们就赶到了。他们奋力地想尽一切办法来镇压那股浑水。看起来不足为奇的一股小水,用那九十九年破堤成功的气势,毫不客气地当着我们的父亲和三千男女的面,又将河堤撕开一道裂口。习惯了逃难的三千人轰的一声散得比洪水还快。
我们的父亲在这种恐惧中,什么也没有做什么也没有说,似乎听任大家仓皇逃命,曾在高音喇叭里发布命令的威严,也随波逐流而去。
三千人从河堤上一泄而下,跑得最快的已到了一处高坡。
就在这时突然有个女人叫了声——啊,刘区长!
女人手指处,我们的父亲一个人站在河堤的溃口旁,他为自己撑着一把雨伞,背对奔逃的人群,眼望着堤外滔滔的洪水,丝毫不理睬脚下正在崩塌的沙堤,甚至不管那三千人流或急或缓或进或退。我们的父亲独自站在生死的分水线上。他不忘时时调整一下雨伞的迎风角度,不让雨水打湿自己的衬衣。
又有一个女人叫起来。男人们打了一个寒噤。叫的女人越来越多。男人像疯了一样,他们返回河堤的速度比逃离时更快。我们的父亲仍然没有理睬他们。在他的嘴角上还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些轻蔑。柳林畈的男人们看出了他的心思,他们比豹子还凶,大声吼叫着不顾一切地抱成团跳进洪水中。柳林畈的女人从此比十里八乡中所有的女人都幸福,因为在转眼之间她们就拥有了许多个真正的男人。男人们用身躯阻隔了那些从沙堤缺口中奔腾而下的洪水,他们也同样在今后一直为有如此美丽的许多个女人而得意自豪。在用完所有救险的材料之后,女人们脱下自己的裤子做成沙包,扔给继续泡在洪水中的男人,垒在从此与崩溃绝缘的河堤上。
沙堤上的缺口被堵住,我们的父亲那紧闭的嘴中哗啦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
我们的父亲只同老秀才说过,那口血硬是急火攻心憋出来的。父亲内心里比所有人都怕,万一逃走的人不回来,我死了还好说,可身后还有一大家子要活命哩。所以父亲常说,不是他救了柳林畈,而是柳林畈的人救了他和他的全家。
堤没垮,柳林畈的庄稼顺利地由绿转黄。
一个从播种到丰收的完整季节又一次被我们父亲奉献给他的组织和他的人民。
春天来时,组织上派他到北京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
我们的父亲终于有幸在最近的距离内亲眼目睹,声名显赫的红旗轿车。同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一样,我们的父亲一见到红旗轿车就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浑身颤抖,思想麻木地扑过去,双手同时指向镶在车头上的那只比在风中飘扬的红旗更有魅力的车标。父亲的双手伸成出所未有的长度,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最终都没有够上那只一尺来长的红旗车标。到头来离红旗车标最近的反而是父亲壮实的脊背。这种形容是在尊重父亲的习惯。实事求是地说,还有比脊背更接近红旗车标的地方。譬如屁股。只是这样说起来,是不是带有某种刺激和某种伤害呢?
对于发生在北京的一切,我们的父亲都会像做文章,能雅致的坚决雅致,能温良恭俭让的一定会温良恭俭让。父亲一辈子极少独自伫立,柳林畈河堤溃口时有过一次,在北京时又有过一次。就在他扑向红旗轿车时,一个身材高大,看上去就晓得营养远远超过父亲的男人,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伸出手掌往父亲肩膀上一拍,分明没有怎用力,那只与民工对手抬过石头的肩膀便塌了,整个身子也转了向,由面对红旗轿车改为背对红旗轿车。男人若无其事地指向一扇大门说,会场在那儿。我们的父亲下意识地嗯了一声,顺着路走了几步后,突然回过头来,望着红旗轿车发了老大一阵子呆。上午的会即将结束时,那只被拍过的肩脖深处出现一种莫名的酸痛。父亲去大会的医务室里要药,医生在他肩上检查出一只红彤彤的掌印。父亲说了早饭后的事,医生宽慰说,有两点可以保证这伤没有触到筋骨,第一是父亲肩上有一层厚厚的老茧,第二是父亲胸前挂着一块鲜红的大会出席证。
事隔多年,世事虽然如白云苍狗,我们的父亲已经会往别的方面想了,他明白那些有能力看守红旗轿车的人,也就是如今的武打片里讲述的那种大内高手。然而,我们的父亲绝没想到,大别山里一个普通的县份,也能拥有红旗轿车作为公务车。他也无法想象,当今的老十一居然根本就不将神圣的红旗轿车放在眼里。
因为与众不同,在北京开会的人都能看上内部电影。那天晚上,我们的父亲捂着自己的肩头,突如其来地从人群中站起来,指着银幕大声叫道,雪弗莱!雪弗莱!正在放映的是一部外国电影,父亲只叫了两声,第三声雪弗莱变成一片湿润,悄悄地弥漫在他的眼角上。 刘醒龙中短篇小说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