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易中天谈美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CHAPTER 03
中国美学史的内在逻辑与历史环节
如果我们承认,所谓历史,虽然不是根据某种先验理性原则,像大本钟那样准时准点地按照事先定好的节目单上演的活剧,但也不是毫无规律的偶然事件的杂货摊,那么,我们就无法否认,无论是以历代王朝的更替为线索来书写中国美学史,抑或是像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出生、活着和死亡一样,把中国美学史分为“发端”、“展开”和“总结”三阶段 ,都是非逻辑、非历史和非美学的分期法。因为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中国美学自身运动的内在原因和逻辑线索,看不到每一阶段作为历史环节必然产生的根据,也看不到后一环节对前一环节的否定和扬弃,因此也就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和理论上的价值。事实上,中国美学史的分期,决不是学究式的经院哲学问题;它的意义,也决不仅仅只是为中国美学史的撰写提供划分章节的便利。正如我们将要证明的,它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界定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评价,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实质上要回答的,乃是中国美学的本质特征和内在逻辑。
毫无疑问,作为现代形态和独立学科的中国美学,即中国的Aesthetica,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的产物。由于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等先驱者对西方美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美学的固有模式,使它不再停留在经验总结和直观描述的水平而上升为理论思维。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以鲁迅为代表的一大群有志之士的筚路蓝缕,使作为独立学科的中国现代美学,几乎一开始就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指导下,踏上了通往真理的坦途。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也应该把鸦片战争之前的漫长岁月界定为中国美学史的史前期。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我们民族审美意识的萌芽时期,即追溯到那没有文字可供稽考、遥远得无法回忆的时代。但是,美学史毕竟不等于审美意识史。也就是说,它只能是人类对自己的艺术和审美活动进行理性规范,即不断探索、研究和界定美和艺术本质的思想史。这一历史,在西方,开始于古希腊,开始于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一大批理性主义哲学家。它的特点,是以美的本质为主要课题,不断地试图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用不同答案来回答“美是什么”这个司芬克斯之谜,而自从柏拉图明确提出这一问题后,它就一直困惑着西方无数睿智的头脑和聪慧的心灵。在中国,这一历史则开始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下面将要讲到的原因,中国古代的先哲圣贤们更加关注的,并非美的本质,而是艺术的本质,尤其是艺术的社会功能。看来,起步于人类历史同一时期(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的“轴心时代”)、产生于我们星球同一纬度(即北纬30°至40°)的中西美学,恰恰正好分别从两个不同的方向照亮了人类美学思想的漫长历程。也许,只有当这两道光芒融为一体时,美的世界才会普照着理性的太阳。
因此,如果说,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前的西方古典美学,可以划分为古希腊罗马客观美学、中世纪神学美学和近代人文美学三阶段的话,那么,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古代美学,则可以划分为封建前期艺术社会学、封建中期艺术哲学和封建后期艺术心理学三时期。 本文将要论述的,便正是这三个历史环节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封建前期艺术社会学
王国维说过:“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的确,在中国古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周革殷命”,决不只是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或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而是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一种文化战胜另一种文化,即“隐蔽地存在于家庭之中的奴隶制”,被直接从原始氏族公社过渡而来的封建领主制所取代。与夏族、商族大约同时发祥的周族,由于世代重农,逐渐兴旺,终于一如东方斯拉夫民族,在原始公社解体之后,没有经过奴隶制阶段,便直接产生了封建制度,并以“三分天下有其二”(孔子语)即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通过武装斗争而一举夺得天下,揭开了中国三千年封建社会史的帷幕。其在文化上的意义,则正如《礼记·表记》所说,是一种早熟的封建文化——“尊礼文化”,逐渐取代了包括氏族社会“尊命文化”(夏)和奴隶社会“尊神文化”(商)在内的原始宗教“巫术文化”。人作为一个群体,从远古文化的神秘性和压抑性中解放出来,终于建立起一个以群体的人为核心、现实精神颇强、伦理色彩极浓的文化系统——礼乐文化,而中国封建文化也就开始了它从早熟走向成熟的历程。
中国古代美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作为中国古代美学的始端,儒、道、法、墨诸家美学,无不是在春秋战国之际“礼坏乐崩”、早熟的封建领主制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的历史条件下,对“礼乐文化”进行反思的产物。也就是说,正是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思考、并仅仅只是为着这种思考,他们才附带地对美和艺术的本质,尤其是对艺术的社会功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们的美学思想,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是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的。
孔子是礼乐文化最坚定的维护者。在他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也只能是按照宗法秩序有差等地结构起来的和谐群体。这种社会秩序的心理根据,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这一生理基础之上的伦理情感——仁爱之心。当社会的每一成员,都从“亲亲”之爱出发,将这种伦理情感辐射到全社会,以至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则“勿施于人”时,便“天下归仁焉”。因此,无论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伦理),还是维系群体和谐的“乐”(艺术),对于一个理想而健全的社会而言,便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诗(艺术)“可以兴”,即可以感发每个人“泛爱众而亲仁”的向善之意;“可以观”,即可以考鉴社会政治的得失;“可以怨”,即可以干预生活、调整政策、实现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诗“可以群”,即通过艺术媒介来传达交流情感,使每个个体都体验到群体和谐的审美愉快,更自觉地维护宗法政治秩序。由于“为仁之方”在于“克己复礼”,因此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前提的个人道德修养,也必须通过艺术和审美来实现,即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唯其如此,孔子才高度肯定艺术的社会价值,并把它的本质归结为政治教化和道德修养的工具。
与之相反,墨家和法家则是艺术的否定论者和美学的取消主义者。在前者看来,艺术和审美都是一种无益于社会改良和物质生产的奢侈品,而后者则更激进地把它们看作一种有害于邦国的坏东西。以发明“矛盾”一词而举世闻名的韩非认为,任何事物的内容与形式,正如矛与盾一样,是冰炭不可同器,水火不能相容的。当一个社会必须以艺术为自己的审美形式时,这个社会的本质也就一定是罪恶的和腐朽的了。因此,艺术即便不是对腐败政治的有意粉饰和对险恶人心的有意遮掩,也至少是它们的必然产物。相反,“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如果一个社会在本质上是美好的,那么,又何劳艺术呢?
在这一点上,道家美学也有相似的看法。道家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与乐、道德与艺术,都是“失道”即“离开古代氏族社会的纯朴道德高峰的堕落” 的必然结果。因此,走向理想社会的必由之路,就是扬弃那令人目盲、耳聋的物质形态的美——艺术,回到“道”,回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自然状态之中去。因为只有自然,才是无为而无不为之“道”的艺术品,也只有“莫之为而常自然”,才是与道同一的真正审美境界。因此,尽管老子和庄子的美学,无疑有一种思辨哲学和审美哲学的意味,但在本质上,却仍是社会政治学的。他们的“自然之道”,虽然有一种形而上学性质,却不是西方“物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只是中国“伦理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中国文化的土壤,只能首先开出伦理美学或艺术社会学之花。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后来由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封建地主制的秦汉帝国在政治上作了结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美学也就成了中国美学的正统学派,而其在两汉的代表著作,则是《礼记·乐记》和《毛诗序》。《礼记·乐记》的作者是谁,成于何时,学术界颇多争论。但本文认为,就其思想内核而言,当产生于战国而完成于西汉。因为贯穿于其中的,正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礼乐同体”的艺术观。它反复地以“天道”比附“人道”,以“物理”比附“伦理”,提出“礼者天地之别,乐者天地之和”“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的观点,明显地带有董仲舒那个时代的印记。要言之,儒家伦理美学的神学化,只能是儒学被定为官方正统哲学的必然结果。于是才有“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社会功利论,有“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的审美教育论,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艺术创作原则,有“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的艺术欣赏原理。一切通乎伦理,一切为了政教,名为“天人合一”,实则泯灭个性。总之,大道理已经说尽,老调子已经唱完,中国美学在期待着新的机会,以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二〛封建中期艺术哲学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到了,那就是社会动乱达三百年之久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封建社会从前期到后期、从早熟到成熟的转折时期,其间有许多“反常”现象。在经济上,它表现为封建地主经济向封建领主经济的倒退,豪强兼并土地,庄园坞堡林立,大批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不再是向国家交纳赋税的编户齐民,而沦为与坞堡主有着人身依附关系的农奴或准农奴;在政治上,它表现为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分崩离析,一方面是南方汉政权的迭次更替,另方面是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相继建立历时极短、五花八门并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性质的政权;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儒学信仰的危机、传统价值的失落和外来文化的入侵。总之,在中央政权不再有力量进行更多钳制的情况下,思想文化界出现了继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空前活跃与繁荣,其核心,便正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正是通过这一批判和反思,早熟的封建文化才得以走向否定之否定的成熟。
在这里,起着极重要作用的便是玄学与佛教。玄学是从儒学内部发展而来的反对派别,即由东汉名教之治的清议,而清谈,而玄谈,而玄学,终于成为一种论本体、辨言意,具有较浓形而上学思辨色彩的“纯哲学”。佛教在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直到这时才真正风靡全国,并开始其中国化的过程,形成玄学化的佛学——般若学。玄学盛行于前,佛学(般若学)风行于后,二者都有一种迥异于传统思维模式的新鲜活力,启迪着中国知识界以新的眼光看世界,也以新的眼光看艺术。这种新世界观的体现,在审美领域,是如宗白华先生所说,对内发现了人情美,对外发现了自然美;在艺术领域,则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产生了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为艺术而艺术”作为新崛起的美学原则,是对“为政教而艺术”的反叛。于是,当哲学脱离经学而成为“纯”哲学时,艺术也超越政教而成为“纯”艺术。先秦两汉艺术社会学的影子已日淡如水,文坛上高扬的是“诗缘情”的旗帜,而“诗缘情”之取代“诗言志”,也就是个人私情的自我扩张取代了伦理观念的普遍传达,导引着诗人艺术家的,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和审美意味的人生态度——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造就了一种“哲学的艺术”。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人物、玄言、山水。这是一个走向“太一境界”的正反合过程,虽一则为“神超形越”的品评,二则为“但陈要妙”的说理,三则为“澄怀味象”的欣赏,但一以贯之的,却正是对永恒生命本体的追求,即以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哲学态度,去观照自然,体验人生,以有限求无限,化瞬间为永恒。无论是那感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慷慨悲歌,抑或是那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玄远风神,还是那澄怀观道、得意忘言的审美心理,都如此。它们都是要通过那看似无意、貌似无为的人情物态,去体验“自然之道”这个生命本体的大意与大为,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这种“与道同一”的“太一境界”,在刘宋山水诗那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而“哲学的艺术”也就从此走向更为成熟、更为纯粹的艺术,并把哲学留给了自己的理论。事实上,文学艺术与审美意识的独立,确乎需要哲学在理论上予以肯定。自从曹丕的《典论·论文》把文学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从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以来,艺术的本质与功能,再一次成了中国美学的头号重要课题。无论是嵇康的《声无哀乐论》,还是陆机、钟嵘的“滋味说”,都以一种对形式和形式感的高度自觉,强调了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而当萧统提出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标准时,这种精神就在理论上更为自觉了。于是,在这个极富创造精神的艺术开拓期和理论开拓期,当众多的艺术现象和艺术问题迫切要求理论作出解释和回答时,一种具有总结意义的艺术哲学也就应运而生。
这就是刘勰的《文心雕龙》。这部中国美学史上杰出的艺术哲学著作,以一种中国美学罕见的本体论宏观态度和因明学逻辑方法,对先秦到齐梁之间的文艺学理论,做了全面清理、高度概括和哲学总结,提出了一个以“自然之道”为核心的艺术世界观。这个艺术世界观认为,“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本体,包括文学艺术和一切审美形式在内的“文”,归根结蒂是“道”的产物,是“道”的外在形式和表现,因而具有一种与天地并生、与万物共存的普遍性。从“自然之道”出发,刘勰第一次将文学的反映论与表现论、实用论与目的论统一起来,提出了一个包括本体论、发生学、形态学、创作论、批评论和作家论在内的严密体系,而“勒为成书之初祖”。事实上,《文心雕龙》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毋宁说是整个时代艺术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
于是,在接受了哲学的洗礼之后,中国美学和中国艺术开始走向成熟。如果说,先秦两汉艺术社会学是艺术的“知之”阶段,即由思想家们根据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总体把握,来告诫人们“艺术应该是什么”;魏晋南北朝艺术哲学是“好之”阶段,即由艺术家们本着“文学的自觉”精神,反思“艺术可能是什么”;那么,中唐之后,中国美学将进入“乐之”阶段——艺术心理学阶段,即由鉴赏家们根据自己的审美经验,来描述“艺术实际是什么”。“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更何况在这时,艺术已发展到炉火纯青的成熟程度,而重大的理论问题又被认为已经解决。那么,剩下的事情,难道不只是“一味妙悟”,并把那审美的愉快传达出来吗?
〚三〛封建后期艺术心理学
的确,中唐之后,无论中国社会,抑或中国美学,都已走向成熟。
中唐以后政治上成熟的标志,是科举制度的确立。它意味着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体制结构已通过由儒生组成的官僚机构这一中介,有效地、牢固地耦合起来,形成一种既有弹性又有韧性的组织力量,从而使儒家的国家学说现实化为超级稳定社会结构,真正成为封建社会的立国之本。中唐以后文化上成熟的标志,则是禅宗的盛行。它既是本土文化(孔孟庄玄)与外来文化(印度佛教)的有机结合,又是正统文化(忠君孝亲)和非正统文化(礼佛避世)的相得益彰,还是政界文化(仕途、军旅)、都市文化(商贾、青楼)、江湖文化(侠)与山林文化(隐)的互补交融。社会与自然、群体与个体、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富贵功名与逍遥之乐,乃至物质与精神、此岸与彼岸,似乎都在这里找到了相互沟通和相互转化的最好中介。而这一中介,说到底,又不过只是“悟”与“迷”之间的一念之差。那么,以成熟了的中国封建社会和成熟了的中国封建文化为背景的中国美学之转向心灵,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封建后期审美心理学的第一人是司空图,而划时代者为严羽。以司空图、严羽为代表的唐宋审美心理学,其显著的特点,在于他们的理论视角即出发点和着眼点,已既不是艺术社会学的政教之理,又不是艺术哲学的形上之道,而是审美主体的美感经验——文外之味。味在文外,也就是美在心灵。因此,继司空图提出审美鉴赏必须“辨于味”,而“味”又在“咸酸之外”后,严羽明确指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艺术)的传达载体和心理感受既无关于知识与观念,那么,当然也就以“不涉理路,不落言荃”者为上,而必须“一味妙悟”和“唯在兴趣”。妙悟也好,兴趣也好,都是艺术心理学的范畴。它们既非共存于群体之中的道德观念,又非常存于作品之中的形式规范,而只是审美主体当下即得的瞬间感受,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得于意象又诉诸心灵的心理效应。不仅是形象大于概念(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而且是欣赏大于作品(言有尽而意无穷),主体的创造性超越客体的有限性。所以,艺术的“妙处”是“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艺术的“兴趣”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而艺术的本质规定也就只在心理学之中,这真是中国美学的一大变革,舍此便没有封建后期千余年无比丰富多彩的感受型经验型美学,也没有中国人审美意识的真正自觉。当《礼记·乐记》用“统同”和“辨异”来区别乐与礼即艺术与非艺术时,或者当昭明太子用“能文为本”和“立意为宗”来甄别文学与非文学时,他们虽然意识到了文学艺术理应有着自己的本质特性,但他们对这一特质的界定,却仍是外在的,甚至前者还是非艺术的。只有当严羽提出“妙悟”与“理路”之别时,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才是内在的和心理学的了。至此,文学艺术才真正在理论上获得了独立。
当诗人和艺术家们津津乐道地“一味妙悟”时,一种注重审美感受、审美趣味的经验形态的“理论”也就取代了前期的艺术社会学和艺术哲学。老成持重的中国人已不再去强调艺术对于社会的实用价值,也不再去构造什么艺术哲学的庞大体系,而是驾轻车沿熟路,把目光转向艺术的趣味、风格、技巧和情调。总之,不再是寻根问底,也没有高谈阔论,而是仔细地品尝,反复地斟酌,认真地推敲,感受到入微之处,一切文字和概念都已失去精确表达的功能,而只能诉诸介乎形象与概念之间的暗示,让读者自己去心领神会。这可以说是中唐以后中国美学的主流。
在这个艺术心理学时期,有两个人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明中叶的李贽和清初的王夫之。尽管他们一个是新文学的鼓吹者,主张“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并把《西厢》《水浒》一类俗文学,抬到与《六经》《语》《孟》相提并论的高度;另一个则是旧传统的维护者,认为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仍有数典忘祖之嫌,谓之“吾未见新鬼之大也”;但是,他们的共同之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都深受禅宗的影响,因而都注重艺术活动的心理特征和强调艺术情感的真实性。作为王阳明哲学的杰出继承人,李贽学说有一种禅宗式的平民化世俗化特色和呵佛骂祖的批判精神,但其思想内容却带有明显的近代特征和异端色彩。所以,李贽不仅认为艺术的真实在于心灵,而且认为在于童心。“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也就是一己之“私心”。与之相反,王夫之虽然也认为艺术的真实在于心灵,但强调它又必须是审美主体对客观事物当下即得的真实反映,他借用禅宗的术语称之为“现量”。现量者,现在、现成、显现真实之谓也。即不但是审美观照中当前直接感知和瞬间直觉获得的经验,而且是客观事物完整实相与审美主体真实情感的统一,即“情景合一”。因此,王夫之提出,诗学的方法,在本质上是属于心理学的,即“总以灵府为逵径,绝不从文字问津渡”。显然,如果说司空图、严羽主要是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来对艺术本质作心理学的界定的话,那么,王夫之诗学的中心便是艺术创作心理学了。他们在方法论上之明显地有别于前两个阶段,实已无须赘言。
封建后期的艺术心理学,在王夫之这里达到了高峰,也走向了终结。事实上,王夫之的现量说即已表现出向封建前期艺术社会学回归的倾向。他说:“只咏得现量分明,则以之怡神,以之寄怨,无所不可,方是摄兴观群怨于一炉,锤为风雅之合调。”十分有趣,《礼记·乐记》《文心雕龙》和王夫之诗学,分别作为中国史前期美学三个历史阶段的总结者,都带有明显的儒家美学印记。尽管有墨、道、法家的批判,有玄学与佛教的冲击,有禅宗和明中叶异端的干扰,儒家文化和儒家美学总是能在挑战面前应付裕如,一面坚守立场,一面化敌为友,丰富和完善着自身,并为每一次变革作出总结。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值得引起学术界注意的文化现象,但本文已无法展开,只有留待将来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中国古代美学之所以有着这样三个历史环节,完全是它按照内在逻辑而自身运动的结果。前已说过,中国美学的文化土壤,是以群体的人为核心的伦理型人文文化,其思想内核则是宗法群体意识。因此,它必然将自己美学的主要理论视线,投向政教伦理、人际关系、社会交往和情感传达方面去,并更多地关注艺术。因为艺术恰好有一种交流情感、沟通心灵和维系群体的心理功能。孔子早就说过,不学诗,便“无以言”,即不能进行社会交往,也就等于面墙而立。所以中国美学的主要课题必然是艺术,而第一环节必然是人际。由“人际”(艺术社会学)而“天人”(艺术哲学)而“心物”(艺术心理学),既是中国美学从客体走向主体的转化过程,又是艺术本质从外在走向内在的认识过程;既是文化模式从早熟走向成熟的深化过程,又是美学思想从开创走向终结的僵化过程。这种内在逻辑力量之强大,当是墨法、老庄、屈骚、玄禅乃至李贽们最终只能成为补结构和亚文化的悲剧所在。王夫之以后,有清一代,已不再出现划时代的美学大师。中国古代美学已在精细入微之中走向穷途末日。 只有当帝国主义的炮舰敲开中国封闭的大门,马克思主义乘北方十月之风吹入中华大地,给古老民族以新的生气时,中国美学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历程。
我们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通过对西方文化的吸取和对自身文化的反思,中国美学将走向自己的新阶段。那将是一个具有世界文化高度的现代美学,一个中国美学真正光辉灿烂的时代。我们将以自己的全部热忱和智慧,去迎接和拥抱这个时代。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易中天谈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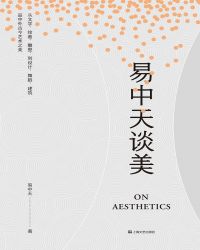

![在后妈文里当女配[七零]](/uploads/novel/20210419/0972fc914f8ccf05a8fe61a562a11f06.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