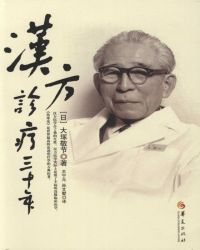代序
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年)时,我还是熊本医学专科学校(现熊本大学医学部──译者注)的二年级学生。有一天,我路过熊本市外水前寺公园后面的一条街时,看到了“汉方深水医院”的名牌。那时见过的其他医院的广告牌子于今都忘记了,只有这个深水医院的名牌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为什么只记住了这个名牌呢?这是因为数年后我也研究起汉方,得以翻阅旧时记忆的缘故吗?不,并不是那样。
当时看到这个名牌时,我是用轻蔑的眼光看“汉方”两字的。其实这家深水医院是从德川时代(即江户时代,1603-1867年──译者注)延续至今的汉方医学名家,对此一无所知的我,好像透过名牌看到的是一种江湖庸医的面孔。
可是,有些讽刺意味的是,数年之后,我只要看到“汉方”两字时就要激动得心里扑通直跳,自己已经一头扎进汉方医学的世界里了。
为什么学习现代医学出身的我,又告别了现代医学,做起了被世人冷淡和疏远的汉方医学研究呢?现在静静地回顾这些事情,最后应该可以用这么一句话作为答案,就是“汉方医学合了我的生性”。
对于“你为什么做起了汉方研究”这样的询问,我做过如下的回答。
(一)自己幼年时因病而体弱,对现代医学治疗的无力感心生厌倦。(二)我家代代行医,家里有汉方的医籍和家传的方药。
可是,再仔细考虑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使用汉方治好过多名医生的疾病,虽然这些人生病时也服用汉方药,但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去研究汉方。另外,即使是出身医家,也有家传汉方医籍和方药的医生,像我这样放弃现代医学投身于汉方研究的人也很少见。
这样想来,我之所以能够迈进汉方研究世界的理由,除上述的(一)、(二)之外,我自身性格使然的考虑,应该是更接近真实的吧。
但是,如果没有下述的机会,在我的一生中也许就不会出现进行汉方研究的事情了。
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译者注)的三月,我从学校毕业,虽然取得了医师资格,但自己并没有一生投入到医学研究中去的想法,总有一种所学得的医学与自己性格不符的感觉。就这样,没有一个要去积极做某件事情、达成一定目标的理想,完全是顺其自然地回到了家乡。父亲是个开业行医的医生,于这一年的十月里五十五岁上病故。
我必须为养活母亲和弟弟妹妹而工作,然而除了行医才能支撑生计,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于是我就继承父亲的工作,在土佐(日本旧国名,今高知县──译者注)的海滨开业行医了。
就这样,我不由自主地成了一名医生,很快地度过了二、三年的时光。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译者注)三月的一个早上,我像平时一样,于开始诊疗工作前先看看报纸《读卖新闻》。该日报纸文艺栏目里有一篇对《汉方医学的新研究》的书评。书的作者是中山忠直,书评的作者叫福永荣。我看了这篇书评,产生了阅读的念头,便立即向出版社宝文馆订购了该书。
中山忠直在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年──译者注)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秋季增刊号上发表了《汉方医学复兴论》,引起了轰动。《汉方医学的新研究》就是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作了若干补充而于昭和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令我惊奇的是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出版发行的。
我读了这本书,知道了一直被自己小看的汉方医学实际上是很了不起的高级临床医学,以前认为汉方医学也就是煎服一些类似鱼腥草、老鹳草等药草的民间疗法,现在真是为自己的无知而羞愧了。通过这本书的介绍,我知道了汉方医学的《伤寒论》是世界最高的论述治疗学的古典医著。我从储藏室里找出了《伤寒论》,打开来看,但全是很难认的汉文,一行也没有读下来。
那个时候,《读卖新闻》几乎每天都在公布向内务省提交的新刊行书目。看看有没有汉方医学相关的书呢?每天早上我都是一边激动着,一边仔细地搜索着这个栏目。就这样,终于发现了于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译者注)六月二十八日发行的《皇汉医学》第一卷,便订购了该书。这本书是后来成为我的恩师的汤本求真先生在生计困苦中以自费的形式出版的,我读了它,下定了把自己一生投入到汉方研究中去的决心。
从那时至今,三十年的日夜流逝而去。
现在,在执笔写《汉方诊疗三十年》之际,回顾往昔的岁月,万千的感慨充满于心胸。
汤本先生的《皇汉医学》第二卷、第三卷也相继出版,我惜时如金地阅读它们。一遍又一遍地读了,但是,越读越觉得不明白的地方越多。
昭和五年(一九三〇年──译者注)的一月,我决意关闭诊所,从零开始学习汉方医学。这可以说是背水一战。
到东京去,然后在汤本先生的身边认真充分地学习,下了这样决心的我,于这一年的二月二十六日早晨,到达了东京。
我在神明街车站下了汽车,向一位路过的老人询问:“一位叫汤本的汉方先生的住所在什么地方?”
“不远,水沟对面的那家就是哟。”
我按照老人所指的方向,找到了一家小而陈旧的平房。这个家就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尊敬的汤本求真先生的诊所兼住宅。
大门口挂着“皇汉医术诊疗教授汤本医院”退色字迹的名牌。
我在相邻的房子里住下了,本来非常疲劳,但这一夜怎么也睡不着觉。天快亮时,梦见自己去乡下出诊了。第二天,我和荒木性次、佐藤省吾两君一起成为了先生的门下生。
汤本先生是于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译者注)以首位成绩毕业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的高才,但因有所感,便放弃了现代医学,学习汉方,已经自成一家。
日本政府在明治初年废除了汉方医制度,形成了西洋医学一边倒的局面,所以现在汉方医这种特别的医师消失了。但是在我决心投身到汉方医学世界的昭和初年,从明治初年留下来的纯粹汉方医和学习西洋医学取得医师资格后又转向汉方研究的人还有一些。虽然说即使废止了汉方医制度,只要取得了医师资格,也还可以自由地进行汉方治疗,但是学习了现代医学之后再转向汉方研究的人极为罕见,汉方的传统几近断绝。
日本的汉方进入德川时代后产生了多个流派,其中占主流有古方派、后世派和折中派。
汤本先生是代表昭和时代古方派的大家,我跟随先生学习了古方派。古方派的基本立场是,只要研究了汉末医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唐宋以降的杂书就没必要看了。为此,在最初的二、三年里,我全力以赴地做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研究。这样一来我达成了与汉方医学最根本经典的亲近和熟悉。像这样在学习的初期,没有涉及杂学,而能够直接全力攻读了伤寒论,这是汤本先生予我的恩赐。
但是我终于还是产生了疑问。《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重要性是自不待言的,可是唐宋以降名医的著作都是无用的吗?真的就没有研究价值吗?
这些疑问藏在心底不得释然。有一天,从我的汉学老师权藤成卿先生那里得到了如下的告诫。
“你是个古方派,可是古方派有排他癖。你不觉得这是古方派的短处吗?”
我好像突然被刺了一下,吃了一惊。如果只认古方为是,便以后世方为非,这种态度与只认现代西洋医学为是,以汉方为非的态度不就一样了吗。此时,我做了深深的反省。又下了决心,不论唐、宋、金、元、明、清的医书,还是德川时代后世派和折中派医家的著述都要读。于是,将龟井南溟(1743-1814,日本江户时代医家──译者注)的箴言挂于壁龛,
“医者意也意生于学方无今古要期乎治”
对呀,是这样的,从我的心底发出了共鸣。
对于医术,没有古方与今方的区别,能够治愈疾病就好。
这样,我从古方一边倒中解放出来,与后世派和折中派医师交朋友,壮大了自己的药囊。
在这里,再次向这些师友献上感谢的话语。
我在本书中,收集了三十年经验里的近三百七十例验案。其中的约一百五十例曾在《古医道》、《汉方与汉药》、《东亚医学》、《东洋医学》、《汉方》、《日本东洋医学会志》等杂志发表,这次又作了简单的修改。其他案例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病例记载中挑选的,以汉方诊断的必要证候为主,现代医学的记载尽可能地简略。在这些案例中也有失败例和令我赧颜的拙稚东西,考虑到这类案例也许反而成为初学者的参考,也就鼓足勇气收录进来了。这里案例的主人公们给予了我宝贵的经验,在这一点上与师友一样也是我的恩人。
在即将止笔之时,也向他们各位奉上感谢的话语。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三日于梅开之窗际 著者 汉方诊疗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