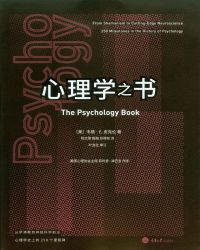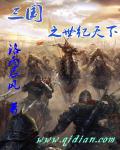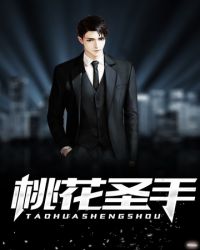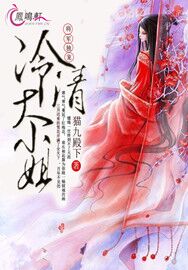序言
构成我们的材料也就是构成梦幻的材料,我们短暂的一生,前后都环绕在沉睡之中。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暴风雨》,约1611年
※ 序言
心灵有它自己的地盘,在那里可以把地狱变成天堂,也可以把天堂变成地狱。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
《失乐园》,1667年
大约40年前,我做了一个令我至今仍感困惑的实验。我在探索“什么样的环境催生了罪恶”这一问题时,我发现,在斯坦福大学地下室的模拟监狱中,那些原本仅仅是进行角色扮演的大学生志愿者,竟毫无顾忌地做出了残酷行为。事实上,这些行为与心理发生了巨变的学生,都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年轻白人,他们被随机分配担任“罪犯”或“警察”的角色。该实验原计划进行2个星期,但仅仅在6天后,我就不得不终止了实验。正如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早年证明的那样,大多数普通的成年人经过引导,都容易盲目地服从非正义的权威。我的这项研究,同样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描绘了无处不在的情境因素,如何压制了个体的意向倾向性。
在几十年后的2004年,阿布格莱布监狱发生的虐囚事件,再次证明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正确性。我在2007年出版的《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一书中,描绘了两种对比的情境,清晰地阐述了由显著的权力差异所激发的心理动力因素(psychological dynamics),这些动态性因素包括去个性化、服从权威、自我辩白、合理化与去人性化。尤其是去人性化,它使一个普通的个体变得冷漠,甚至成为荒唐而偏执的犯罪者。除了调查导致这些罪恶行为的因素,我还对了解隐藏在人们及其情境背后的因素感兴趣。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人们无视罪恶、形成公众冷漠(public apathy)、对其他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或在紧急情况或犯罪情境中出现旁观者效应(bystander effect)。
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罪恶产生的心理机制。我之所以这样做,本身就证明了,在一个罪恶产生系统的影响下,那些广泛的情境因素会对人们的行为造成影响。我是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南区的犹太人贫民区长大的。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我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以及对事件轻重缓急的看法。都市贫民区的生活,就是依靠发展有效的“街头智慧”(street smart)策略来生存的生活。这意味着,如果谁有力量攻击或者帮助你,你就要注意避开谁或者迎合谁。这还意味着,为了创立互利互惠的责任,就要去破译那些微妙的情境线索,以确定什么时候可以赌一把、什么时候必须果断地放弃。对我这个骨瘦如柴、疾病缠身的小伙子而言,最重要的是,通过观察不同情境中这两种类型,来理解一个人是怎样从一个被动的追随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领导者。我一旦把握了这些行为或语言差异的关键,我就容易变成一个领导者、队长,甚至通过选举成为美国心理学会的主席。
在那些日子里,贫民区的生活就是没有财产的人们的生活。这些小孩中,一些变成了暴力犯罪的实施者或受害者。我认为,一些孩子之所以最终干了一些真正的坏事,部分是因为他们被更大的孩子带坏了。大孩子为了获得钱财,唆使小孩子干坏事,比如贩卖毒品、盗窃甚至卖掉他们的身体器官。我非常清晰地了解,这些坏孩子与我另一些朋友的差异。这些朋友没有越过那条罪恶之线,因为他们保持着积极向上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又来自于抚育他们的完整家庭,比如至少在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父亲都陪伴在身边。
但是,即使是我们这些好孩子,大多数也要接受来自东区151街的成人仪式。作为加入这个群体的步骤之一,我们都要去偷小卖部,或同其他后来加入的成员打架。我们胆大妄为,恫吓他人。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是罪恶的,甚至是不好的;我们只是服从群体的领导,遵守群体的规范。成长于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就很容易明白,我为什么会对这种恐怖的权力来源特别感兴趣,并用我整个的生命在抵制它,包括反对那些政治势力,它们迫使我们的国家进行不必要的、非道德的越战或者伊拉克战争。
我在美国心理学会的一位曾经的同事、历史学家韦德·皮克伦(Wade Pickren),把研究心理与行为历史上有趣的里程碑事件集合起来,给予读者一个比四十多年前斯坦福地下室所展现出来更为广阔、更有意义的发展情境。当然,这本罕见的书籍还做得更多——它为我们欣赏构成人类生活条件的众多因素,提供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历史情境。还在史前时代,人类就已经在寻求如何更好地理解自我与他人。以人类的残酷行为偏向(propensity for cruelty)为例,解释就多种多样,从犯罪幽灵、荷尔蒙失衡到反社会人格等,不一而足。到了20世纪,攻击性的原因又被追溯到复杂的性心理,或大脑中杏仁核过度的神经活动。当然,暴力来自于生理、心理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但已有众多的研究表明,当下的“情境性”压力,比我们所已知的、跨情境地塑造我们行为的因素影响更为强大。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一系列无处不在的、微妙的情境因素,能够决定一个人对抗的意愿。是强有力的复杂因素系统,组成了整个情境。但是,大多数心理学家,对那些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及文化等规定情境以及决定情境是否合法的系统力量与深层根源并不感兴趣。与原本仅仅关注“坏苹果”相比,我们必须意识到揭示“坏桶子”的本质(有时“好苹果”放在坏桶子里面就变坏了),了解谁是“坏桶子的制造者”,才能对犯罪动机有一个完整的把握。因此,我建议,对人类行为动力的完整鉴别,需要我们了解个人力量、情境力量及系统力量作用的范围及作用的有限性。
心理学领域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切探究人类心灵的研究,最终的目标都是在个体与社会的基础上,改善人类的生活质量。无疑,了解心理障碍及变态行为背后的生理机制是很关键的。在过去的100多年里,我们关于大脑的知识已经显著增长。但是,据近年的估算,存在于大脑皮层及小脑的神经元约有1000亿个。大脑比宇宙中任何其他的物质更为复杂,也更难理解。最近,奥巴马总统发起了一个名为“大脑”(“BRAIN”)的项目,这有助于阐明大脑的神经活动、心理状态及其产生的行为之间的重要关系。但是,面对大脑这一奇妙的器官,我们的认识也许永远都不会完结。
确实,神经科学为了解大脑如何工作提供了重要而详细的信息。但是,我们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脑科学在告诉我们作为人类的生活及其经验等方面,还存在缺陷。相对而言,社会心理学采取了更为广泛的观点,退回来观察文化框架中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如果要改变或预防个体或群体的不良行为,就需要了解特定情境中人们的力量、美德或弱点。然后,我们还需要更加完整地意识到在具体的行为情境中起作用的情境因素的复杂性。其中,有些因素在文化内至关重要,但对文化外的人而言却难以理解。想办法改变或避免这些因素,比仅仅在情境中直接实施治疗行为,更能减少个体的不良行为。
当前,大多数治疗项目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往往聚焦于个人的改变,即通过教育、宣传、治疗、惩罚、拷问、监禁或流放,来改变单个的个体。但如果犯罪因素是情境性的、系统的,或者不同个体本身就具有不同的反应模式(如:现在导向—未来导向),这些做法就很难获得预期的结果。相反地,我认为,在普通大众中,提倡预防措施的公共卫生模式,要比直接治疗个体已有的病痛与伤害的标准医疗模式更为有效。当然,除非我们对这一系统(真实因素它往往是隐藏于神秘的面纱背后)有着更为清晰的了解,能更为完整地把握这一系统运行的规律与法则,否则,行为的改变将是暂时的,情境的改变则更加虚幻。
最后还强调一点,对我而言,最为奇妙的是现当代的心理学研究,在拓展宽度的同时正在增加深度。我的一些同事正致力于发展新的方法与技术,来破解个体、群体与社会(跨文化、跨年代)的心灵、大脑及行为的秘密。(叶浩生 译)
菲利普·津巴多博士(Philip G.Zimbardo)
斯坦福大学名誉退休教授 心理学之书:从萨满教到神经科学前言,心理学史上的250个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