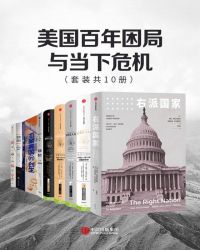3.寻找“金山”的华人移民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部分
大规模移民
与排亚时期亚裔美国的创生
3.寻找“金山”的华人移民
1848年1月24日,詹姆斯·W.马歇尔(James W. Marshall)在北加利福尼亚的美利坚河边发现了黄金。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者纷纷涌入加利福尼亚,淘金热随即开始。这一消息花了些许时间才传到中国,但它一旦抵达中国,就像大火一样蔓延开来。一名广东人在给他弟弟的信中写道:“很多美国人都在谈论加利福尼亚,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金子……我想明年夏天我应该去加利福尼亚。”
1849年,325名中国“四九年人”前往加利福尼亚。1850年,来到这里的人数比上一年多出450人。在一年之内,这一数字呈指数增长:1851年,有2 716名中国人来到加利福尼亚,1852年达到20 026人。只有少数人在金矿中致富,但在美国也有足够多的经济机会,再加上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引发了中国移民的新时代。正如一则广告所宣称的,中国的劳工招聘人员向潜在的移民们发出了这样的信息:“美国人是非常富有的。他们想要中国人来到美国……在美国,钱很多,且好赚。”到1870年,美国有63 000名中国人,其中大多数(77%)在加利福尼亚地区。
在成千上万涌向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中,有我外高曾祖父梅东基(Moy Dong Kee)。他于1854年抵达旧金山,当时是一名20岁的已婚父亲,来自中国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孙乔克村(Sun Jock Me Lun)。他把妻子和两个儿子留在身后,追逐着“金山”的梦想,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美国”。当他到达加利福尼亚的时候,山脚下已经没有多少金子了。不过他还是留了下来。我们不太了解他早年做了些什么。当他在美国官方记录中出现时,已是在45年之后。该记录是一份宣誓书,美国移民局在上面写着他打算前往中国并返回美国的意愿。
图6.梅东基的名片,1899年。
这种纸上证明只针对中国移民。从1882年开始,美国颁布了一系列排华法律,禁止华工进入美国,只允许某些“豁免”类别,如商人、学生、教师、外交官和游客,进入或重新进入美国。在华裔美国人的抗议之后,华人后裔的美国公民和美国公民及商人的妻子与子女也被允许入美或再次入美。但在美国所有的华人都在严格的监控下,我的外高曾祖父发现,他需要填写大量的政府表格,以使他服从讯问和调查,并在两个白人见证人面前提供宣誓书,这两个人在他离开和重新进入美国时证明他以及他作为商人的身份。
他1899年的申请是在纽约市提出的,当时他在那里已做了20年的市民和商人。他跟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离开西海岸寻找更好的机会和更友好的社区。1882年,他在纽约中国城的查塔姆广场(Chatham Square)开设了跃升公司(Yuet Sing & Company)商店,几年后又将其搬到了莫特街(Mott Street)6号。到了19世纪90年代,他在费城的中国城开了另一家店,然后又在莫特街14号开设了广华泰公司(Kwong Wah Tai & Co.),并在他的双语名片标示出该公司是“中国食品及普通商品的进口商和经销商”。
但就像当时的许多中国移民一样,梅东基的生活也横跨太平洋。他的家人留在了孙乔克村,他在回到其出生的村子退休之前,在美国45年的旅居经历中,至少三次往返于中美之间。他把自己的生意传给了大儿子梅坤喜(Moy Quong Shee)。梅坤喜离妻别子,继续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穿梭,在纽约和费城经营家族生意,并采用了约翰·梅(John Moy)的名字。
到1907年,我的外曾祖父梅华忠(Moy Wah Chung)进入美国。因为他,梅家三代人的跨国家族模式随之终结。1911年,他与袁西(Yuen Si)结婚,并于1912年生了一个女儿,名叫寿白(Sau Bik),也就是我的外祖母。1918年,一个叫崇蒙(Chong Mon)的儿子降生。第二年,我的外曾祖父决定永久定居美国,并更名为雷蒙德·梅(Raymond Moy)。作为一名中国商人,他有资格把他的妻子和孩子带到美国。当他向美国政府提交必要的表格来协助妻儿进入美国时,雷蒙德列出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一个是崇蒙,另一个其实是他的侄子崇顿(Chong Don)。寿白则从未被提及过,根据美国移民局的记录,她并不存在。崇顿占据了她的移民指标,并取代了她进入美国。而我的外祖母仍然留在广东,跟着她的祖父母,并进入学校学习。
有很多原因让我的外曾祖父决定让他的女儿留在中国。也许他认为男孩更有可能找到稳定的工作并为家庭经济做出贡献。也许崇顿没有别的办法来移民,给他出入境的机会是外曾祖父向家族长辈尽孝的方式。也许他认为我的外祖母留在中国比较安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的行为实际上把我的外祖母排斥在美国之外。她此后再也未曾见过母亲。嫁给我的外祖父季慧兵(Huie Bing Gee)后,直到1933年她才移民到美国。外祖父是一个在纽约的商人和餐馆老板。
我的外祖母很讨厌被留在中国,不过一旦到了纽约,她和外祖父便开始了新生活,并生育了三个女儿。外祖父在布鲁克林成功地经营着两家餐馆。其中的一家餐馆在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的联邦计划(federal program)之后,被命名为“新政炒面店”(New Deal Chow Mein Inn),它位于布莱顿海滩(Brighton Beach)的一处名为“小敖德萨”(Little Odessa)的地方,客户主要是犹太人。这家餐馆是一个家族餐馆。外祖父经营生意,许多厨师来自他在中国的家乡。外祖母作为餐馆的女主人穿着优雅的中式服装——旗袍。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放学后做蛋卷,一块可赚一美分。“新政”餐厅的菜品包括粤菜龙虾、鸡肉炒杂碎和新政捞面(New Deal Lo-Mein)。“新政”餐厅的馄饨在当地名声大噪,多年后被人们记在一本以纽约市伟大烹饪传统为特色的烹饪书中。到了20世纪30年代,我的母亲和姨妈们在布鲁克林上了公立学校,上了大学,长大后自我身份界定为“首先是美国人,其次才是华人”。
经过长达四代人在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往返移民后,我的家族终于成为华裔美国人。
梅氏家族为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华人移民世界提供了一个窗口。家族成员被分割在太平洋两端,但由于他们通过偶然的回家、信件和汇款,保持着彼此的联系。梅东基在美国待了将近50年,但当退隐的时候,他回到了出生的村庄,在那里实现了作为一个富有、成功的“金山客”而荣归故里的梦想。
图7.季慧兵与梅寿白的结婚照,1931年。
梅氏家族“成为美国人”的方式在许多移民中很常见。梅东基并未成为美国公民,因为归化法禁止华人和其他亚洲人归化而获得公民身份。但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美国,先是在旧金山,然后是纽约和费城。他在纽约和费城中国城经营的生意,很可能是这些城市最早的生意。他与非华人供应商和客户做生意,学习了足够的英语阅读和写作能力。(他在美国政府所有文件上的签名都用英文。)尽管他在中国隐退,但其家庭的未来则与美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梅东基的移民文件也揭示了美国移民法律——特别是《排华法》——阻碍了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生活及其在中国的家人迁往美国。当梅东基1854年第一次来到美国时,他不需要任何文件即可进入美国,也没有任何讯问、医学检查或所要求的白人证词。正如另一位早期移民所回忆的:“在那些日子里……人们来去自由。我们卷起铺盖,收拾好篮子,整理好衣服……将它们装上一辆正在等待的手推车。”但是,当梅东基在1899年填写他的宣誓书时,因种族和阶级的不平等已成为移民法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切都改变了。作为一个商人家庭,连续两代梅氏家族的儿子们都能几乎没有太大困难地进入美国。但我的外祖母被排除在美国之外,这揭示了性别不平等如何成为美国移民法针对中国移民战略的一部分。
梅氏家族只是世界范围内华人大规模迁徙的一部分。来到美国的中国人与那些去东南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北美和南美其他地区的人,其迁徙是平行的。据估计,从1801年到1875年,有55万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6.5万人去了澳大利亚,17.8万人去了美国,3万人去了加拿大。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初,像我的梅氏家族祖先这样到美国的男性移民,尤其与到加拿大、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多有重叠。所有这些移民一道,经过数代人的时间,帮助形成了近现代离散华人。
淘金梦首先驱动了华人去往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8个地区。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国内危机和外国干预使得该地区到美国的移民持续并扩大。作为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的贸易中心,珠江三角洲是美国劳工招募人员、商人和传教士的乐园,而美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也有助于建立一个利润丰厚的跨太平洋中国移民业务。到19世纪60年代,香港已成为一个“建立在移民之上的城市”。
虽然公众舆论经常把在美国的中国劳工视为不自由的苦力劳工,但把华人带到美国的体制同将华人送到拉丁美洲的体制不同。那些前往美国的人并不受制于契约,而是自己支付旅程的费用,或借钱支付船票。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信用票据制度支付船票。家族或同乡会为船票提供贷款,借款人承诺偿还本息。这种贷款有时收取的利率过高,需花上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能还清,但与古巴和秘鲁的苦力劳工不同,前往美国的华人在法律上不受其他人的约束。
然而,来到美国的中国人确实与那些去拉丁美洲的契约劳工有着共同的经历。例如,二者都被外国劳工组织大量招募。它始于19世纪60年代,寻找工人建造中央太平洋铁路时期。自1867年,太平洋邮船公司(Pacific Mail Steamship Company)在香港、上海和旧金山之间的定期跨太平洋轮船服务建立后,对华人劳工的招募工作变得更加频繁。在接下来的数年里,美国和日本的蒸汽船公司在美国与加拿大西海岸的西雅图、温哥华和其他一些港口开通了新的航线。一个新的移民时代开始了。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国外和国内的危机也继续推动着华人向海外发展。随着清朝的衰落,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动荡不断加深,日本在甲午战争(1894—1895年)中击败了中国,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加强了它们在中国的经济存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帝制的历史,但未能带来政治的长久稳定。相反,强大的军阀成了许多地区的主导势力;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内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争斗加剧;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再次与日本开战;30年代末,日本控制了中国的部分地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新中国的建立导致了新的动荡。
与此同时,美国通过同墨西哥的战争继续其帝国主义扩张,并进一步对美国原住民进行压迫。工业化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增长,在美国创造了对劳动力的极大需求。西部诸州尤其需要大量的劳工来开发自然资源,建设交通基础设施。中国人满足了这种需求。他们被一次次地雇用来从事白人认为太肮脏、危险或有辱人格的工作。而他们所获得的工资与白人相比却更低。
很快,中国的移民文化通过信件、返乡的移民,甚至是民间歌曲而得以建立。王升陆(Wong Sing Look)的哥哥(已经在美国)在给他写的一封信中写道:“尝试离开那个你永远无法在那里生存的村庄。”20世纪早期的粤语民歌赞扬“金山的旅居者”,如果没有“千金”,至少也有“八百”。像李澈(Lee Chew)这样的年轻人目睹了贫穷村民们是如何离开家园,返乡时又是何等富有。李村的一个“金山客”赚了足够的钱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有四个街区长的家族建筑,里面有宫殿、避暑别墅、小溪、桥梁、人行道和道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听说:“任何一个来到金山的人都能很快赚到钱,作为一个富人返回故里。”
对一些人来说,移民只是为了生存。然而,在20世纪初,在潘龙程村(Poon Lung Cheng village)的李驰业(Lee Chi Yet)年轻时就成了孤儿,作为一名农民“白白忙活”。他村子里的情况非常危急,周围不断有人饿死。他于1917年移居美国。80多年后,他解释了自己的决定:“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受苦受难!我得找条活路。我想活下去,所以我来到了美国。”其他村庄的情况同样糟糕。一个华裔美国人组织在1910年解释说:“我们中国人来到美国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保持在一起。我们应该被阻止吗?……我们的灾难能怎么诉说呢?”
一旦最初的移民去往国外,一个移民链在一些国际商业的帮助下就很容易出现。泛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代理人出售越来越多现代船只的船票前往旧金山、维多利亚和秘鲁的卡亚俄(Callao)。邮局、银行和金山公司,将人员、信息、资金和货物从中国传达到世界各地。有意向的移民可以购买船票、参加健康测试、安排文件,并在当地的金山公司(gam saan jong)填写领事表格。这些公司还向移民提供在香港停留的地方,等待他们的文书处理结果,并向他们出售长途旅行的必需品,比如被子、食物、泳裤和洗漱用品。这些人移民到他们已经有亲戚或同乡的地方,他们反过来鼓励更多家乡的人跟随他们的脚步。通过这些连锁移民,或移民的“渠道”,中国人遍布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
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美国的华人社区主要是由男性组成的,其中一半以上为已婚。像许多欧洲移民团体一样,中国男人经常作为旅居者来到美国,或者是打算在国外暂时工作和生活后回国的移民。他们被称为“金山客”(gam saan haak),或“金山人”(Gold Mountain men)。中国妇女确实也有移民到美国的,但人数很少。在19世纪,传统的中国男权家庭制度不鼓励,甚至禁止“体面”的女性移民海外。中国民间俗语有云:“一个女人的责任是照顾家庭,而不是想着出国。”一般认为已婚妇女应该留在中国,照顾其丈夫的父母,并代替缺席的丈夫履行孝道。加州恶劣的生活条件,激烈的反华暴力,昂贵的跨太平洋旅费,以及妇女缺乏就业机会的情况,也是阻碍中国妇女移民的因素。
但美国移民法对中国女性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最严重的障碍。1875年的《佩奇法》(Page Act)禁止涉嫌卖淫的亚洲女性,也禁止将亚洲契约劳工运往美国。1882年的《排华法》进一步阻碍了中国妇女进入美国。尽管她们并没有被明确禁止入美,但移民法所列举的豁免类型——商人、学生、教师、外交官和旅行者——在19世纪的中国几乎完全是由男人所垄断的职业或身份。
华人在美国发起的诉讼案件,最终使中国商人和华裔美国人的妻子和子女得以来到美国。但中国女性不能擅自移民。因为她们进入这个国家是基于其与男性亲属的关系,她们依赖其丈夫或父亲对她们进行的担保。此外,她们自己进入美国并留在美国的权利是基于其担保人的合法移民身份。如果其丈夫或父亲失去了继续留在美国的权利,她们也随即同样失去这种权利。尽管如此,这些家庭仍算是幸运的。对于像洗衣工和餐馆工人等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中国人来说,把他们的妻子带到美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1880年,中国女性占准入美国华人的人数比例仅为0.3%。到1900年,她们只占华人进入这个国家总人数的0.7%。在夏威夷,这种情况略有不同,在那里,种植园主鼓励中国的妇女移民,以之作为安定这些岛屿上中国移民劳工的一种方式。在1900年的夏威夷,女性占华人总人口的13%,而在美国大陆,这一比例仅为5%。
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大多数中国移民家庭都被太平洋所阻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要彼此造访就非常困难,许多妇女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山寡妇”或“被弃寡妇”(grass widows)。如果她们幸运的话,至少可以依靠信件和汇款来维持生计。但在俄勒冈州约翰迪(John Day)的钟锦华(Kam Wah Chung)公司大楼里发现的幸存信件记录了许多中国跨国移民家庭关系的破裂,以及他们的失望和哀伤。作为靠地区采矿、牧场、农业和伐木业支撑的小镇,约翰迪在19世纪70和80年代的繁荣时期曾有500~600名中国人。钟锦华商店既是一家职业介绍所、社交聚会场所,也是邮局,收发往来中国的信件。这些写好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才被发现的信件,尚未来得及收发。
以下是一个无名的丈夫,不知在什么时候写给他妻子的信:
爱妻:
你愚蠢的丈夫离开你到一个偏远不毛的异域土地已有数年……
但我没有能力寻得黄金,我被阻隔在这一陌生土地的偏僻角落里。
以下是一位母亲在1898年2月2日的信件:
秦鑫(Chin-Hsin)吾儿知悉:
汝已离家数载。这期间,汝二哥不幸亡故,随后汝父与汝长兄也相继亡故了。……如今,我已垂垂暮年,随时可能撒手人寰……
望你略备薄资,于来年之前返归故乡,勿忘汝母,切切。
你的母亲 注释标题 信件可见于Yung, Chang, and Lai, eds., Chinese American Voices, 97-102。
到19世纪末期,确实开始有少量的中国女性移民美国,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男性移民的数量还是一直超过中国女性。第一批女性移民中部分是作为妓女踏上旅途的,是那些被绑架、诱骗、贩卖和进口的被契约束缚或被奴役的劳工。一名妇女在1892年做证说,她是被承诺嫁给一个在美国富有且善良的丈夫后才离开中国的。但当她抵达旧金山时,她被以4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奴隶贩子。这个奴隶贩子以1 700美元的价格把她卖给了另一个人。她对调查人员说:“从那以后,我就一直是一个妓院的奴隶。”
少量的中国妓女成为中国富人的小妾或情妇,大多数则被卖给了唐人街的妓院。这些妓院是为了迎合满足富裕的中国人和白人男性。那些最终沦落在巷子里陈设简陋的小屋的女性被迫招揽顾客,直到她们被再次卖掉,或者死于性病。这些被称为“总是向上抱着腿”(lougeui)和“百人之妻”(baak haak chai)的中国妓女,是事实上的奴隶。
中国妓女逃脱的情况非常罕见。波莉·比米斯(Polly Bemis)在中国还是一名少女时被以1000文卖为妓,然后被带到旧金山,后来又被带到了爱达荷州。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再加上一点儿运气,她最终获得了自由并结婚,拥有并经营着一个远近知名的商号和牧场。多年来,她作为一名女商人和社区成员而受到尊重。她的房子现在是美国国家历史名胜登记在册的博物馆。
一些中国妓女得以求助于基督教女传教士,她们在旧金山管理着两个“营救”庇护所,为这些妓女提供逃离卖淫、包办婚姻和虐待关系的机会。其中规模最大的基督教长老会之家(Presbyterian Mission Home)先后由玛格丽特·库伯森(Margaret Culbertson)和多纳迪娜·卡梅伦(Donaldina Cameron)领导,它宣称已解救了1 500名女性。许多华人传教士之家的女性学得了宝贵的技能,以在往后的日子里派上用场。例如,12岁的泰伊·梁(Tye Leung)逃到长老会之家,逃离了包办婚姻。她留下来做翻译,帮助传教士营救中国妓女。其工作赢得了卡梅伦的赞扬,卡梅伦亲自推荐她担任美国移民局的口译员,并担任在天使岛移民站被拘留的中国妇女的女总管助理。基督教女传教士是妓女的唯一盟友,但她们的传教热情和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及其救援行动,也使得中国男性移民的负面刻板印象得以延续。中国男性移民被视为不道德的奴隶贩子,而中国移民女性被视为堕落的性奴,这种负面刻板印象助长了反华情绪。
随着中国男性留在美国的决定,其妻子和女儿的到来使得华人移民女性也越来越多。中国性别角色地位的变化,以及文化上对女性移民限制的松动,使得一些移民相对容易地离开中国。到1910年,在整个美国的中国移民中,女性占了9.7%。10年后,这一数据增加到20%,到1930年,女性移民的比例上升到30%。
其中的许多女性视婚姻和移民为经济机会。王兰芳(Wong Lan Fong)的经历并不少见。1911年辛亥革命后,她的家人缺乏稳定的工作,他们被迫在广东四处流动,寻找工作。她回忆道:“我记得每隔几年就搬家一次,房子会变得越来越小,也不那么好。”王家人卖掉他们的财产,这也让他们愈发悲伤。王兰芳的母亲病死后,父亲和继母催促她去找一个“金山客”嫁了,这样她就可以去美国。他们解释说,这是确保她未来经济状况的唯一途径。1926年,她嫁给了李驰业(Lee Chi Yet),一年后来到美国。刘曦若(Law Shee Low)的家庭情况更糟。强盗抢劫了他们所有的财物,毁坏了他们的农田。她回忆道:“我们变得很穷,没有饭吃。”一些邻居开始乞讨求生,甚至卖掉女儿。“就在那时候,我的父母决定把我嫁给一个邻村的‘金山客’。他们认为我会在‘金山’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然而,她们与之结合的那些男人却常常因为从事艰难低薪的工作而勉强度日。中国人首先在金矿里找到工作,到1860年,70%在加州工作的中国人都是矿工。大多数人独立工作,但有些人则自发组建小公司。只有少数人找到了黄金。另一些人则通过在矿区开设餐馆和洗衣店来养活自己。在美国西部的其他州,中国人也有分布。在每个地方,他们都遭受了极大的敌意。白人对他们在金矿区的大量人数和竞争感到不满。骚扰、抢劫和暴力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中国人试图在与世隔绝的地方工作,以避免冲突。
几十年来,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了。在铁路、工厂、罐头厂、渔业和田野上,来自中国的工人很快就变得不可或缺。1869年,美国《阿尔托加州日报》(Daily Alto California)赞扬了中国移民在发展国家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记者指出:“中国人民是耕者、洗衣工、矿工、羊毛纺纱工和纺织工、家政用人、雪茄制造者、制鞋商、铁路建设者,为本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西部的铁路公司是中国劳工的最大雇主。1865年,第一批中国人受雇于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从萨克拉门托往东铺设横贯大陆的铁轨。公司总裁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称赞中国人“安静、平和、勤奋、节俭”,并正确地认识到“没有他们,就不可能完成这条伟大的国家交通干线的西段”。随着铁路向东推进,联合太平洋铁路正在向西修建,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开始,到犹他州的普拉蒙特利岬(Promontory Point),两条铁路将在这里相接,并最终从东到西连接全国铁路。中国劳工的能干和可靠,驱使中央太平洋铁路的代理人从中国招募了更多的劳工,并支付他们去往美国的路费。到1867年,华人劳工达到1.2万,占全部正在修建铁路劳工总数的90%。
华工清理树木,用炸药、镐和铲子开山劈石,清理碎石,铺设铁轨。内华达山脉崎岖的山峰“挤满了中国劳工,铲、挖、钻、爆破岩石和泥土”,一位观察人士说。这项工作既困难又危险。许多中国人死于1866年的冬天,当时暴风雪袭击了建筑工人,并将他们困在雪堆之下。另一些人在爆破炸出隧道时丧生。一家报纸估计至少有1 200名中国移民死于修筑中央太平洋铁路。
1867年,有5 000名中国人进行了罢工。他们的工作时间更长,所获得的薪水却更少。他们宣称:“白人每天工作八小时,中国人也要同样的待遇。”铁路大亨查尔斯·克罗克(Charles Crocker)的回应是切断了矿工的食物供应。他们被孤立在山区的工作营地里,遭受着饥饿,罢工者最终屈服了。最后的侮辱发生在1869年5月10日,当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普拉蒙特利岬会合,敲入最后一颗道钉时,那些使之得以实现的中国工人却没有出现在官方庆祝典礼的照片中。
华人和其他亚洲人也被大量征召到夏威夷群岛上收获甘蔗(就像他们在加勒比地区一样),在整个19世纪,那里的糖就是国王。从1850年到1920年,有30多万亚洲人来到夏威夷。最先到达这里的,是由夏威夷皇家农业协会的种植园主所招募的华人。在19世纪50年代有700人来到这里。1875年到1887年间,又有25 497名中国人来到这里。到1890年,华人几乎占了这些岛屿总人口的19%。不像中国劳工在古巴的甘蔗种植园,中国人在夏威夷工作,虽然签有合同,但并非契约劳工。他们称夏威夷为“檀香山”(Tan Heung Shan)。糖种植园主称赞中国人“闻铃而起,工作踏实,学习迅速”。他们鼓励更多的中国人来到这里并留下。但中国人另有想法。绝大多数人在合同到期后离开了种植园,改种水稻、咖啡、香蕉和芋头,并饲养牲畜。许多人在城镇和火奴鲁鲁找到机会。另一些人则彻底离开了这些岛屿,前往美国的其他地方。
1869年之后,美国西部铁路建设工作枯竭,数千名华工涌入旧金山,在那里,他们帮助扩大了该市新兴的制鞋业、纺织业和雪茄行业。到1872年,在工厂工作的工人中有将近一半是中国人。他们的工资很低,在与白人一起工作的商店里,工资比白人低。在19世纪70年代,中国与白人工人进行不公平竞争的指控将成为反华运动的核心话语之一。
对中国移民劳工的需求不仅在美国西部。华人也被招募到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的制鞋厂,以及南部种植园去工作。到1880年,在新奥尔良和密西西比州都有小规模的华人社区。在种族隔离的南方,华人占据黑人和白人中间“部分有色人种”的地位。相对于非裔美国人,他们有更多的行动自由和其他权利,但从未作为与白人平等的一群人而被接受。
在加利福尼亚,中国人也从事农业。在萨克拉门托—圣华金河(Sacramento-San Joaquin River)三角洲,他们被雇来建造灌溉管道、堤坝和沟渠。他们在齐腰深的水中工作,把沼泽地里的水抽干,把它们变成这个国家最肥沃、最高产的农田。中国移民还修建道路,清理土地,进行种植、耕耘,并为纳帕和索诺马山谷的葡萄酒产业供应葡萄。他们种植柑橘类水果、豆类、豌豆和甜菜,在自己的小农场里种植土豆、蔬菜和水果,并将产品运送到城市和小城镇。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萨克拉门托—圣华金河三角洲地区的中国人口中,95%的人都是农民、农场工人、水果包装工,其他人也从事与农业相关的职业。历史学家凯里·麦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指出,在使加利福尼亚农业转型成为可能的过程中,“华人是关键因素”。但工资不平等也伴随华人进入这一领域。他们每月的工资比白人少10~20美元。
在从事农业的华人中,有两位园艺家帮助改变了这个行业。其中一个是阿炳(Ah Bing),他在俄勒冈培育了著名的“炳氏樱桃”。另一个是佛罗里达的刘锦浓(Lue Gim Gong),他成功地种植了一种美味多汁的橙子,可以大量运往全国各地。1911年,“刘锦浓橙”赢得了美国果树学会的杰出奖章。他接着以几种不寻常的植物嫁接,培育出了一种新的葡萄柚品种。当刘锦浓于1925年去世时,他以“柑橘奇才”而闻名,并以此来纪念他在佛罗里达的柑橘行业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到20世纪初,华人移民已经扩展到西部和中西部、东北部、大西洋中部和南部的大城市和小城镇。通常情况下,他们通过经营小本生意来维持生计,尤其是洗衣店、餐馆或商店。1920年,加州48%的华人从事小生意。尽管行业类型集中,但这些生意绝不是中国传统职业。洗衣工李周(Lee Chew)在1906年解释道:“华人洗衣工不了解中国的这一行业,中国没有洗衣店。那里的妇女们在浴缸里洗衣服,没有洗衣板或熨斗。”华人也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工作。当然,作家和活动家王清福(Wong Chin Foo)在1888年解释道,中国人成为洗衣工,“仅仅因为没有其他职业可以稳定快捷地赚钱”。
这应该从一个名叫李华(Wah Lee)的人开始讲起。1851年,他在旧金山的杜邦(Dupont)街和华盛顿街的拐角处,挂了一个“清洗”和“熨烫”的标志。由于在加利福尼亚的淘金潮中,几乎没有女性,也没有任何族裔背景的洗衣女工,这个城市面临着严重的洗衣工短缺问题。洗涤和熨烫一打衬衫要价8美元。清洁衣服的花费一度太高,以至于有些人把他们的衣服打包运往檀香山清洗,即便如此也比在旧金山的花费要便宜得多。唯一的缺点是,他们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把干净的衣服拿回来。李华和其他人抓住了一个机会。到1860年,加利福尼亚有890名华人洗衣工人。10年后,据统计大约有3 000名华人以洗熨衣服为生。
中国餐馆也有类似的起源。淘金热时期,加利福尼亚少有女性,甚至更少的男性愿意专为他人做饭。就像创业者李华一样,中国移民抓住机会,为维持生计而在矿地营做厨师,经营小餐馆。到20世纪初,餐馆是许多移民家庭的经济支柱,他们为全美各地的非华人开办了炒杂碎餐馆。
随着中国人移居美国,中国的洗衣店和餐馆也在美国四散开来。由于种族歧视,中国被迫放弃了其他工作,从事自我雇用、族裔经济和其他无人问津的工作。而且中国移民也满足这两种行业的需求。它们既不需要专业技能,也不需精通英语或受过良好教育,生意可以单独经营、小家庭经营或较大规模的群体合伙经营。而且,它们在许多城市和城镇成了有利可图的生意。李周起初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铁路营地开设洗衣店,19世纪80年代他同其伙伴被抢并被逐出小镇,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州。当到达芝加哥的时候,他自食其力,重开洗衣店,此后先后搬到底特律、布法罗和纽约,在这些地方,他都开办了洗衣店。
这项工作很困难且耗费体力。波士顿的洗衣工人董博秦(Tung Pok Chin)记得,他的工作从早上7点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2点,“夜以继日,每周六天”。他和洗衣店中其他五名工人直到凌晨两点才在洗衣间吃晚饭,两点半睡觉,只剩下四个半小时的睡眠时间。尽管如此,在美国的工资还是比大多数人在中国挣得多。在20世纪20年代生意良好的一周,一个洗衣工可以挣到50美元。如果他节俭的话,这些收入通常可以养活他在中国的家人。一个有进取心的洗衣工可能最终会拥有自己的生意。社会学家保罗·苏(Paul Siu)发现,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经营一家洗衣店的投资相对较低,约在2 800~3 000美元之间。
通常在远离其他中国社区的小城镇里的洗衣店和餐馆工作很长时间的华人移民,开始向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中国城汇聚。美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华人社区,即旧金山及其中国城——也被称为“大埠”——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华人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在淘金热期间,城市里一个熙攘的华人聚居区出现了,其中包括商店、餐馆、旅店和肉店、草药铺和裁缝店。到了19世纪70年代,华人区囊括了6个街区,从加利福尼亚街一直延伸到百老汇大街。到1900年,加州45%的华人都生活在旧金山湾区。大多数中国移民和中国货物通过旧金山港进入美国,在那里,人员和物资分散到美国各地,以及北美的其他地方和南美。
旧金山的唐人街也是许多提供支持和互助组织的所在地。这些组织让华人在美国的生活更加轻松,包括兄弟组织、政党、商会、秘密社团、地区组织和工会。“方氏”(Fongs)是家族组织,以协助在美国的家族成员,其意是“房子”或“房间”。“方氏”是俱乐部的会所,扮演着旅店与社区中心的角色,其成员可以在这里会面,交换新闻,收发信件,并安排将遇难亲属的遗体运回国内。“堂会”(兄弟会或组织)是围绕兄弟宣誓忠诚而成立的组织,并沿袭了帮会或三合会的模式,它们是为了反对清朝在中国的统治而成立的。这些组织还帮助移民找工作,共享经济资源,并提供其他形式的互助。随着它们的成长和扩张,堂会的活动也延伸到鸦片、赌博和卖淫行业,这些都是男子单身社会的常见恶习。
在堂会和“方氏”之上的就是会馆,或者是基于移民来源地的组织。在旧金山,第一批中国移民形成了与珠三角地区相关的六个地区性组织。后来,这些组织联合在一起,形成了“六大公司”,这一组织成了华人在美国的代表,解决地区间冲突,提供法律、教育和卫生服务。最终,它还从旧金山管理位于加拿大和拉丁美洲的海外分支机构。
这些组织可能提供了在美国及北美其他地区和南美中国社区的社会和经济支柱,但对大多数中国移民来说,旧金山的中国城简直就是故乡。在这里,他们可以讲自己的母语,吃最爱的食物,囤积日用品和中国食物,拜访家人和老乡,同时听闻来自故乡的消息。在他们的休息日,华人男性移民们会在唐人街的街道上漫步,或者在朴茨茅斯广场(Portsmouth Square)集会。在那里他们可以饮茶,阅读墙报上关于中国政局的最新消息,美国移民法的变化,以及社区公告。晚上,他们可能会去赌博或看戏,逛庙会和妓院。正如一位中国城居民在20世纪20年代告知采访者说:“我们大多数人在亲朋之间比在陌生人之间过上更加温暖、自由,更加人性化的生活……只有在中国城,一名华人移民才有社会、朋友和亲戚,同他们分享梦想和希望、艰辛与冒险的经历。”随着华人迁徙至全州以及整个美国各地,其他中国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诸如萨克拉门托、明尼阿波利斯等城市,以及如蒙大拿的巴特(Butte)这样的城镇。此外,在芝加哥、波士顿、圣路易斯、费城和纽约等大城市,中国城也在进一步发展。
例如,在1880—1890年之间,纽约的华人数量增加了两倍,达到2 000多人,其中大部分定居在曼哈顿下东区的五点(Five Points)社区。第一个抵达纽约的华人是水手。到19世纪50年代,华人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大的社区,他们从事街头小贩、雪茄制造商、洗衣工人、厨师和餐馆老板,以及经营中国食品杂货店的工作。尽管社会改革家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称中国人是“我们当中无家可归的陌生人”,但在纽约,华人正忙着建设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其中包括有效的社区机构、家族和组织。
一些华人移民同爱尔兰移民妇女结婚,比如著名的“中国佬典范”奎波·阿波(Quimbo Appo),他是一名茶商,出生在上海东南部沿海的舟山岛,会说英语。该岛经常有西方的鸦片贸易商造访,很可能是通过他们在1847年的一艘船,阿波才能安全地抵达加利福尼亚(当时尚属墨西哥领土)。从那里,他作为律师和乘务员乘船到波士顿。在纽黑文,他遇到了一个名为凯瑟琳·菲茨帕特里克(Catherine Fitzpatrick)的爱尔兰女人。他们搬到了纽约,在下曼哈顿的一家茶叶店工作。当他们的儿子在1856年7月4日出生时,他们给他起名叫乔治·华盛顿·阿波。到19世纪60年代,这种华人与爱尔兰人结合的婚姻非常普遍,以至于《纽约论坛报》评论道:“这些华人对凯尔特人血统的妻子有着特殊的幻想。”
莫特(Mo)街是纽约中国城的中心,其间挤满了旅馆、家族组织、杂货店、草药铺和餐馆。虽然其他移民群体,包括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和犹太人,最终离开了现在中国城所在的社区,但华人留下了,而纽约的中国城仍然是世界上最大、最具活力的中国城之一。
尽管中国城的街道上到处都是活动,但历史学家杨碧芳(Judy Yung)解释说,中国家庭里的中国移民女性往往“在中国城内受父权控制,在中国城之外受种族主义的束缚”。早期的移民妇女——包括在社会和经济阶梯一端的妓女,以及在另一端的商人的妻子——依然过着受限制的生活。她们通常不会说英语,被其丈夫、父亲以及中国和美国社会的男权价值观所限。一位中国移民妇女抱怨道:“可怜的我!在中国,我从10岁起就被关在家里,后来离开我父亲的房子,又被局限在我丈夫在美国的房子里。17年来,我一直待在这所房子里,没有让它空闲超过两个晚上。”
到20世纪初,来到美国的妇女们发现她们的生活受到了中美女性角色地位形势变化的影响。她们开始自我教育,在外面工作,参加社区活动,并开始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美国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随着在中国的华人女性成为“新女性”,在美国的华人女性亦然。
1902年,华人学生和社会改革家谢晶晶(Sieh King King)站在拥挤的旧金山人群面前,提出解放中国妇女是中国解放的关键的思想。作为中国改革运动的忠实信徒,这一运动认为现代化是中国摆脱外国统治的一种方式。谢晶晶创造了历史,她是中国第一个向旧金山中国城介绍女权主义思想的华人女性。正如《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报道的那样,谢晶晶“大胆谴责了奴役女孩的制度,对缠足的罪恶怒不可遏,并主张男女平等,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
其他中国移民妇女受益于世风的改变,以及为妇女提供的新的教育和就业机会。在华人移民简·邝·李(Jane Kwong Lee)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的时候,还很少有女性追求高级学位。她继续负责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的项目计划,即为妇女提供英语课程及对移民、就业、教育和家庭问题进行援助。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简·邝·李在旧金山不同群体、不同代际的华人女性之间,华人社区和非华人社区之间,以及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充当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纽带。
中国的移民妇女也同她丈夫一起在华人餐馆、商店和洗衣店工作,或者在工厂、罐头公司和其他企业工作以挣得工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女性已经主导了旧金山的服装业。一些移民家庭也接纳寄居者作为增加收入的一种方式。在这些家庭中,为额外的家庭成员准备食物和清洁卫生则是妻子的职责。由于对家庭主妇和工薪劳工双重职责的驾轻就熟,中国女性是其家庭在美国的经济生存斗争中不可或缺的搭档。
移民法同样禁止或阻止中国女性移民到美国,从而减缓了中国家庭在美国的增长。在美国和中国有如此多家庭分裂的情况下,许多华人社区里妇女和儿童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不多见。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女性成为商人和美国公民的妻子(成为女儿的较少),妇女和儿童在全美各地中国社区的街道上变得更加常见。1900—1940年,在美国出生的华人人口翻了两番。
华裔美国人家庭学会了将中国的文化习俗适应于新的美国环境。在中国传统中,小孩出生,人们通常会庆祝小孩“满月”以及出生后100天。但新生儿同样在天主教和新教教堂里接受洗礼。家庭庆祝中国春节和7月4日美国独立日。孩子们通常起中国和美国两个名字,这标志着这个家庭与美国联系得越来越紧密。帕迪·刘(Pardee Lowe)的父亲以加州州长的名字给他起名。他的兄弟姐妹分别起了美国总统、副总统及他们妻子的名字:伍德罗·威尔逊、托马斯·赖利·马歇尔、海伦·塔夫脱、爱丽丝·罗斯福和梅布尔。
家庭生活常常围绕着家族企业和学校展开。早上,孩子们去公立学校上学,如旧金山的东方公立学校,然后在下午去中文学校,在那里学习汉语,年长的孩子还要学习中国历史和经典。宗教社会服务机构如旧金山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Chinese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YMCA)和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还为男孩提供机会学习音乐、篮球、英语、汉语和机械制图课,为女孩提供英语课、缝纫、钢琴和烹饪课,以及乒乓球和羽毛球等体育休闲课。晚上,孩子们则在家里的餐馆和洗衣店干活,如洗碗、做饭、熨衣服。
和其他移民群体一样,在美国出生的第二代华人移民引发了成为美国人的新途径。学习英语是华人学会适应美国生活的一种方式,许多华人移民依赖英汉双语会话书籍。一个常见的版本是1888年版,其重点是“在美国的中国居民的日常和相关问题的对话”。其中有会见朋友部分,在邮局办理业务部分,在洗衣店服务客户部分,获得厨师或服务员工作部分,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和处理移民问题部分,这个会话书提供在生活中可能会用到的基本英语沟通技巧,如:“这是去邮局的路吗?”“您能告诉我第五大道第10号在哪里吗?”“先生,我听说您需要一名服务员。”短语书籍还揭示了中国人所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其他经历,比如:“他从我这里抢走了它”“他被一个强盗用套索勒死了”“她是个废物”。
华人移民还通过改变他们的衣着、饮食习惯和社会习俗,以适应美国生活。一些华人与白人、美国原住民、墨西哥人、夏威夷原住民、非裔美国人妇女结婚,并在允许的情况下融入当地的非华人社区。他们皈依基督教,换了名字,还有一小部分华人移民即使在联邦排华法律下也成功地归化为美国公民。但华人成为美国人,也有赖于他们利用美国的平等价值观反对歧视,并利用美国司法体制试图推翻歧视性法律。
少数华人为确保华人在美国的平等所做的努力,影响了美国的法律史。1884年,玛丽(Mary)和约瑟夫·泰普(Joseph Tape)试图在旧金山的春谷学校(Spring Valley School)给他们的女儿玛米(Mamie)注册。根据加州教育法规,允许学校将“肮脏、有恶习,或有传染性疾病的儿童”排除在外,学校官员和旧金山学校董事会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学校董事会将所有华人孩子描述为危险人物或患病者,并利用这一法规来维持在公立学校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泰普一家发动了一场争取获得平等教育机会的法律战。在一封写给董事会的抗议信中,玛丽·泰普写道:“我注意到你们将会寻找各种借口,以将我的孩子排斥在公立学校之外……难道生为华人是一种耻辱吗?难道不是上帝创造了我们所有人吗!!!正义何在!难道你们将我的孩子排斥在校门之外不正是因为她是华人的后裔吗?”泰普一家最终起诉了旧金山学校董事会,并认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玛米有权享受每一个美国人与生俱来的免费教育。旧金山一名高级法院法官同意了这一说法,但旧金山学校董事会拒绝让玛米与白人一起上学,而是在中国城地区建立了一所独立的华人小学。虽然这并不是泰普一家所乐见的结果,但在1885年4月学校开学时,玛米和她的弟弟弗兰克(Frank)是最初两名出现在学校课堂上的学生。泰普一家对法律的挑战,确保了华人儿童在美国有接受公共教育的权利。
1898年,最高法院的裁断,确认了所有出生在美国者的出生公民权的宪法地位。黄金德(Wong Kim Ark)是土生土长的华裔美国公民,他是一名厨师,也是土生土长的旧金山人。1894年24岁时,他在访问中国后返回加州。令他惊讶的是,他被拒绝重新进入美国。美国海关负责移民处理的官员约翰·怀斯(John Wise)声称,他虽然出生于美国,但并不是一个公民,因为他的父母都是中国公民,在《排华法》之下,他们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怀斯自称是“积极反对华人移民”的人,试图尽可能广泛地利用排斥法,将第二代华裔美国人也包括在内。怀斯命令黄金德“返回”中国。
黄金德和他的律师用人身保护令对这一认定提出质疑。他声称,根据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他有权根据他作为美国公民的身份重新进入美国。法院的问题是:美国是如何确定公民身份?根据出生地还是血统?加州北部地区法院为黄金德做出了裁决,但美国律师对这一判决提出上诉。1897年3月,美国最高法院就此案进行了辩论。在法官霍勒斯·格雷(Horace Gray)的多数意见中,法院裁定黄金德胜诉。美国诉黄金德案表明,无论何种种族,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都有权享有公民的所有权利。
其他在美国的华人,像作家兼活动家王清福也利用公共领域挑战美国的歧视。1847年出生的王清福,在20岁时跟着一名美国女传教士来到美国,该传教士同其后来的丈夫一道,在中国照顾家道中落的王清福。王清福进入华盛顿特区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学校学习,此后返回中国结婚成家。但当他开始批评清政府时,他被驱逐出中国,并于1873年返回美国。第二年,他归化为密歇根州大急流城(Grand Rapids)的美国公民。(联邦法律禁止归化亚裔移民,但在1882年明确规定华人不得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排华法》颁布前,这些法律并没有严格地在美国强制执行。)王清福在美国各地发表了有关中国和美国华人的演讲。随着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反华运动的发展,他为华人社区进行了辩护,攻击反华领导人丹尼斯·科尔尼(Denis Kearney),并在纽约创办了第一家华文报纸——《华裔美国人报》。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在1892年成立了“华人平等权利联盟”(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并持续地反对《排华法》,包括1893年在美国国会做证(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华人)。他明确地表达正义的声音。王清福的平等权利联盟在1892年上诉中说:“我们宣称与所有其他族群具有同样的男子汉气概,根据共同人性和美国自由的原则,我们认为我们的男子汉气概应当被承认。”在1898年去世之前,王清福一直在争取华裔美国人的公民权利。
图8.尽管1898年最高法院确认了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无论种族皆享有出生公民权的权利,但黄金德仍然被视为一个不平等的美国公民。就像所有的华人移民和华裔美国人一样,他不得不一直带着这种身份证件(1914年)来证明自己在美国的合法居住身份。
华人在美国争取平等之时,也在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华文报纸《中西日报》在1900年解释说,由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弱势地位变成华人在国外的弱势地位,这两种运动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19世纪后期,欧洲和美洲列强继续以不平等的条约和领土扩张欺凌中国。清廷因软弱而无力反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主张改革,从传统的帝国体制调整到彻底的革命,再到以共和国取清帝国而代之。由于他们的颠覆性观点,改革者和革命者在国内被禁,便到国外争取财政和政治上对其事业的支持。他们找到了热情的拥护者。
孙中山是一位华人基督徒,曾在夏威夷求学。他是在海外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活跃的两大主要政治组织的领导人。在夏威夷华人中产阶级的帮助下,他于1894年在夏威夷成立兴中会,向西方世界的华人介绍中国革命运动。1905年,他在日本将数个组织联合在一起成立了同盟会,并以民族、民主和民生为基础,提出了一种更复杂、更详细的革命意识形态。
另一个主要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根据地在北美。1899年,中国皇帝的前顾问、学者康有为来到北美,发表了关于中国帝制改革的演说。他同其学生梁启超及其追随者在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一起组建了保皇会。由于保皇会的重点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因此它颇受欢迎。在其鼎盛时期,还出版了自己的中文报纸《华人世界》(Chinese World),并拥有500万名成员。这些得到南北美洲部分华人支持的改革活动,帮助推动了1911年清王朝的覆灭。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1912年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同盟会与其他政治团体合并,组成中国国民党。在美国的华人继续支持中华民国,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拯救中国,拯救我们自己”,成了漫长战争年代整个美洲华人的战斗口号。
但“拯救”中国和挑战美国的歧视并不容易。不平等继续影响着华裔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学家通过研究美国华人社区发现,华人移民和华裔美国公民遭受着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和“心理恐惧”,其原因是:“在排斥和种族歧视的条件下,华人并没有家的归属感”。由于在美国不受欢迎,也没有成为完全的公民,许多华人移民继续把自己视为这个国家的旅居者,是赚了钱后就可以离开的地方。正如一位芝加哥洗衣店老板所解释的:“我没有其他的希望,只能赚钱,然后返回中国。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在这里你无法成为美国人。”
在美国社会中成长起来并已适应美国社会文化的第二代华裔美国人中,受到歧视的感觉也很强烈,他们渴望在追求教育、职业,以及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美国公民的潜力。但在更大的社会里,种族主义将其中的诸多梦想摧毁。歧视限制了工作机会,无论他们去到哪里,社会隔离都如影随行。对许多华裔美国女性来说,成为美国人尤其意味着违背父母所期望的传统性别角色。
许多人还发现,他们的公民身份几乎没有保护他们免受歧视。在1913年和1923年,政治家们在国会提交法案,旨在剥夺有中国血统者的公民权。《1924年移民法》明确排除“不符合公民身份的外国人”,目标所指包括所有亚洲人;1922年的《凯布尔法》(Cable Act)规定取消那些嫁给“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的妇女的公民身份,这条法律的主要受害者是那些嫁给亚洲男性移民的美国亚裔女性。一旦一个女人失去了她的公民身份,她拥有的财产、选举权和自由旅行的权利也随即被取消。这项法律直到1931年才得以改变。
华裔美国人失去了对美国的钦佩之情,同时也对疏离感感到沮丧。一名华人向采访者解释说:“我觉得我更像美国人而非中国人。我是一个出生在美国的美国公民,拥有所有权利,但他们像对待外国人一样对待我。”另一人注意到:“我以为我是美国人,但美国并不想要我。在很多方面,她都不认为我是美国人。此外,我发现针对我们的种族偏见无处不在。我们是名义上的美国公民,而非实际上的美国公民。”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华裔美国人才开始觉得自己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 美国百年困局与当下危机(套装共10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