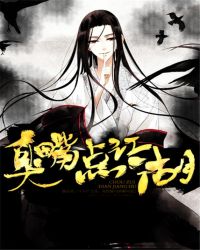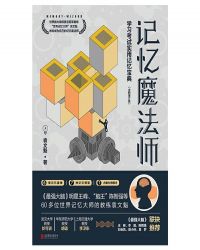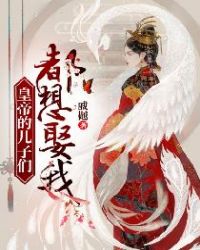3.环境民主与环境威权主义之争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3.环境民主与环境威权主义之争环境民主的理论叙事
关于什么是“环境民主”,现有的文献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在其基本原则和涉及的内容上早已达成了共识。“环境民主”强调的基本原则是保护公民平等的环境权利,追求环境正义(environmental justice),因此政策过程应该更多地体现多中心和参与原则。具体内容包括:(1)政府间纵向和横向权力分享。环境治理的决策权不但在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之间共享,而且在不同政府层级之间共享;(2)国家与社会权力分享。政策制定不应该只局限于政府和企业,还应该包括真正受到环境影响的民众、社区、非政府组织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3)环境治理中不限制公民个人基本的自由权利;(4)当公民的环境权利受到损害时,可以通过司法途径得到有效救济。环境民主理论的倡导者认为民主政治体系下能为实现上述原则提供制度保障,而这恰恰是威权政治体系所缺失的。虽然民主制度下出现的环境问题饱受诟病,但是和威权制度相比,其环境治理的绩效仍不失为一个“更不坏”的选择。
罗杰·佩恩(Rodger Payne)在“Freedom and the Environment”的文章中,代表了对环境民主理论坚定支持者的观点。他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为什么民主制度能够更好地保护环境;要想保护环境,应该先发展民主。第一,个人权利的保护和思想市场的开放性。民主国家压制环保主义者的个人权利,限制他们批评政府的抗争活动的可能性较小。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形成了开放思想市场和信息的高流动性,来自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科学界的不同观念的沟通、交流和辩论有利于环保主义者表达声音,提高公众的环保意识。自由结社权利让环保主义者凝成行动的力量,影响决策。第二,政府的回应性。选民可以通过手中的选票来支持更加重视环保的政党,比如德国的绿党。听证会等民主程序为公众参与提供了渠道。第三,民主政府的学习能力、实验能力和创新能力高于威权政府,环保知识和科技的创新能力更强。第四,国际主义。民主政府更支持国际组织的工作,愿意通过合作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比如《蒙特利尔公约》的实行。国际环保组织能够帮助主权国家改善环境标准,增加环境投入。全球性环保非政府组织在民主国家更容易发展,民主国家更能够接受全球公民社会的批评。第五,开放市场。开放市场环境下的私有产权和自由竞争市场常常被批评为环境危机的根源之一,但实际上,那些没有实行开放市场国家的环境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前东欧和苏联。民主国家在环境治理中运用了一些有效的市场激励机制,比如碳排放交易制度。在一些民主国家,环保产业发展得更好,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
玛格丽特·温斯洛(Margrethe Winslow)在“Is Democracy Good for Environment”一文中总结了支持环境民主理论的主要观点:第一,政治领导人的责任性使得他们个人从环境破坏中获益的情况很难实现。第二,公众参与决策过程增加了环境问题被发现和解决的可能性。第三,信息公开和透明有助于民众环境意识的提升。第四,非政府组织的存在能够帮助民众获得更多信息,监督政府部门,直接游说政策制定者。第五,民事诉讼权有助于环境保护法律的执行。第六,从国际层面看,民主国家之间在环境信息和具体管制措施方面的信息交换频繁,制定一些国际公约应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相反,威权国家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他们比较容易以牺牲环境来谋取自己的利益;信息封闭或流通不畅;出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而限制在环境保护上的长期投入。在温斯洛看来,环境民主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很多形式的环境破坏都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需求和利益而损害大多数人的权益;民主政治系统内的权力分离和共享有利于克制少数人对环境的破坏。民主环境理论不否认威权政体在处理环境恶化方面采取的行动,但认为从总体上说,威权政体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要比民主政体差很多。
其他一些支持民主环境理论的观点还包括:(1)民主政体的法治传统能够保证其更好地履行环境国际公约;(2)民主政体更尊重人的生命,对涉及威胁人类生存和健康的环境问题更关切;(3)战争破坏环境,民主国家国内的战争较少,因此,应该有更好的环境;(4)饥荒破坏环境,民主国家没有发生过饥荒,因此,应该有更好的环境。
环境民主的经验验证
环境民主理论的大量文献都不只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应然”描述和预测,而是以实证的方法回答一些经验性的问题。这些具体的问题包括:民主政体的环境绩效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民主政体是在所有的环境问题上都有较好的绩效,还是有必要详细区分不同的环境问题(水、大气、土地荒漠化等)?民主政体是否在某些环境保护方面的绩效(比如控制城市大气污染)好于另外一些方面(比如节约能源和自然资源保护)?如何解释民主程度处于同一水平的国家,其环境保护绩效却各有不同;如何解释一个民主国家在不同时间段内表现出的不同环境绩效;究竟是民主政体内的哪种具体制度或政治过程更能影响环境治理结果?
验证民主与环境绩效相关性的经验研究的最初问题意识来自于普林斯顿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吉恩·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和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于1995年提出的著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这个倒U型曲线显示随着人均GDP的上升,环境破坏的程度也会上升,但是当人均GDP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拐点就会出现,环境开始好转。但是这个研究没有解释倒U型曲线存在的背后原因。一种不言而喻的预设是,当一个国家的民众变得越来越富裕的时候,他们的非物质性需求便开始增长。但这种需求的满足需要依靠一些政治因素:(1)民众有能力获得环境方面的信息;(2)政府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去改变原来的政策,以满足民众需求偏好的转变。
斯科特·巴雷特(Scott Barrett)和凯瑟琳·格雷迪(Kathryn Graddy)的研究代表了最早尝试使用不同的政治性变量去验证这个假设的研究路径。在“Freedom,Growth,and the Environment”一文中,他们要验证的问题是:更多的自由对环境保护来说是好还是坏?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悬浮颗粒和烟雾与该国的公民和政治自由成反比。但是,和空气质量不同,水环境质量与公民和政治自由不总是成反比。水中的化学需氧量、硝酸盐、总大肠杆菌群会随着公民和政治自由程度的升高而升高,但铅、铬等重金属含量与自由程度成反比。作者的结论是,更多的自由有利于保护环境,特别是在空气质量这样直接和民众健康息息相关的环境问题上。这项研究的理论引申之一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背后的预设是成立的,即政府为了选举的需要会根据民众需求偏好的转变而及时调整政策。
佩·弗雷迪克森(Per Fredriksson)等人以82个发展中国家和22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哪些具体的政治力量能够影响政府的环境决策。他们的研究发现:(1)环保组织(游说集团)数量的增多可能降低汽油中铅的含量;(2)公民的民主参与本身对环境政策没有影响,但是选举政治竞争的强弱能够影响汽油中的铅含量。在没有充分选举政治竞争的政治体制下,民主参与不能影响环境政策结果。
李泉(Quan Li)等人研究了政体类型与六种由人类活动直接产生的环境破坏之间的相关性,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氮氧化物排放、土壤破坏、土地荒漠化和用于衡量水质的化学需氧量指标。结果显示:以上六项指标与民主政体都有显著相关性,更民主的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人均氮氧化物更少,化学需氧量排放也更少;更民主的国家,其土壤破坏和土地荒漠化率的程度更低,但是森林覆盖率更高。但是,民主程度对这些环境指标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对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化学需氧量排放的影响要小于对人均氮氧化物、土壤破坏和土地荒漠化率的影响。
埃里克·诺伊迈尔(Eric Neumayer)的研究验证了民主政体比非民主政体有更强的国际环境承诺的假设。他选取了六组代理变量来测量一国的国际环境承诺水平,分别是:签署和批准国际环境公约,参加国际环境组织,按照《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要求汇报本国情况,列入保护范围的土地面积的比例,在国家政府层面设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这样的机构,环境信息的公开。结果显示,民主政体与上述六组变量都成正相关。
对环境民主理论的批判
尽管大多数的环境政治学文献的研究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阐释、论证或验证了环境民主理论,但是对环境民主理论的批评也非常引人注目。这些批判性观点认为民主制度在应对环境问题上存在很大缺陷,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1)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保护可能导致对资源和环境的无限制开发,比如对于生育权利的绝对保护可能造成人口膨胀,进而威胁到全人类的生存。(2)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造成的美国式“消费主义”崇拜是导致资源和能源浪费的经济根源之一。(3)私人产权制度下,“经济人”的利己主义行为,可能造成“公用地灾难”;环境公共物品的“外部性”特征造成的市场失灵难以通过经济激励的方式来进行环境治理。(4)以争取选票为目的的政客可能为了获得选举的胜利而迎合那些追求短期眼前利益选民的需要,放弃长远的环境利益。(5)尽管信息公开,但普通民众对充满专业性知识的环境问题不一定能很好地理解,因此过多的公众参与可能造成效率低下。(6)政策的制定过程常常被工业界强大的利益集团主导,环保组织的资源和力量不足。(7)民主的有效范围只限于主权国家内部,但是,大多数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
一些经验研究的结论也支持对环境民主理论的批判,认为民主一定有利于环境治理的主导性观点需要修正。马努斯·米德拉斯基(Manus I.Midlarsky)的研究认为,土地荒漠化、二氧化碳排放和水造成的土壤腐蚀这三项环境指标都与民主成负相关性,洁净水供应和由重金属造成的土壤腐蚀两项指标与民主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莱尔·斯克鲁格斯(Lyle Scruggs)认为,前东欧和苏联政治转型之后在环境治理上取得的成就是经济发展变化的结果,与政治自由化没有相关性。但他也承认他的研究不能证明民主政体对环境治理有副作用,只是提醒人们不要迷信那种想要好的环境就应该尽快推行民主化的观点。
值得强调的是,对环境民主理论的批判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理论结果。一方面,有些学者以批判为基础,想办法在民主制度体系内部进行修补以克服那些不利于环境治理的因素,例如协商式环境主义(Deliberative Environmentalism)等概念的提出。格雷厄姆·史密斯(Graham Smith)等人认为应该将协商民主与环境治理结合起来,弥补选举民主出现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则有学者出于对民主制度在环境治理上的不满,开始寻找替代性方案,环境威权主义的概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由此可见,环境民主理论的批评者不一定是环境威权主义的支持者,但他们的研究结果可以被环境威权主义的支持者用来挑战环境民主理论。
环境威权主义的理论叙事
在环境政治学中,“环境威权主义”与“环境民主”是一对相对立的理论模式,是在批判后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替代性理论方案。其核心观点是:为了更好地应对主权国家内和全球的环境危机,威权主义可能比民主更有效,甚至需要产生一个威权主义政体。这些威权主义的特征包括:(1)限制公民个人的自由,特别是那些可能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行为;(2)限制环境决策中公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而是依靠一些“生态精英”(eco elites)和环境专家来作决定;(3)更多地实行中央集权,限制地方、企业和社会力量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4)在环境治理中更多地采用政府管制而不是经济和市场的激励机制。
环境威权主义的理论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的美国,代表人物是罗伯特·海尔布隆(Robert Heilbronner)和威廉·欧弗斯(William Ophuls)。在《追问人类的前景》(An Inquiry into the Human Prospect)一书中,海尔布隆悲观地认为需要依靠一个环境独裁者式的中央集权政府采取大规模的强制性手段,否则人类将陷入因为争夺资源所引发的环境灾难之中。这些强制性手段包括:控制人口,对资源和能源实行配给制,暂停公众的政治参与,由政府接手私人经济和财富的分配等。欧弗斯在其著名的《生态与稀缺的政治》(Ec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Scarcity:Prologue to a Political Theory of the Steady State)一书中指出,自然资源的匮乏是这个世界的物理本质,一个稳定的政府就是要有秩序地分配这些匮乏的资源。为此,需要制定类似“生态社会契约”(ecological social contract),要取消一些公民自由和政治对市场经济的服务。
2000年以来,随着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加剧,环境威权主义的声音又开始重新出现。大卫·希尔曼(David Shearman)和约瑟夫·韦恩·史密斯(Joseph Wayne Smith)在《气候变化的挑战与民主的失灵》(The Climate Change Challenge and the Failure of Democracy)一书中提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环境问题,理想的模式是威权式的精英统治(meritocracy),需要一个开明的、利他的、任人唯贤并具备美德的统治者。但他们也同时意识到现有的威权政体的环境治理能力并不比民主政体高。澳大利亚学者马克·比森(Mark Beeson)的最新研究预测,在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环境恶化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威权统治的发展和加强,因为政治精英认为维护政权和内部稳定比政治自由化更加重要。应对环境挑战的努力可能涉及个人自由的减少,因为政府试图转变人们那些环境不友好的行为。结果就是,在这个对未来预期越来越悲观的时代,能够禁止环境不可持续行为的“好”的威权主义——“环境威权主义”可能成为越来越普遍的选择,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消极作用。
环境威权主义的经验验证
与环境民主理论的经验验证明显不同,支撑环境威权主义观点的经验研究极为有限。现实中,支持威权主义政权与环境治理绩效成正相关的经验研究很少。有一些研究认为低质量的民主制度或者民主化的过程可能对环境治理造成消极影响,因为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要面对众多矛盾的需求,可能缺乏足够的国家能力来应对环境问题。但是,汤京平和邓穗欣对台湾民主化转型之后政府在沿海地带治理地下水超采和土地沉降问题的研究表明:在民主化转型的初期,政治系统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确实面临更多的困难,但是,从一个长时间段来看,民主化有利于政府处理更加复杂的环境问题,因为民主政治的参与性和整合性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环境治理能力。
中国政府采用的环境治理模式被认为是环境威权主义的一个代表。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的控制效果,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环境威权主义。但是,环境威权主义的质疑者认为环境威权主义的优势在于短时间内对环境危机作出快速的、集中的反应,动员国家和社会的能力较强。但是,由于缺乏社会和地方力量的参与,中央政府作出的政策往往无法得到执行。布鲁斯·吉雷(Bruce Gilley)以中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为例讨论了环境威权主义的意义、原因和结果。他的研究发现,环境威权主义更容易制造政策输出(policy output)而不是具体的政策结果(policy outcome)。萨拉·伊顿(Sarah Eaton)和柯珍雅(Genia Kostka)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频繁更换地方领导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环境政策在地方的执行效果,因为短暂的任期导致他们追求以更快、更简单的方式应对环境问题,倾向于把复杂而棘手的环境问题留给继任者。延续以上的研究脉络,本书将讨论中国环境政治表现出的威权主义特征及其对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的影响,进一步回应以上对于环境民主与环境威权主义的争论。 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