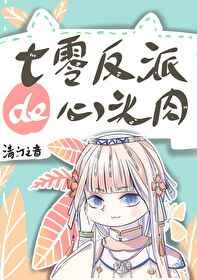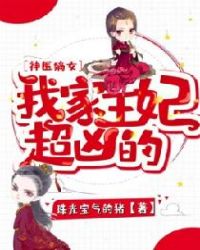2.群众监督还是中央监督?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2.群众监督还是中央监督?
从中央—地方关系的视角看,环境信访是压力型体制下中央控制和监督地方官员的一种手段,环境治理中的地方自主性受到限制。尽管从机构设置上看,环境信访是环保行政部门的一种自我监督。环境信访不是环保部门工作的重点职能,有些基层环保局甚至没有专门的环境信访机构和人员。但是,地方环保部门,特别是基层环保部门承受的环境信访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并不来自于办理自身接待的一般信访,而是疲于应对各种“越级”上访,特别是“进京”上访案件。
环境信访案件包括纵向、横向和斜向三个不同来源。基层环保局的监察机构除自行受理环境信访外,还要接受各级党委、人大、政府信访机构交办和其他职能部门转办的涉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职责,以及依法应由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的信访。例如,江苏省D市某区的环境信访机构(监察科),纵向上受D市环境监察支队(12369环保投诉热线)的业务指导,接受其交办的本区辖区内环境信访,同时将自已受理的地域上跨区或者事务上须市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处理的信访上报。横向上则受区信访局(区长信箱)指导,承办其交办的应由环保部门处理的信访件,同时上报自行受理的涉及其他部门职权或者须区政府协调的信访件。纵横两项并不是环境信访的全部来源,还需处理各级各部门领导下访、接访过程中受理或者日常工作中批示的群众来信来访,以及媒体特别是上级官方媒体曝光的环境信访等。
这些不同来源的信访案件受到的重视程度差别很大。其中,最不受重视的是那些大多数直接反应到本地环境监察机构的合法的、正常途径的信访;最受重视的是那些被认为“非法”的、非正常渠道的“越级”上访案件。有学者对环保局的网络环境信访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虽然大多数环保局官方网站设立了类似环境信访机构的栏目,但大都未正常开通。辽宁省C市一位居民长期向本地环保部门投诉小区周边的粉尘问题,半年多没有得到明确答复。之后不得不在辽宁省纪委的网络投诉平台“民心网”进行投诉,20多天就得到了本地环保部门的答复和处理结果。他表示,以后有问题不再会直接向当地投诉,“还是沈阳好使,最好使的是上北京”。
对于不同来源环境信访重视程度的不同根源于信访“压力型”体制的特点。按照“分级负责、属地办理、就地解决问题”的原则,上级将信访案件层层转交给基层。同时,下级要接受上级层层分解、下达的环境信访指标和任务的考核。上级对下级政府的越级信访量进行排名。在地方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中,“越级上访”的指标一直占有非常关键的份量,是带有“一票否决”性质的维稳类“硬指标”。因此,基层环保局领导对环境“越级上访”案件非常紧张,同时也颇为头痛,采用各种方法降低“越级上访”的数量和人数,转移了其日常环境治理工作的重心和精力。
理论上看,信访的设计初衷应该是鼓励“越级”上访的。信访作为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希望通过这个渠道了解群众“疾苦”,为群众排忧解难。正如应星指出的,联系群众是高层联系群众,基层和群众已经很近很密切了。信访设在基层是失去意义的,越级上访是一种必然。中央允许老百姓越级上访是跨越地方官僚主义这个障碍物获取信息、监督基层的一种方式,“而且也是人民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是政权合法性再生产的一种手段”。中央在宣传中不断展现“亲民”形象,一些老百姓幻想访民希望(幻想)进京上访能够避免地方干涉,一旦拿到某位中央领导人的批示,问题解决效率异常快。
但是,中央又担心源源不断的进京上访带来的社会不“稳定”,自相矛盾地要求地方政府将问题解决在本地,层层控制进京上访成为对地方官员的刚性要求。李连江和于建嵘等学者认为信访制度的功能在于民意的“上达”而非“表达”,成为中央向地方单方面施压的工具。换句话说,中央通过老百姓的信访可以自下而上收集地方信息,并以此来管控和监督地方政府官员,自上而下层层设置和分解信访指标就是这种操控的一个制度化形式。
这种压力型体制下的环境信访模式不利于发挥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动性和自主性,对真正的环境治理来说是缘木求鱼。《环保法》规定地方政府要对辖区内环境质量负总责。为了真正履行这种责任,地方政府需要相应的自主权,在环境治理开展地方性实验和创新。但是,一些地方环保局为了应付“越级”上访的压力,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而这些往往无助于改善地方环境状况。
2011年7月,江苏省D市的环境“越级”上访量有60多件,排在全省第一位。因为受到来自上级排名的巨大压力,环保局领导的工作重心都转向了如何降低排名,减少越级上访量。为此,专门在全市环保系统设立了“环境信访化解月”攻坚活动,采用各种方法在10月份将越级上访数降为30多件,排名全省第四。这些方法包括环保局主要领导亲自“大接访”、“大调解”,重要案件领导包案制度等。在一篇名为“接访就分流,减少信访量,望闻问切四诊法在环境接访中的巧用”的总结报告中倡导要用“切”抓住信访问题的要害,找出解决方法。他们宣传的案例是:某村民的农作物死亡,怀疑是工业区排污管网从承包田中窨井溢出的污水的影响,不断上访,要求赔偿。最后,环境接访人员帮其老婆办理了低保,这位村民就不再上访了。这个越级上访案件就算“圆满”解决了。
需要质疑的是,为什么环保局还要负责为上访者办社保?环保局的责任本来应该是依法查处那些污染源,防止他们继续造成新的环境破坏,这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上访。但是,为了减少越级上访数量,不得不采用一些“旁门左道”。环保局工作人员抱怨到,处理环境越级信访案件时往往出现“有权的部门不处理,没权的部门难处理”,多数只能先治标,很难治本;真正大规模污染,投诉问题一般较复杂,且多涉及工业企业和拉动地区经济的大项目,处理难度较大,很多问题不是环保部门一家能解决的。
于建嵘长期建议改革信访中的这种压力体制,他认为,“中央应该减少对地方党政领导的压力,不按信访量给各地排名,取消信访责任追究制;不对信访公民的信访级别作特别的限制”。“通过减弱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降低群众对信访的预期,会迅速使一些信访案件平息,减少群众进京上访;而给地方政府减压,才能给中央减压,维护地方的政治权威,才能加强和巩固中央的政治权威。”他还清楚地看到,在绝大多数案例中,中央对于上访者的诉求也不能作出满意的处理。极个别成功的个案往往是因“运气”得到了高层的重视,缺乏制度性和可复制性。相反,大量信访案件最后却演化成了“维稳”案件,国家为此付出的成本难以计算。 中国地方环境政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