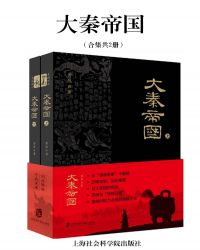盟约在诗诵歌吟背后悄然而成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盟约在诗诵歌吟背后悄然而成在晋国这一次延续近二十年的内乱期间,秦国眈眈虎视于一旁,伺机以武力为后盾施加影响,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人选和方式不断更换晋国新主,史称“三置晋君”。
但晋毕竟也是中原一个大国,兵多将悍,谋士如林,岂肯俯首听命!其间威胁接欺诈,逼约继毁约,忽而杯觥交错于筵席,忽而戈戟搏杀于沙场,呈现了复杂多变的斗争场面。而参与其中的各色人等,在猝然降临的荣辱生死拷问面前,一个个赤裸裸地显露出了自己的人格和人性。
险恶的骊姬与神秘的宝夫人
按照传统历史学家的说法,晋国的这场旷日持久的动乱,又是源于“女祸”。
而且巧得很,也许是纯属偶然,也许是祸福相依、乐极生悲那些古老谶言的反复应验,古代史书上引起灾祸的那些女人,几乎全是凯旋而归带回的战利品。
前面已经提到过三位,她们是——
夏桀征伐有施国,带回了妺喜;
商纣征伐有苏国,带回了妲己;
周幽王征伐褒国,带回了褒姒。
现在要说的是第四位:晋献公征伐骊戎,掠得了骊君的女儿骊姬。
这骊姬生得花容玉貌,美艳绝世。于是,历史上不知重演过多少次的宫廷悲剧便由此开场:先是君王宠幸新妃;接着是新妃在枕头边下功夫:或是要立自己为正,或是要立亲生儿子为太子;随后便是接二连三的互相残杀。
史书对骊姬记载甚多,尤以《国语·晋语》最为详尽。其实把祸乱之罪全推在一两女人身上,显然是男性主导话语权的一种偏面观点,有失公允;不过这个骊姬其生性之阴险和残忍,却确实令人不寒而栗。
晋献公原有八子,其中三子,即已立为太子的申生,和夷吾、重耳,俱有贤行,时称三公子,分别由三个母亲所生:齐桓公之女齐姜生申生,狄之狐氏姊妹生重耳和夷吾。献公幸骊姬姊妹后,又生奚齐、卓子。骊姬想废申生而立亲生儿子奚齐为太子,便百般怂恿献公让三公子远离国都绛城分别出居。但即使这样做了,她还是不死心,又在夜半忸怩作态吞声暗泣,待献公问她,她又故意不胜依恋地说是因为想到自己已无多日能恃君为欢而伤心的。经献公再三逼问,才说出了预先编好的一套话:申生在外如何散布对君上不满,如何说她“惑君乱国”,如何以此为口实将图谋不轨等等。然后珠泪涟涟地哭着说:这件事,朝廷上下都早知道了,只有君上还蒙在鼓里。贱妾一死何惜,最担心的是怕因此而累及君上。所以为今之计,莫如君上亲手杀死贱妾以安申生了!
这确是妖媚女人极厉害的一手,献公哪还有分辨是非能力,一怒之下,便要惩治太子,只是苦于找不到可以服众的罪名。这时骊姬便提出让申生去讨伐皋落狄族,这样败了可以借刀杀人,即使不死也可以此治罪;若是胜了,骊姬以为也可以促使申生因恃功而早起异谋,那时再讨伐自然便会得到国人拥护。
但是申生在攻打皋落狄族中居然不死,而且还取得了很大胜利;取得胜利后又更加敬事献公,恭谨自守。拿不到可以治罪的把柄,就干脆制造一个吧!于是骊姬又使出了更阴险的一计。她谎称梦见了申生已去世的母亲齐姜,要申生在自己居地曲沃祭祀母亲。当申生把祭祀母亲用过的祭肉、祭酒按礼制规定送到绛城来孝敬父亲享用时,骊姬暗中放进了毒堇和毒鸩,并当着献公的面毒死了一条狗和一个小奴隶。这样原本无辜的申生便有了一条十恶不赦的大罪:图谋弑父。有人劝申生应当赶快申辩说明毒药是骊姬放的,申生却说:父亲老了,没有骊姬,他食不甘味,寝不安枕,我怎么能那样做呢?又有人劝申生赶快逃奔他国,他又说:我担着弑父的罪名,人们都把我看作禽兽,有谁还肯接纳我呢?如果我归罪于父亲,那便是张扬君上之恶,必然使晋国见笑于诸侯,我岂非成为叛国罪人了吗?为人子,为人臣,我都不应当弃国亡命!说罢,北向再拜,竟然就这么不明不白自杀死去了!这样的事,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实在难以相信。但《史记·晋世家》却连时间、地点都记得清清楚楚:晋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于新城”。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还作了考证:“申生乃雉经于新城庙。”雉经,就是上吊自杀。这又叫人不得不信!
历代论者大多认为申生死得不值得,但在当时,这或许还被认为是一种崇高的人生信念吧?《史记·卫康叔世家》里还记有卫宣公之子太子伋,几乎在与太子申生相同的情况下自愿死去。稍有不同的是太子伋有个弟弟子寿极为难得,他瞒过太子伋抢先代哥哥去死。但太子伋知道后,还坚持认为“所当杀者乃我也”,硬是又跟着死去。这两出极为相似的悲剧,引起了司马迁很大感慨,他说:
余读世家言,至于宣公之太子以妇见诛,弟寿争死以相让,此与晋太子申生不敢明骊姬之过同,俱恶伤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
的确是何其悲啊!
但骊姬却觉得单害死申生还不够,又诬陷公子重耳、夷吾是下毒弑君的同谋者。晋献公在下达了最后一道荒唐的命令——追杀两个同谋犯即自己的一对亲生儿子后不久,在梦魇似的错乱中突然死去,夷吾、重耳则已分别逃亡到了北狄和梁国。
晋国内乱进入了高潮。文武大臣们围绕着拥立谁为君主的问题展开了生死搏斗。经过激烈、残酷的相互争夺,终于形成了两大派:以大夫荀息为首的一派,坚守“先君遗命”,先后拥立骊姬之子奚齐和骊姬之妹的儿子卓子为君,苦苦支撑了一小段时间。以正卿里克、大夫丕郑等为首的一派,则主张拥立逃亡在外的重耳为君,他们联合可以联合的一切力量,先后杀死了奚齐、卓子和骊姬、荀息等。
晋国在相互残杀中暂时变成了无君之国,国人为此遭受了无穷苦难。但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对一直眈眈虎视于一旁的秦国来说,不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实施东进之策的好时机吗?
偏偏就在这时,秦穆公却生病了,而且一病就是五日不省人事。后来才弄清楚,原来晋乱一起,秦穆公和他的谋臣们就有些迫不及待之感。但如今他们都认定自己是要成就大事业的人了,因而不得不用足够的耐心来捕捉一个最佳时饥。所以穆公那个病,实在全是由既兴奋又焦急,日夜辗转反侧闹出来的!
生病的滋味不好受,但他在病中做的一个梦却美妙无比。先是缥缈如在云际,渐渐又璀璨若临仙境。忽有一少妇美若蟾宫月娥,手握天符轻盈而来,将穆公引至一处,拜于殿下。须臾帘卷,满眼辉煌。见有一王者冕旒华衮,凭玉几上座;左右肃侍,威仪端庄。王者传命赐酒。当即有内侍奉上玉斝(jiǎ),穆公接过,刚一沾唇,已宛若醍醐灌顶。那王者以一简与左右大声宣读道:任好听旨:朕命尔平晋乱,尔其勉之慎之!这样接连宣读了三次,那少妇才又引着穆公出了宫阙。待要离去,穆公已是恋恋难舍,不由转回身去深深一揖,请问少妇姓氏和来处。那妇人道:妾身就是宝夫人,居于太白山之西麓,即在君上之宇下,君上难道没有听说过吗?君上若能为我立祠,妾身当使君上成就霸业,留名万世。
穆公醒来,满朝文武都说这是上天授命于秦的吉兆,穆公自然更加高兴,即日便命人鸠工伐木,在离霸城宫不远的太白山上为宝夫人立祠,并隆重祭祀。
梦自然是虚假的,但那美妙的梦境却正是穆公急欲成就霸业的内心的真实写照。
越俎代庖:秦为晋置君
当期盼中的最佳时机终于到来的时候,秦穆公特地在新落成的霸城宫举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朝议。这一回的议题是秦国历史上空前的:以受命于上天的名义,议一议秦国究竟让谁去当晋国新君?
一个中原大国的君主居然要由秦国来议定,这一事实本身最雄辩不过地说明了:昔日被人鄙视的秦国,如今已跻身于少数强国之列了!
朝议的结果认为尽管晋献公有子一大群,但多系庸碌无能之辈,能够站得住脚的,也只有重耳、夷吾二人。因而以从二人中择一为妥。
那么究竟选择谁呢?
百里傒说:重耳奔于狄,夷吾居于梁,此去都不甚远。君上能否派人去对献公之死表示吊唁,一则显示我秦国之重于礼仪,二则可以借机观察二位公子之为人,然后从中酌定。
穆公觉得有理,就派公子絷代表国君前去吊唁。
公子絷先到狄。
宾主礼毕,一身缞绖的重耳即行告退。公子絷通过守门人给重耳传去一句话:公子如有意乘时入主上国,敝国国君愿以车马为公子前驱!
在晋三公子中,重耳居中。他以宽厚仁爱闻名,其实却是个极有志向和城府的人。在申生接连受谗害以至最后自杀时,他是同情的;但如今奚齐、卓子先后除去,那么申生的自杀便是给他提供了一个曾经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的机会。不过他知道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奚齐、卓子虽死,其余党尚存,更何况逃亡在外另有夷吾,仍在国内的公子就更多,一场争夺势所难免。如同摘取甜美的果子需要等待一个成熟期一样,他还得忍受和等待直到各种条件大致成熟,然后才能较为顺利地去获取。因而三日前当正卿里克、大夫丕郑等大臣派人来奉迎他回国去继位时,他对来使说了这样一番话:重耳不孝得罪先父,逃亡四方,生既不能尽问安侍膳之诚,死又不得奉视含哭位之礼,更何敢以德薄才微之躯乘乱贪位呢?还祈各顾命大臣更立他子,重耳当竭诚敬奉新君,不敢有违!
但是,眼前却出现了一个不曾预计到的新情况:一个强大的邻国主动找上门来愿意作他的后盾,要不要接受这种保护呢?
重耳在后舍召来跟随他逃亡的大夫赵衰,问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赵衰还保持着昔日中原大国的气度,说:靠别国力量保护入主晋国,即使做到了,也不怎么光彩吧?重耳自然也有同感,但他觉得到实在必要时,这也未尝不是一条可行之路,只是其他条件目前尚未成熟。于是便出来对公子絷说:君诚意惠吊亡臣,并转致上国大君美意,重耳不胜惶恐。亡人无宝,唯以仁亲为宝。父死亲丧,重耳已形容枯槁,唯依制丁忧而已,哪里还敢有什么其他想法呢?说完竟伏地大哭起来,声感天地。
公子絷转而向梁国进发。
这时候,夷吾正与跟随他逃亡的大夫吕省、郤芮等大臣,在梁国为他提供的官舍里进行着紧张的磋商。
接连几天,忧喜参半、吉凶难定的消息,不断从绛城传来。开头说,奚齐、卓子已被杀,这当然是喜讯。后来又说,几位顾命大臣已派人去迎接重耳。夷吾一听,顿时发了急,命人火速筹划,准备赶回绛城去争国。恰在这时,官舍外飞来几匹汗淋淋的快马,来人禀报说:重耳无意入国,几位大臣派来迎接新君的乘辇很快就要上道。夷吾以手加额欢呼一声:这是上天有意要把晋国赐给我啊!
郤芮却说:重耳恐怕不是不想做国君的人吧?他不去,其中必有缘故。正卿里克、大夫丕郑等人如今已在那里控制了局面,公子也有好几位在,他们还要向外求君,肯定是有企图的。这些人,本来就是私欲很大的啊!
夷吾说:那也不难,就答应给里克以汾阳之田百万,给丕郑以负葵之田七十万吧!说时就命左右书契缄封,立即派人送到绛城去。
吕省说:即使如此,还不能算是十分稳妥。常言道:入虎穴者,必操利器。如今晋国朝堂怕已是虎狼成群,公子欲求入主,看来非借强国之力为助不可。
夷吾觉得有理,但究竟是西借秦国之力,抑或东赖齐、郑之助,一时议论未定。
守门人就是在这个时候跑了进来,大声禀报道:秦国使者大夫絷来到!
作为走过场的吊唁仓促礼成。
宾主落座,夷吾就直奔主题:大夫以君命远道来吊,当有以赐教亡人吧?
公子絷一见对方如此急切之态,反倒故意延宕迂回,待夷吾再次逼问,才缓缓说出了秦国将出兵为援的话,却又有意戏言几句:卫国地方男女多情,他们作诗唱道:“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絷向闻上国名山众多,不知也出产此种琼瑶否?
夷吾立即接口说:时雨之恩,当以此心相报。夷吾又何惜一琼瑶呢?
说完又稽颡称谢。
夷吾以为已经吃到了定心丸,就进入内舍,向他的臣属通报了与秦国来使商谈的结果。。
郤芮说:看来贪心的秦国,是不会白白这样做的。恐怕得割出一大片土地来给它作为酬谢吧?
夷吾说:贿赂自然是少不了的。不过寡人很快已是晋国国君了,割一大片土地,对晋国损失不是太大了吗?
吕省说:这笔账看你怎么算。公子若是不能回国即位,岂非只是梁国一匹夫吗?晋国那么多土地连一寸也没有公子的份。所以割让给秦国的土地原本就是他人的,谈不上损失不损失!
夷吾再次出来时,就对公子絷说:里克、丕郑即将迎我入国,亡人都将给予相当多的酬谢。亡人若能获得上国大君宠爱,入主晋国社稷,则敝邑愿献河西八城之地,聊报大德于万一。其域东尽虢地,南至华山,可为大君闲暇时东游狩猎之便!
说着,从袖中取出已经书契的盟约,双手捧上。
公子絷待要作些谦让之态,夷吾又说道:亡人另有黄金四十镒,白玉六双,愿献于大夫左右,还求笑纳,不敢说是报答。卫国男女诗中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公子絷接过盟约,仰首一阵大笑,说:好一个“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贵公子果然有情啊!
公子絷回到秦国,详细复述了见到两个公子的情况。
秦穆公说:如此看来,重耳要贤于夷吾。是否以接纳重耳为妥?卿等可一议。
公孙枝说:这要看君上纳晋君的目的何在了:是为晋国之安定强盛呢,还是为秦国扬威于天下?如果是为晋国,自然应当择贤君;若为秦国计,那倒不如接纳不贤者!
穆公说:那为什么呢?
百里傒说:纳贤与纳不贤可以得到“置君”之名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接纳贤君,等于为自己安置了一个强大的邻国;接纳不贤之君,其国就难以强盛,但邻国之弱,不正是秦国之利吗?这个道理很残忍,但这个道理很现实。
穆公兴奋地说:先生这番话,使寡人有顿开茅塞之感!看到蹇叔一直未开口,又问道:卿因何默而不语?
蹇叔喟叹一声说:唉,这大概也是上天安排的吧?看来,晋国祸乱还远远没有到头呢!
穆公一阵朗声大笑说:您老真是一位爱好仁义的大长者啊!
秦穆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霸城宫前严整地陈列着三百乘战车,戈戟森森,旌旗猎猎。举行过隆重的祭祀仪式后,穆公亲授符节,以百里傒为特使,由孟明视等三将率领这支宏大的队伍,护卫着夷吾由梁国进入晋国去即位。这在秦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一百多年前,曾经有过一次秦襄公护送周平王东迁,不仅规模完全不能与这一次相提并论,更重要的是所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作为“附庸”小心翼翼地听人调遣的,如今却以一个新兴大国的身份,独立作出决定,把战车开进另一个大国,去主宰那个大国的命运。这是秦人历史上从未享受过的荣耀啊!
但当这支队伍渡过黄河,刚要踏上晋国土地时,忽而飞来一片乌云,几乎遮没了刚才还是他们独自拥有的那片阳光灿烂的天空。
不远处灵宝山下尘烟起处,望不到尽头的战车阵列正滚滚向这边驶来。三员虎将勒马横戈以手加额望去,但见那队伍前头猎猎飘动着的旌旗上绣着一个大字:“齐”!
一场更大范围内的争夺战,就这样拉开。
欺骗也成了一种战术
《韩非子·扬榷》篇有句极为生动、形象的话,叫作“一栖两雄,其斗(yán,争斗貌)”。《礼记·曾子问》也有类似的话:“天无二日,土无二王。”我们大致可以推定,这些都是当时流行的俗话。因为在春秋战国那个特定时代里,人们天天看到、碰到的最突出的事实便是:诸侯在相互为争霸而无休止争战中可以暂时无霸,却决不允许同时存在两霸!
当秦穆公在西陲之地又是修造霸城宫,又是祭祀宝夫人,一厢情愿地做着称霸美梦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绝不可能逃过已经称霸于诸侯的齐桓公的耳朵和眼睛。齐桓公岂能容得关西蛮儿如此目无他这个公认的霸主!但他觉得尽可沉默以对,没有必要立刻作出反应。待到夷吾归国前夕,齐桓公突然以受命于周天子的名义,率领诸侯来到晋国;同时派出大行(礼官,掌接待宾客)隰(xí)朋统率五百辆战车浩浩荡荡到黄河边迎接夷吾。这一来,踌躇满志的秦国一下被推到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只是由于齐桓公有老练沉着的管仲在一旁辅佐,才没有把事情做得太绝,后来各自后退一步,算是两国“共同”扶持夷吾入晋。
这样,夷吾便在两大强国的扶持下,于周襄王二年(秦穆公十年、公元前650年)坐上了君位,称晋惠公。
人们通常以为一仆二主就是仆人的地位双倍低贱,却不知同时也意味着主人权威的贬值:此时仆人不仅可以有所选择,有所依赖,还可以利用一方去制约另一方。
惠公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毁弃前约。他派丕郑带着他的信函出使秦国,信的措辞不免有些滑稽。他说他本来曾应许秦国以河西之地为酬报,可如今大臣们都说土地是先君的土地,你当时还是一个逃亡在外的公子,怎么可以擅自把先君的土地奉送给人家呢?他怎么也说服不了大臣们,因而只好对秦国表示歉意。
秦国朝堂上下一片愤怒。对如此忘恩负义的小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但秦穆公与百里傒等大臣再三商议的结果,却觉得晋惠公所以敢于公开毁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因齐国的介入而有恃无恐。秦国如果贸然出兵,必然引来齐国干涉,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无奈只得忍着这口气,以待事态的发展。
惠公即位后的第二件事是诛灭异己。最先想到的是正卿里克、大夫丕郑,因为按他们本意要立的是重耳,而不是他夷吾。对这两人曾经有过的封赐允诺,自然早已变成子虚乌有。当时也不过是随便拿起的一块敲门砖,如今既已进门,要考虑的就是如何除掉他们的问题,还谈什么封赐不封赐!于是先派丕郑出使秦国,支开他们当中一个,单留一个对付起来就要容易得多。惠公召来大夫郤芮商议说:里克对寡人是有功的,现在要杀他,该用个什么罪名呢?
郤芮说:里克杀奚齐、卓子两位国君,又杀顾命大臣荀息,罪行太大啦!君上念他迎纳之功,那是私劳;而讨其弑君之罪,那是大义。古来贤明的君主都不会以私劳害大义。请君上准许臣奉命讨逆!
惠公说:你说得有理。那就去办吧!
郤芮来到里克府第说:君上有命令,派我来转达给您。君上说:没有足下,寡人不可能立为新君,寡人不会忘记足下的接纳之功。不过,足下弑二君,杀一大夫,这就使得寡人很难为足下说话了。寡人要遵奉先君的遗命,就不敢以私劳害大义,只好请足下自己裁决!
里克愕然不语,郤芮在一旁催逼。里克仰天喟叹一声,留下一句千古名言:“欲加之罪,其无辞乎?”随即引剑自刎。
还在秦国的丕郑一听到里克被逼自杀的消息,就在辞行时向秦国献计:让丕郑带一信函回晋国,诱使为夷吾出谋划策的吕省、郤芮来秦而杀之,再以重兵送重耳回国即位,丕郑则在国内做内应。秦国朝堂上下原本就憋着一股子窝囊气,急待奔突而出却苦于找不到缺口,因而一听到丕郑献出这样一计,便以为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秦穆公欣然采纳,亲书一信,并回赠以丰厚的聘问之礼。
信是这样写的:
上国大君左右:秦晋乃甥舅之国,前效微力,何敢言报。上国诸大夫忠义可鉴,不穀断不至于以区区八城之地而伤诸大夫之心。况仅以一河相隔东西,晨昏举首可望,地之在晋亦犹在秦也!
敝邑近有校场演技之事,久闻上国吕、郤二大夫武艺精湛,欲求当面赐教,幸旦暮一来,以慰不穀深望。
惠公收到信和厚礼有点喜出望外。但吕省、郤芮却从丕郑对里克的死似乎并不怎么在意,而丕郑府第人事往来却异常频繁等迹象中起了疑心,禀过惠公后,一面暗中监视,一面派人打入内部窃得真情,一举将丕郑等九名大夫尽行擒获、杀戮。至此,以里克、丕郑为首的一派力量已被消灭殆尽。
九大夫的亲属只有丕郑之子丕豹得以脱身逃命。丕豹逃到秦国,跪伏在穆公面前,大哭不止。他请求秦国立刻发兵讨伐晋国,并且说:如今的晋君背秦恩而积民怨,百姓愤怒已到了极点。大国偏师所向,国人必以箪食壶浆出迎义军,废旧立新易如反掌!
经历了又一次挫折,这时候的秦穆公已较为冷静,他让大臣们来议论这件事。
蹇叔说:听丕豹的话而兴兵伐晋,那是助臣犯上,有违道义。
百里傒说:若是晋国百姓真像丕豹说的那样愤怒了,那是很快就可看到内变的。是否还是等发生了内变,再来商议对策为好?
穆公说:寡人也有些怀疑。如果百姓已愤怒到那种程度,还能一下子杀九位大夫吗?夷吾这样做了还能站得住,说明支持他的人还有相当力量。
于是决定不兴兵,暂作壁上观。留丕豹在秦,并仕以大夫。
此后,秦晋之间居然过了一段颇为太平的日子。秦穆公十三年(公元前647年),晋国遇上严重灾荒,百姓大饥。晋国向秦国借粮,百里傒、蹇叔都认为灾荒难免,哪一国都有,救灾恤邻,理义之常,应当借给。丕豹则还念着杀父之仇,攘臂高呼,要趁此天赐良机,征伐晋国。穆公说:负我者乃晋国君主,与百姓何干?寡人不忍因君主之故而迁怒于民。
于是紧急调运黍粟数万斛,经由渭水、黄河、汾水,送往晋都绛城。数十天里,舳舻相接,纤人连行,历史上称之为“泛舟之役”。
应当说,这“泛舟之役”才是秦国历史上取得最辉煌胜利的一役。这不是战争的胜利,却胜过战争的胜利,即道义的胜利,争取人心的胜利。此后一段日子里,晋人提起秦人会有一种特别亲切之感。甚至死去的太子申生也托梦给人说:“夷吾无礼,余得请于帝,将以晋与秦,秦将祀余。”(《史记·晋世家》)死人托梦,固属无稽,但做梦人有过类似想法,却又是真实的。
巧得很,只过了一年,情况就倒了过来:秦国大荒而晋国大丰收。秦穆公派人向晋国借粮,晋惠公却在近臣的怂恿下,非但拒绝出借,还乘人之危准备立刻大动干戈。穆公大怒,主动率兵迎击。这一年(公元前645年)秋天,秦军越过黄河,深入到晋的韩地,秦、晋爆发了著名的“韩原之战”。
韩原之地,一说在今陕西韩城西南;一说在今山西河津、万荣间。韩原之战的发展充满戏剧性。两军对峙,惠公与穆公原是郎舅之亲,战场上却成了生死对手。他们先通过书简进行了一场有趣的对话——
惠公说:寡人此次仅带甲车六百乘,但似已足可败君于马下。君若退师,正合寡人之愿;如其不然,则寡人也愿退而让君,只是三军将士其势汹汹然奈何奈何!
穆公说:君欲国,寡人迎而纳之;君欲粟,寡人筹而送之。今君欲战,寡人岂敢抗命失陪呢!
战幕拉开,求胜心切的惠公,披甲横戈奋勇出击,竟至脱离了主力部队,被泥泞的山路绊住了马足。穆公率领麾下军士恰好赶来,双方展开了一场生死肉搏。盔落发散的惠公眼看就要被生擒,恰在危急关头,晋军的部分主力军已匆匆赶到。转眼间被团团困住的已由惠公换成了穆公。穆公战车左侧的马已被晋军扣住,晋军一位将军的长戟击中了穆公的胸甲,七层厚的甲衣已经刺到第六层。就在这时,前方忽而响起了潮水般的呐喊声,眨眼间,不知从何处飞来三百余名勇士,左冲右突,一下攻破了晋军的包围圈,非但穆公得以脱险,还活捉了惠公。秦军乘胜追击,全歼了晋军。
这三百余名闻讯赶来解救穆公的勇士,穆公却并不认识。询问后方才知道,那已是多少日子前的事了。那次穆公轻带随从到岐山脚下去闲游,不知怎的走失了一匹心爱的坐骑。好容易找到时,那马已成了釜中之物,正被一群村野农人美美地享用着。一位侍从官吏正要对这群粗人绳之以法,穆公却阻止了他,反而对那些村野农人说:我听说吃马肉不同时喝点酒,会伤身子呢!说着,就命人马上扛来酒,让他们尽兴而饮。这回对韩原之战起了如此重要作用的三百余名勇士,正是那些吃过马肉的村野农人。
大获全胜的秦军,兴高采烈地渡过黄河,沿渭水浩荡西行。晋惠公和他的一些近臣被作为俘虏押在这支狂欢的队伍之中。如何来处置这位在押的国君,穆公曾有过杀之以祭祀天帝的想法,只是尚未与大臣们最后议定。秦军刚要进雍城时,却见一辆披以缟素的乘辇缓缓从城中驶出。乘辇停下,走出一个端庄绢秀的女子来,也是一身素白,却正是穆公夫人,即当年因结“秦晋之好”而从晋国迎娶来的晋献公之女穆姬。将士们一个个敛容惊视,穆公急忙走下乘辇迎上去说:夫人为何这般装束?
穆姬说:君上凯旋而归,妾身本应以盛装相迎。只是妾身不愿看到秦晋之好因此一战而永远不再,故以缞绖来见。夷吾纵然负义且不仁,但穆姬不能因怨而忘亲,因怒而弃礼。若晋国国君早晨押解到秦宫,妾身就早晨死去;若晚上押解到秦宫,妾身就晚上死去。还望君上恕罪!
穆公连忙说:夫人快别这样想了,寡人与夷吾原是郎舅之亲,又何至于如此绝情呢?今日邀来,原也只为一叙情谊。难得夫人提醒,寡人当择日护送晋君归国就是!
随即命内侍为穆姬除去缟素,同登乘辇进城。
这时候又有几匹快马奋蹄赶到,是周天子从雒邑派出的使者,也是来为被俘的晋君说情的。
于是穆公便对惠公做出了不杀而送回国的决定。当然,穆公所以这样做,也并非全是由于夫人的以死相胁和周使节的远道赶来说情,更主要的是他自知秦国远没有强大到可以吞并另一个大国的程度。勉强那样做,只会使自己陷入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而释放夷吾,秦国不仅可以继续保持道义上的优势,而且还能控制和利用晋国。
这样,秦晋两国便达成了以下内容的和约:
(一)秦送夷吾回国继续君位;
(二)晋割河西八城之地予秦;
(三)晋太子圉入秦为质,穆公以女儿怀嬴嫁与圉为妻,以续秦晋两国累世联姻之好。
从国君跌落到阶下囚,这个人生大转折,终于使晋惠公对自己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回国前,他特地派出大臣代表他去向晋国臣民说:是我污损了国家的体面,我还有我的儿子圉,都不配再即君位,请国人另立国君吧!国人听了都感动得大哭,还是要求惠公复位。此后,在惠公继续当政的三五年内,晋国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其中包括废除井田制,实行了与秦国相同的爰田制;还建立了“州兵”制,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的一种地方武装力量。
经过这样一些整顿和改革,晋国才又渐渐恢复了生气。
但不久,惠公病倒了!
在秦国这边,这天凌晨,怀嬴公主忽然哭着来对父亲说:太子圉逃走了,逃回晋国去了!
穆公大骂一声:竖子欺我!又仰天长叹道:呵,早知夷吾父子都是此等小人,悔煞当初不立重耳啊!
怀嬴公主当了两次政治筹码
在晋国内乱外患相继迭起的这些年月里,三公子之一的重耳还一直逃亡在外。由于他的贤名,追随他一起逃亡的有赵衰、狐偃、介子推等一大批颇具才识的辅臣。他们在外流亡十九年,历经狄、卫、齐、曹、宋、郑、楚、秦等国。其间卫文公的轻慢,曹共公的无礼,晋惠公还曾派人谋刺,所遭逢的艰险和屈辱,可想而知。重耳出亡时尚是壮年,待到归国即位为晋文公,已是六十二岁的老人了。也许正是这一段阅尽世态炎凉、尝遍人生百味的经历,冶铸了他的意志、毅力、气度和人格,使他后来有可能继齐桓公之后成为春秋第二个霸主。
太子圉的逃跑,使秦穆公下决心作出了一个新的选择:改立重耳为晋君。
经过一番追影探踪,得知重耳已逃亡在楚国,穆公立刻派公孙枝去聘问楚成王,迎重耳入秦。重耳一到,又待以国君之礼,举行了盛大的酒宴。红灯绿酒,轻歌曼舞。席间,宾主实际上进行了一场政治谈判,却以诗诵歌吟的形式出现,妙语联珠,精彩纷呈。
重耳以往赴宴通常由正卿、又是他舅父的狐偃陪同,这回却特意换了颇通诗文、善于辞令的大夫赵衰,因为他知道穆公十分讲究礼仪,又熟习中原文化,有赵衰在场便于应对。
先是穆公吟诵《采菽》诗:
君子来朝,何锡予之?
虽无予之,路车乘马;
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这本是周天子欢迎诸侯来朝时演奏的一首乐歌。穆公与重耳原是郎舅之亲,但他经过精心选择的这首诗,却暗示自己与这个小舅子是天子与诸侯关系,秦国与晋国是宗主国与附属国关系。
穆公刚吟完,充任赞礼的赵衰便唱名让重耳下堂拜谢,穆公也下堂答拜。接着赵衰便选了一首《黍苗》让重耳赋诵:
芃芃黍苗,阴雨膏之。
悠悠南行,召伯劳之……
重耳吟这首诗的用意,是在头里两句。他懂得《周易·系辞》中说的“尺蠖之屈,以求信(通“伸”),龙蛇之蛰以存身”的道理。如今他尚处于逃亡中,不能不对穆公卑躬以求,离开秦国强有力的支持,他是断难回国即位的。但若由他来明说,则有碍风雅。于是在一旁的赵衰便以赞礼的身份半真半戏地吟唱道:呵,这诗说得多有意思!公子仰望君上的降恩,就像禾苗渴望时雨的滋润一样。如果禾苗因有雨水滋润而得以结出金黄饱绽的谷子,奉献给晋国宗庙,那全是君上的大德啊!如果公子承蒙君上的大德成为晋国百姓的君主,晋国怎么会不听从君上的安排呢?如果有晋国这个获得君上恩泽的范例,那么四方诸侯,有谁还敢不诚恐诚惶来听从上国大君的命令呢?
穆公赞叹说:您先生真会说话啊!但那是贵国公子得道多助,哪里是只靠寡人一人呢?
接下去,宾主又分别吟诵了几首诗歌。穆公诵《小宛》,盛赞重耳“翰飞戾天”的志向,表示愿意尽力帮助重耳回国争得君位。重耳赋《河水》,表示即位后要像流水归于大海那样朝事秦君。最后穆公朗诵了气势宏大的《六月》,鼓励重耳去创建未来大业。宾主再次拜谢和答谢。
以上情节采自《国语·晋语四》,我们现代人读此可能会感到很新鲜。其实,古代在贵族子弟间,以诗歌作为交际应酬手段相当盛行,以至被视为一种身份、修养的标志。所以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至于在外交场合以诗歌作为谈判的一种技巧,更是屡见不鲜,如《左传》中就有大量此类记载。
这个夜晚,穆公似乎特别高兴,特地从嬴氏宗室中选了五个女子赠给重耳做侍妾。重耳自然也高兴。十九年的流亡生活行将结束,梦寐以求的君位抬眼在望,都是值得庆幸的;但作为大国的晋国竟然要如此低眉折腰仰求于人,又不免有几分难以明言的隐愤。次日清晨起来,一个侍妾又端着盆盂来让他洗手,洗过后,他挥挥湿手让她走开。可能眉宇间已泄出了内心的几分隐愤了吧,那女子突然正色道:秦国、晋国是同等的国家,公子怎么能这样轻慢我呢?
重耳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子正是秦穆公的女儿怀嬴!他赶紧除去衣冠表示罪己,听任惩罚。穆公得知后却反来自责,再三说明怀嬴是他女儿中最有才德的一个,但因已嫁过太子圉,所以不敢正式婚配,只是暂充奉巾执帚之列,收不收留她,听凭公子处置。
又一个万万没有想到:太子圉是重耳之侄,因而怀嬴还曾是他的侄媳呢!
该不该娶这个侄媳,重耳的几位辅臣进行了郑重而有趣的讨论。他们说古道今,引经据典,最后得出结论说:重耳与太子圉虽然原为同姓,但因异德异心,如今已如同陌路,因而“取其所弃,以济大事,不亦可乎”(《国语·晋语四》)?
在这里,最要紧的是“以济大事”四个字。为了回国即位这件大事,娶侄媳为妻又有何妨!于是,同是这位怀嬴公主,第二次为“秦晋之好”做出了牺牲,与说起来还是她伯公的重耳,在霸城宫里隆重地举行了婚礼。
太子圉所以要抛弃娇妻仓促逃回国去,与现代人所说的爱情呀、婚变呀,全然无关。他是因重病的父亲归天在即,怕“近水楼台”之人会乘机抢去本属于他的君位。果然,子圉归国不久惠公便溘然离世,临终托孤于吕省、郤芮。太子圉即位,是为晋怀公。吕、郤提醒说:诸公子倒不必担心,最需防备的是逃亡在外的重耳。于是发出一道命令说:凡是跟随重耳出亡者,限三个月之内回国。逾期不回,录罪注死。父子兄弟坐视不召者,并杀不赦!
不是三月,而是只过了三天,重耳和他的随从们便一起回到了晋国。但不是来向怀公服罪,而是来夺他君位的。秦穆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秦国以五百乘战车、两千精骑、五万步卒的强大威势,护送重耳渡过黄河,踏上晋境。在国君位置上坐了不到半年的怀公子圉慌忙出逃去了高梁。吕省、郤芮等一班大臣也不敢以卵击石,纷纷出郊恭迎。重耳一面派人去高梁刺杀子圉,一面宣布即位,是为晋文公。其实,吕省、郤芮等人只是迫于秦军的强大威势,才不得不暂时屈从的。待秦军退走,他们便暗结同党,歃血为誓,约定时日,欲焚烧晋宫,杀死文公。但其中有个叫寺人披的参与者却向文公告了密。文公看到自己在国内实力还不足以固位,便逃出绛城,在王城(今陕西大荔县朝邑东)这个地方与穆公秘密相会,以求庇护。到约定时日,晋宫果然起了火。吕省、郤芮等人这时才发觉文公不在宫内。估计文公是向秦国方向逃去的,又匆匆追到黄河边。穆公以另立吕、郤等人愿意接受的新君公子雍为诱饵,将他们诱到王城,这时便出现了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吕、郤问新君何在,愿求一见。穆公便高声说道,请新君出来吧!屏后一闪,果然出来一个贵人,吕、郤抬头一看,竟是文公,当场惊倒在地。
到这时,穆公终于帮助文公除去了全部政敌。又派兵三千第二次护送重耳回国。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倒有近半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三置晋君”这件事情上。文公第二次回国后,励精图治,完善爰田制,增强军队,晋国很快强盛了起来。接着又以“尊王”相号召,平定周乱,迎接周襄王复位,败楚军于城濮,会诸侯于践土,成了赫赫霸主。穆公扶持重耳的本意,是欲使晋受控于秦,但后来的发展却是事与愿违,在诸如上述尊王平乱、城濮大战等事件中,秦国往往不得不追随于晋国,扮演一个呐喊助威的角色。多少年前,穆公曾经后悔不该接纳夷吾,此时是否又有些后悔两次护送重耳了呢?
不管怎么说,终文公之世,秦晋两国关系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友好的。文公一死,秦国立刻尝到了晋国抛出的苦果,而且是一颗很大的苦果!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