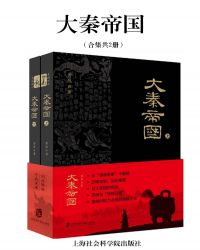中原列国之树上的最后一片黄叶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中原列国之树上的最后一片黄叶
来自民间的末世贤后
中原六国,还剩下一个齐国。
在历史上,齐国前后有姜齐与田齐之分。始祖吕尚,姜姓,就是因演义小说《封神榜》而在民间流传极广的姜太公。周武王封吕尚于齐,建都营丘(后称临淄)。春秋初期齐桓公任用管仲,厉行改革,国力富强,成为第一个霸主。春秋末年,君权逐渐为专以小斗入、大斗出收揽民心的大臣田氏所夺。传至齐简公,田成子杀简公立平公,齐国之政已几乎全为田氏所有。田成子数传至田和,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承认田和为齐侯。又过六年,齐康公死去,姜齐终为田齐所代。田和三传到齐威王,国势大盛,径称王号,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从此便开始了与秦、楚形成东、西、南三强鼎立的局面。苏秦说齐宣王时称:“齐南有泰山,东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史记·苏秦列传》)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任用乐毅为将,与秦、楚、韩、赵、魏五国联合伐齐,齐国大败。乐毅率军攻破齐都临淄,尽取珍宝,并焚烧宫室宗庙。齐国城邑只剩下莒、即墨,其余皆为燕国所有。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做了流亡国王的齐闵王,居然还要大摆其曾经想自称为“东帝”的天子架子,在先后奔卫、邹、鲁过程中,竟还要人家按照天子巡行的礼节来迎候他,结果自然遭到拒绝,弄得狼狈不堪,最后只好退到莒即今山东莒县这个地方。在这里,又发生了一桩奇案,插进一个具有戏剧性的人物来,叫淖(zhuō)齿,是楚人。据《史记》记载,楚原先也是与燕联合伐齐国之一,但此时它却又派出将军淖齿率领楚军来救齐,居然还得到了齐闵王的信任,让这个楚人做了齐国之相。但就是这个淖齿,忽而转过身来,捉住齐闵王,煞有介事地先来一番批斗,随即一刀将他杀了。淖齿这样做的目的,竟然是为了“与燕共分齐之侵地、卤器(即宝器)”(《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齐闵王被杀,他的儿子法章侥幸得以逃脱,改名换姓,乔装打扮,开始在莒城(今山东莒县)街头流浪。
这位昨日的王太子,成天无所事事地踯躅在沭河边,看看那些渔夫、纤夫日夜都在辛勤地劳作不息,开头还有些弄不明白:作为一个庶民,单是为了生计因何竟有如此艰难!但很快,饥饿和寒冷迫使他懂得了这一切。
几天后,法章不得不也穿着破衣烂衫走向佣仆市场。
他出卖了自己,被带到一座府第,做了奴仆。
太子与奴仆,相隔不啻天壤,其中辛酸可想而知。总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他的主人还是当地颇有学问和声望的太史敫,为人耿直厚道,待下人也不薄。法章每天只是奉箕执帚,担水灌园,克尽作为一个奴仆的职守,日子一长,倒也渐渐习惯起来。
作为奴仆,他暂时栖身于一间狭小的柴房。
忽然有一天,一位美丽而贤淑的女子从天而降,于是简陋的柴房成了充满温馨的伊甸园。这位女子便是太史敫的千金。她开始还只是出于同情,偷偷拿点衣食来接济这个眉清目秀的仆人;渐渐便产生了感情,直至真心相爱。
多少年后,当法章回忆起当奴仆的这段经历来时,都还抑制不住激动。作为太子或者将来作为国王,他将拥有成群的嫔妃侍女,原也不足为奇,但那只不过是权力在性方面的炫耀,绝无半点真情可言。不是在王宫里,而是在柴房里,他享受到了人世间如此宝贵的真情,说起来倒还得感谢那场导致他流浪的灾难呢!
自然更其难得的还是那位太史的女儿。她从小生长在优越的生活环境里,并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但她却能摒弃世俗偏见,以千金贵体选择一个奴仆为终身伴侣。在他们相识的那些日子里,淖齿还居留在莒邑,法章决不会以生命为儿戏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因而太史公女儿看到的只是法章这个“人”,一个纯粹的人,绝不附带任何齐王贵胄的观念;相反,她自己倒真是书香门第之后。这样,她从闺阁走向柴房的每一步不仅需要眼力,还得有极大的勇气。《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正是这样记载的:“太史敫女奇法章状貌,以为非恒人(常人),怜而常窃衣食之,而与私通焉。”这是发生在古代杜会里的一个真挚的爱情故事,弥足珍贵。
这期间,齐人的复国运动已在各地迅猛展开,其中十五岁少年王孙贾杀淖齿的故事,最为人称道。王孙贾原是齐闵王家臣。齐闵王逃亡,后又被杀,他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母亲责备他说:“汝早出而晚来,则吾倚门而望;汝暮出而不还,则吾倚闾而望。汝事王,王走,汝不知其处,汝尚何归焉?”(《资治通鉴·周纪四》)王孙贾受到极大激励,赴市中振臂高呼:贼人淖齿,乱我国,杀我王。诸父老有愿与我去杀此贼者,请袒右!当场用袒露右臂这种方式表示相从者,就有四百余人。后来果然杀了淖齿。
淖齿既除,莒城民众纷纷额手相庆,流亡在各处的齐国王室和大臣也相继到莒城来寻找太子的下落。满城老少都在争说太子的年岁长相,渐渐地自然有人把眼光落到太史敫府上这个来历不明偏又长相不凡的奴仆身上。法章余悸未消,怕有不测,犹是百般隐蔽,直到有一天王室中相识的人突然找到了他,他才敢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
这位做过奴仆的太子,就这样在莒城被众人拥立为王,他便是齐襄王。太史敫的女儿被尊为王后,就是君王后。
太史敫一夜之间当上了国丈,按说该是喜出望外了。可老人生性奇特,这时他却说:女子不经媒人作伐私自嫁人,玷污了家族的门风,她不配做我的女儿!竟然发誓不肯再见女儿一面。贤淑的君王后,没有因为父亲的绝情而忘记子女应遵奉的礼制,还是恪守自己的孝道。
不仅如此,她还能很好地佐助襄王,使齐国迅速走出困境,渐渐又强盛起来。齐襄王五年(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齐国运用反间计,使继位的燕惠王对乐毅产生猜忌而改任骑劫。接着齐将田单运用著名的“火牛阵”战术,大败燕军,杀死骑劫,很快收复了被乐毅攻取的七十余城,襄王回到了临淄,齐国又大致恢复到原来的大国地位。
齐襄王在位十九年后死去,儿子齐王建继位。建年少,暂时由太后管事。这样,又给这位来自民间的王后一个机会,让她更能充分发挥自己在治国经世方面的智慧和才干,《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曾作过这样的评述——
君王后贤,事秦谨,与诸侯信,齐亦东边海上,秦日夜攻三晋、燕、楚,五国各自救于秦,以故王建立四十余年不受兵。
关于君王后谨慎地与秦国交往,保持了不卑不亢的大国气度,《战国策·齐策六》记下了一件小事可以作为例证。有一次秦昭襄王派专使给齐国送来一只玉连环,使者说:我们大王听说上国多智能之士,所以特地送此玉连环,不知上国有人能解得否?君王后看出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玉连环,秦王特派使节送来,显然带有作难、挑衅之意。她不动声色地将玉连环交与左右群臣试解,自然一个也无法解开。于是她便拿起锤子当场把玉连环击得粉碎,然后对秦国使者说:很抱歉,只有用这个办法解得开!
齐王建十六年(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即位,吕不韦率军攻灭东周,周室彻底灭亡。就在这一年,君王后病倒了。她在弥留之际,对软弱无能的儿子齐王建似乎很有些不放心,她把他叫到病榻前,训诫说:我儿万万要慎于用人。群臣中可用的……
话还没有说完,就已气竭力衰,听不清她说的名字。
齐王建说:能请母后写下名字来吗?
君王后微微颔首说:好。
齐王建立刻命人取来笔和木简,但这时候君王后头已垂了下来,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也写不成一个字。
临淄成了不设防的都城
从君王后去世,到齐国灭亡,还有二十八年时间。
这段时间,无论在齐国本身历史上,或是其他六国历史上,都很难找到类似的时期。它集中表现了一个没落阶级、一种没落制度临终前夕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腐朽和颓废。众多附着于这艘孤舟之上的人们,以醉生梦死为常态,以追求瞬间的感官刺激为时尚。他们没有看到、也不愿看到这艘孤舟已在下沉。广阔的周边正在经受着血与火的煎熬,而他们却庆幸自己的双脚总算还踏在一片似乎和平安宁的乐土上。
在如此颓堕萎靡的氛围中,再也产生不出韩非、荆轲,产生不出项燕、李牧,也不会有太子丹、太子嘉,甚至连魏王假都不可能有!
产生这种奇特的现象自然有它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其中一个直接的外部原因,则是秦国在这个特殊时期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对策。
在秦国筹划和发起兼并六国大决战这个时期内,秦对齐的战略基点便是要设法稳住这个东方大国。
在这一点上,燕昭王任乐毅为将,联合五国把齐国打得几乎趴倒在地,龟缩在即墨、莒这两个海边小邑苟延残喘,这件事实在帮了秦国大忙。以后是原为临淄掾吏的田单,以反间计使燕王怀疑乐毅而将其撤了下来、又用“火牛阵”大败燕军收复七十余城,总算给奄奄一息中的齐国冲出了一条生路。但无奈齐国元气已伤,致使秦国此后威胁利诱并用的对策每每奏效。最明显的例子是,赵国在长平之战和邯郸被围那样危急关头,曾经向齐国请求借粮,齐国的谋臣周子也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救赵抗秦,可以获得“高义”和“显名”,应该借给赵国粮食,但齐王就是不听。
接着发生了淖齿杀齐闵王的事件。一个名义上还是来救齐的楚国人,竟然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把齐王杀了,这件事自然激起齐人对楚的无比愤恨。秦国立刻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情绪,派出两名使节,一至楚,一至齐,都表示要修好。而其实对楚国的修好是假的,是特为做给齐国看的,那意思是:你齐国如果不乖乖听我秦老子的话,我就跟你的死对头楚国联合起来,看你以后还怎么过日子!从此拒楚亲秦便成了齐国的一条基本国策。
在这同时,秦国又充分发挥“第五纵队”作用,以黄金和珠宝收买齐国新上任的相国后胜。《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是这样记载的:“君王后死,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通“纵”,指合纵)朝秦。”齐王建已被后胜及从秦国“游历”回来的宾客,即一大群秦国间谍所包围,齐国朝廷几乎已成了秦国的一个派出机构。齐国在最后二十八年里执行的可说是一条“双不”方针: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抗秦。
于是,临淄便成了一座不设防的都城。
这自然是醉生梦死中的齐王室及后胜等辈所需要的,只要眼前能够获得充分的感官享受,管它明天是个什么样子!但更为需要它的还是秦国:让你们在末日来临之前去极乐逍遥吧,老子就可以无所顾忌地逐个吞并其余五国啦!
一座不设防而又似乎置中原大战于局外的都城,对那些正不断从死亡线上挣扎、脱逃出来的五国残余贵族来说,更无疑是最好的避难所和天堂。
于是历史出现了一次逆向轮回:两百多年前,当中原诸国由“三晋”首倡其声,纷纷掀起改革热潮的时候,一些旧的奴隶主贵族慑于新兴地主阶级威势纷纷西逃投秦;当时政权还暂时控制在守旧势力手里因而顽固地抵制改革的秦国,成了他们心目中的避难所和安乐乡。历史前进了两百多年,昔日关西那个童头豁齿的垂暮老人,忽然变成了一头撒野中原的猛虎,而在春秋第一霸主齐桓公的故土齐国,却奇迹般地出现了一个“太平乐世”,这样逃亡的方向便由西转向了东。
这些前前后后来自五国的流亡者,该是一个为数不小的群体,只是史书上无法找到确切的记载。《战国策·齐策六》记录了即墨大夫一次对齐王的谏言,其中提到了这样两笔数字:
夫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
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数。
“三晋”,指韩、赵、魏;“鄢、郢”为楚。“阿、鄄”、“城南”都是齐国地名。
单是这两笔数字加起来,就有两百左右。他们都是中原诸国的一些所谓簪缨袍笏之族,先后逃亡到齐国来避难的。估计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已经破灭的废墟中挣扎着逃亡出来,可说已是赤条条一无所有,成了十足的亡命之徒。另一种是预先逃亡的,那肯定是身携巨额黄金珠宝,以至成群的姬妾美女,专门来寻找享受的。无论哪一种情况,他们带给临淄的,都只能是没落和腐朽!
临淄是一个由齐太公吕尚开辟、营建起来的古老城市,它在战国诸国国都中规模最大,也最繁华。临淄同时又是中原文化的一个圣地,在桓公、威王、宣王之世,在城区的稷门先后聚集过当时第一流的饱学之士,从淳于髡、驺衍,到鲁仲连、荀况等等,形成后人称为“稷下之学”而名闻天下。据史书记载,战国时期,临淄城中共有七万户人家,如以每家五口计算,就有人口三十五万。市民比各国都要富裕。当时的纵横家苏秦曾经作过这样的描画:“临淄之涂(通“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气扬。”尽管运用了文学手法,不无夸张之处,但一个精神高扬、文化繁荣、百业兴旺的都市形象还是跃然纸上。这不仅是齐国的骄傲,也是中原的骄傲!
但是,那个充满着健康向上的进取精神的临淄,已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的临淄已成了一个畸形发展的病态都市。最热闹的场所是斗鸡、走狗、六博、蹴鞠等处;最时行的职业是娼妓和歌舞伎;最受崇拜的人,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英雄,而是出入高楼深院、能够随心所欲地窃到珠宝的盗贼!东城门外,便是都城因以得名的淄水。水面常常漂浮着一些无名尸体,不是因谋财而被害的人,就是因厌世或愤世的自尽者,随同污垢和败草一起默默地由南向北流去……
临淄,你这个不设防的都市,还能苟存多久呢?
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以疾风扫残云之势接连取得攻灭五国大胜的秦王嬴政,却还从容不迫,事情办得有章有法。他决定这一年的重点是做扫尾工作。于是就像《史记》本纪所记载的那样:“大兴兵,使王贲将,攻燕辽东,得燕王喜。还攻代,虏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北,降越君,置会稽郡。”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到这一年五月,十几年来,这位不知下达过多少个杀人毁城命令的国王,第一次有了一道欢快的诏谕:“天下大酺。”
大酺三日,与民同乐,这已经摆出了一副天下共主的气派。
这“天下”,自然也包括临淄和齐国在内,因而想必齐王建和他的臣子们也是一起畅怀大饮了的。很可能要到酒过三巡之后,才渐渐品尝出这酒的味道不对头:他齐王建是作为一国之王与秦王平起平坐的资格祝贺他取得削平五国大胜呢,还是作为一个大统一国家的臣民恭贺圣王的丰功伟绩呢?这么一想才如梦初醒,感到事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一时慌了手脚,赶紧召集群臣来商议对策。臣子中后胜之类都是被秦王用金银珠宝喂饱了的,自然力劝齐王建作为属臣赶快西行朝秦。齐王建明知长途跋涉两千余里,跪在人家脚下称臣磕头,那滋味并不好受,但事出无奈,只好硬硬头皮跨上了乘车。
车驾刚驶出临淄城雍门,据《战国策·齐策六》记载,这时候掌管雍门兵马的官吏急急跑来跪在马前进谏说:劳大王留驾,臣有一事相请!
齐王建说:你说吧。
雍门司马说:臣愚陋,请大王晓谕:臣民所以要拥立国王,只是单单为了立王而立王呢,还是为了卫护国家社稷?
齐王建说:当然是为了国家社稷!
雍门司马说:既然立王是为了卫护国家社稷,大王怎么可以置国家社稷于不顾,自己一个人去朝秦称臣呢?
齐王建不由一震,想想又觉得他说得有理,便下令返车回宫。
数十年来,齐国执行的都是那个“双不”方针,这时候却忽又手忙脚乱地采取了一个更蠢的措施:“齐王建与其相后胜,发兵守其西边,不通秦。”(《史记·秦始皇本纪》)一个人长期沉溺在腐朽的淫乐生活之中,会使他的智能退化到何等地步,齐王建倒是典型一例。“发兵守其西边”,你守得住吗?就是让你守住了西边,如今中原大地几乎全成了秦王天下,他不走“西边”,南边、北边不都随他走了吗?
事实上,此时秦王嬴政早已不把齐国放在眼里。请看他下给王贲的命令何等轻松:“将军平定辽东后,可乘破竹之势,便可取代,无烦再举。自代至齐,归途南北便道也。愿以将军之余威,触电及之,遂成大业。”
听听,“触电及之”,这是何等口气!
事实也正是如此。
英俊少年王贲,在生擒代王嘉后,马头一拨,率领数万之众,扬鞭南下,过高阳,越河间,跨黄河,一路如入无人之境,眨眼间破城入临淄。齐王建“守其西边”策略顿成泡影,仓促间只得跪地求降。于是几天后,便出现了本书《引言》中写到过的那一幕——
清晨,几匹疲惫的老马拖着几辆破旧的乘辇,驶出了已从国都降为郡邑的临淄。乘辇里坐着满脸沮丧的齐国末代国王田建和他的嫔妃、亲从。乘辇前后数十匹关中高头大马上,是负责押送的秦国将士,咄咄逼人。他们的行程终点,将是距此数百里太行山下一个叫作共的小山城,那里便是这位亡国之君的流放地。
发生这一幕的时间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即公元前221年。
中原树上的最后一片黄叶也已经凋落;但是,只要另一个春天到来,它仍然会长出繁茂的绿荫。
六国之亡的历史评说
胜利有胜利的来由,失败有失败的原因,历史最终归结为必然。
对六国之亡,历代都有所论及,我选摘较为系统的三家,都是宋代的,以概一般,并略作点评。
司马光是生活于11世纪的著名史学家,他在《资治通鉴·秦纪二》中作了这样评论——
从(通“纵”)横之说,虽反复百端,然大要合从者六国之利也。昔先王建万国,亲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飨宴以相乐,会盟以相结者,无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国也。向使六国能以信义相亲,则秦虽强暴,安得亡之哉!夫三晋者,齐楚之藩蔽;齐楚者,三晋之根柢,形势相资,表里相依。故以三晋而攻齐楚,自绝其根柢也;以齐楚而攻三晋,自掘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
六国若能以信义相亲,即使秦国再强大,也不会灭亡。这是司马光的中心论点。文中追溯了历史,认为先王分建列国的宗旨,就是为了诸侯间相交、相乐、相结,共同保护国家。可是六国却偏偏违反了先王的宗旨,不是自撤藩蔽,就是自绝根柢,致使秦国有机可乘而遂行其志。最后一句是讥讽齐王建的:“盗将爱我而不攻”,活画出他那副傻乎乎的昏庸相。
与司马光大致生活于同一时代的苏洵,就是大文学家苏轼(号东坡居士)的父亲,写过一篇专论六国之亡的名文《六国论》,论点鲜明,笔锋犀利,剖析透辟。全文近八百字,为节省篇幅,只好摘录其要。文章一开头就点出了全文要旨——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所谓“赂”,指列国割让土地,贿赂秦国,求得苟安。文章接着算了这样一笔账——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也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
说各国因赂所失的土地百倍于因败所失,自然是一种夸张的修辞手法,用意无非是强调“赂”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文章接着以充满感情的文字,说明列国先祖创业维艰,尺寸之地也得来非易,如何可以如此轻易予人,而且嬴秦贪得无厌,你“奉之弥繁”,它反而“侵之愈急”。最后说——
呜呼!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势,而为秦人积威所劫,日削月割,以趋于亡!
苏洵此文,原是有感于当时赵宋王朝一味向契丹输银退让而发的,这一点与本书无关,可以略而不论。就六国之亡而言,赂地也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原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弱国若以赂地予强国求得自保,必然导致敌我强弱之势以反比例的形式迅速向前发展,结果只能是加速自己灭亡。
第三家是苏辙,即苏洵之子,苏轼之弟。通常所说的唐宋八大家,苏氏一门竟占了三席,实在是文学史上的千古佳话。苏辙似乎有意要与父亲比试个高下,同以《六国论》为题成篇,果然同样成了广为流传的名文。苏辙的文章着重做在一个“势”字上。与苏洵的一开篇就揭示全篇要旨不同,他却是从容道来,层递设问:何以有“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六国,反而会败亡于秦呢?然后就势托出一句道:“不知天下之势也!”那么什么是当时的“天下之势”呢?——
夫秦之所与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郊。诸侯之所与争天下者,不在齐、楚、燕、赵也,而在韩、魏之野。秦之有韩、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韩、魏塞秦之冲,而蔽山东之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韩、魏也!
这就是作者心目中的战国之时的天下大势。韩、魏是中原与秦国之间的一道屏障,双方争夺的焦点就表现在一个要破屏东进,一个要护屏自卫上。文章接着回顾了秦国历史,以范睢、商鞅致力于攻取韩、魏获得成功,魏冉远涉千里袭取刚寿遭致失败为据,证明秦国如果越过韩、魏而远攻他国,便是秦国的“危道”。由此得出结论,中原诸国是否采取支持和保护韩、魏的策略,便成了存亡续绝的关键——
夫韩、魏不能独当秦,而天下之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韩亲魏以摈秦。秦人不敢逾韩、魏以窥齐、楚、燕、赵之国,而齐、楚、燕、赵之国因得以自完于其间矣!以四无事之国佐当寇之韩、魏,使韩、魏无东顾之忧,而为天下出身以当秦兵。以二国委秦,而四国休息于内以阴助其急,若此可以应夫无穷,彼秦将何为哉?不知出此,而乃贪疆场尺寸之利,背盟败约,以自相屠灭,秦兵未出而天下诸侯已自困矣!至于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国,可不悲哉!
三家都是大手笔,各有侧重地剖析六国灭亡的原因。苏辙从当时天下大势出发,论述了是否厚韩亲魏是列国存亡的关键;苏洵和司马光则分别从六国与秦国关系和六国相互关系上揭示了导致灭亡的弊病。综合三家文章,大体可以较为全面地看出六国在战略策略上的失误。
但我还是想把问题引申一下:如果六国采取了三家文章中所说的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否就不会亡了呢?那种七雄纷争的局面是否就会永世长存了呢?恐怕也不见得。当然历史的发展都是单线的,都是已然,不存在或然。我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即非历史观点。我只是想说明,六国之亡是由物质因素,即主要由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和由此派生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所决定的,因而是客观必然的,并非单是由于主观上的失策。战略策略上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延缓或加速灭亡的到来,但终究要灭亡,这却是必然,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些早已成为常识性的话,本书《引言》里已说过一些,不再重复。使我感兴趣的是由此细想下去引出的另一个话题。三家文章都力透纸背,经他们犀利的笔触一剔发,赂秦一类策略的危害便洞若观火。那么是否当时六国的决策层都那么低能,连割地赂秦,只能使秦国愈强、自己愈弱这样一些道理都一点不懂呢?恐怕还不至于。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智能大昂扬的时代,中原六国都有自己第一流的智囊团。这里确实有一个智能问题,但首要的却不是智能问题。再高的智慧,有时却会受拘于眼前一点实际利益而变得苍白无力。列国因何要赂秦?苏洵文章中有一句话:为求“一夕安寝”。列国为什么不能厚韩亲魏?苏辙文章也已点明:“贪疆场尺寸之利”。一叶有时可以障目。就因了这“一夕安寝”和“尺寸之利”,使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得了近视症:既看不到“天下之势”,也看不到“日削月割,以趋于亡”即将降临的必然结果,从而采取了这类饮鸩止渴的慢性自杀对策。
那么六国君主又为什么大都会患这种近视症呢?这恐怕也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所得。是一个没落的群体、一种没落的制度,长期养成他们这样的。苏洵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
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
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历史上,开国君主,或中兴君主,特别在他们创业之时,都是有胆有识,能够面对艰难困苦而坚毅不拔、发愤有为,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性格优势和人格力量。具有这种性格优势和人格力量的人,才敢于“暴霜露,斩荆棘”,而这种艰苦创业的过程,又冶炼和发展了他们的这种优势和力量。这就是后人读他们传记时,常常会感受到一种激励奋发之气的原因。坐享其成的君主就大多不是这样,而一当进入没落时期,多数王室成员更是沉溺在无休止的感官享受之中。他们根本不知道艰苦创业为何物,因而一旦战祸临头,首先想到的决不会是如何去迎战,而只能是如何去逃避这场战祸。既然人家喜欢土地,那就“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地割吧,只要它能换到“一夕安寝”又何乐而不为哉!
如此说来,六国采取那些饮鸩止渴的对策,也并非由于一时疏忽,而是事物发展之必然。
历史老人安排得很周到:他为了埋葬一种制度,同时必然使守护这种制度的人,将奋发进取的心志消磨殆尽,一个个变得鼠目寸光,蝇营狗苟。所以不是别人,首先由他们自己,刨土掘坑来埋葬这种制度。杜牧《阿房宫赋》的结语是闪烁着历史真理光辉的名句:“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所以,秦王嬴政吞并六国的大决战,既是实力、智力的一次大较量,也是人性、人格的一次大搏杀。失败者和胜利者最后都可以从性格和人格上找到依据。
从感情上说,我实在无法接受嬴政还在儿童时期就说过的“胜利者有权惩罚失败者”那句话,但在理智上却又不能不承认,因为其实历史正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在多数场合下对失败者的惩罚也是对人性弱点的惩罚。失败而不受惩罚并不是一件好事。广义的失败,人的一生不知要经受多少次。人们正是在不断接受因失败而遭致的惩罚中,逐渐成熟起来;人性,也正是在不断接受惩罚的洗礼中逐渐走向完美。
但无论如何,六国灭亡了,多少无辜的人也为此丧失了生命,还是不能不令人同情。最后就让我们来听一曲挽歌吧。这曲挽歌是一个音乐家用筑这种乐器演奏出来的,20世纪40年代诗人郭沫若曾将它写成史剧,题目就叫《筑》。
六国之亡的尾声:挽歌
中原六国都有数百年根基,一朝倾覆,对于当时当地的人们,无疑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要经受长久的痛苦煎熬之后,才不得不逐渐接受这一现实。
其间,肯定有不少以血肉之躯写出的挽歌,只是没有记载下来罢了。仅有的一曲,是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因为荆轲立传而顺便记录下来的,它的主人公就是高渐离。
高渐离是“筑”这种古老乐器的演奏家。筑似筝而小于筝,颈细肩圆,有十三根弦,以竹尺击弦发音。在邯郸街头,在易水河边,我们已经听到过他时而悲风泣雨,时而金戈铁马的演奏。当荆轲“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而去时,他一定还在易水边伫立很久。他们是好友,他知道他这一去永无回返之日。
果然,不久便是荆轲被杀,太子丹被斩;接着便开始搜捕太子丹和荆轲的宾客亲友。高渐离不得不收藏起心爱的筑,隐姓埋名,四处逃亡。
他流浪到原属赵地的巨鹿郡一个叫宋子的地方,大约就在如今河北赵县东北侧的一个小地方,总算找到了雇主,在一家酒馆里当酒保,便暂时居留了下来。
他无法不怀念荆轲,无法排遣国破家亡的哀愁,更使他痛苦的是,他现在已不能借助筑来抒发自己的满腹郁愤了。
一次,正当他劳作时,蓦地不知从哪里传来了悠扬的筑声,立刻兴奋得心都颤抖起来。
他情不自禁地循声走去。
是主人家的堂上有位客人在击筑。
那特具魅力的乐音,勾起了他往昔生活的一个个画面,使他如醉似迷。两脚在堂下缓慢地来回徘徊着,不肯离去。间或自言自语地评点一两句:哪里演奏得恰到好处,哪里有所不足。有人把这些情况去报告了主人。主人出于好奇,就把他找去要当场试一试。开头,他还有些犹豫,怕暴露真实身份会带来危险;但筑是他的第二生命,它在向他招手,他不应抗拒它的召唤。他激动地抱起了筑。一串乐音从竹尺与筑弦的连续击撞间倾泻而出,像满把珍珠撒到了宁静的水面,围听的人众立刻一个个显露出惊奇的神色。他演奏了一曲《易水谣》,便是在蓟城街头多次为荆轲伴奏过的那一首。全曲终了时,人们才从屏息静气中突然鹊起,纷纷争相赞叹。酒馆东家十分高兴,特地开筵赏酒,尽兴才散。
高渐离回到自己住处,却再也无法平静。他觉得与其这样隐居着在担惊受怕中度过余生,不如索性回返真我,重新抱起心爱的筑,用它来替代自己内心,或痛苦地呻吟,或亢奋地呐喊,那样即使死去,至少还能与音乐同在。于是他翻拣行囊,找出过去穿的学士衣服;又从箱底捧出珍藏着的那张筑,穿戴整齐了,屏息凝神,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十三弦中去,演奏一曲近日来他在腹中已经谱好了的《载驰》。没有想到就在这时,他的前后左右已立满了闻讯赶来的听客。不是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而是因为同有羁旅亡国恨,使他们顷刻间成了相知。酒馆主人再一次作东,恭恭敬敬把他请到堂上,相互施礼后,正式请他演奏。
《载驰》就这样第一次由诗句化作了筑声。
高渐离是根据四百多年前许穆公夫人的诗谱的曲。穆公夫人是听到她的故国卫国已被狄国攻破,骑着快马回去吊问的路上写就此诗的。高渐离长叹一声,理弦,拊筑,庄重地开始演奏。“载驰、载驱……”女诗人的诗句在他心上流过,急鼓似的马蹄声从弦上跳出。他忽而感到手里拿的已不是竹尺,而是马鞭。马在奋蹄疾奔,挟带着浓郁的山野气息的风迎面扑来。渐渐地,出现在他面前的已不是卫国的国土,分明是燕国的山山水水;他就驰骋在燕山脚下,不远处,那条飘曳不停的银色带子,正是他们的母亲河易水……
音乐带着激越、跳跃的旋律,不断推向高潮。
听客们都感染到了一种置身马背的感觉,情不自禁地颠簸起来。
不知谁追着节奏轻声哼了句“载驰、载驱”,众人跟着相和,很快汇成了大合唱——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
驱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则忧……
众人一个个泪流满面,跟着筑声尽情地倾泻着各自胸中的怨愤。高渐离双手忘情地按弦和击打着,突然一仰头,两行泪泉滚流而下。他边奏边随着众人引吭高歌——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
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从这天开始,宋子城里的人纷纷来邀请高渐离去作客,每次又照例要请他击筑。高超的演奏技艺使他名声远播,甚至传到了咸阳。偏偏秦王嬴政也很喜欢听击筑,于是他又被召进了秦王宫。
高渐离走在当年荆轲走过的台阶上,一步一步去接近秦王。他自然想到了好友被惨杀的情景,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刚要上殿,侍卫官却突然前来阻止,命令他跪在殿下接旨。
秦王问了他姓名,他以改换过的姓名作答,秦王就命令他演奏。
他原已做好一旦获得接近机会,就奋起完成好友没有完成的使命的准备。如今非但没有接近的可能,又要被迫为故国和故人的仇敌演奏,这却是他此前没有想到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若是奋起反抗,那是一种愚蠢的无谓牺牲。仓促间,他演奏了一首秦诗《蒹葭》。苍翠的芦荻,叶片上结着薄薄的初霜。一个男子在河边徘徊,望着清凉的水波,寻觅着他梦寐以求中的情人。他尽量演奏得清丽委婉些,希望能赢得秦王好感,或许能有机会接近。果然秦王怡然箕踞于大殿之上,一手在几案上轻点节拍,仿佛正沉浸于一个美好的世界中。但就在这时,近旁有个侍臣对秦王说了几句什么,并向殿下的高渐离指了指。秦王霍然仰起,双目怒睁,大喝一声:推出去,斩首!
高渐离还没有来得及从幽美的音乐境界中脱出就猛然被几个武士拖起,知道自己就要被拉出去砍头,待要大骂几句时,离秦王已经很远。他很后悔自己刚才演奏过于全神贯注了,以至失去了此生唯一可以当面痛骂暴君的机会。
但是后来高渐离竟没有死,而是被押到了一个陈设高雅只是周围布满了卫士的公馆。到这时他才知道,是那个侍臣认出他是荆轲好友秦王才勃然大怒的,而他之所以终于没有被杀,是秦王已忘不了他的演奏。
秦国国君爱好音乐是有传统的,秦穆公、秦昭襄王都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对中原音乐尤为倾慕。秦王嬴政能歌善啸,而筑这种最擅长营造激昂、悲壮之气的乐器,特别使他心醉。正因为一个国王要听一个罪犯击筑,这个罪犯就侥幸地保留了一条性命和一双手。当然,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还得设法除去他可能危害自己的其他器官。
不过,高渐离还蒙在鼓里。他倒好,索性在公馆悠悠扬扬击起筑来。反正主意早已拿定了的:如果秦王还要他击筑,只要有机会,他决不会放弃使用早已准备好了的武器!
但是,就在这天晚上,他被带至一间漆黑的小屋,先是闻到一股冲鼻的秽臭,接着是一阵剧痛后便昏厥了过去。醒来时,眼前已是一片无穷无尽的黑暗,而且是永远的黑暗。
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秦王嬴政认出高渐离后,便下令“矐(huò)其目”。矐,意为失明。在这里用作动词:使失明。就是说把高渐离的眼睛给弄瞎了。用的是什么方法呢?《史记索隐》说:“以马屎熏令失明。”
痛苦和黑暗只能愈益加深高渐离的仇恨。这仇恨在他心中不断积聚,渴望爆发。每当他应召去为秦王击筑时,那种从胸口燃起的复仇的渴望,几乎要把心肺都炸裂。但他深知爆发已只有最后一次了,因而必须十分珍惜,决不可轻易使用。为此他得忍受双倍的痛苦来克制自己,一有机会便向秦王跪谢不杀之恩。他知道秦王所以要把他推入黑暗的深渊,是要使他永远看不清袭击的方向,从一个危险的仇敌变为一具只会击筑的躯体。为此,他以最大的毅力暗暗磨砺自己的方位感,很快做到在三丈之内择取其中任何一点犹如在十三根弦上按捺任何一个音阶一样准确。但在秦王面前,他有意装出东西南北莫辨的傻样,有时甚至故意在台阶上跌得头破血流。与此同时,他的演奏也越来越精妙。
他的韬晦之计收到了成效:武士们渐渐放松了警戒,秦王听演奏时离他也越来越近。
这一天,高渐离要向秦王献奏他的一首新曲:《凤鸣》。
他所以要谱写和演奏此曲,自然煞费苦心。此曲所据为秦氏宗族的一个美丽的传说故事。秦王嬴政最为崇拜的先祖穆公有女名弄玉,善吹箫,与当时一位同样善吹箫名叫萧史的学子结为夫妇。穆公专为他们筑一华台,这对少男少女常常在台上吹箫,并作凤声,雌雄唱和,引得有凤来栖,晨昏长鸣,因名其台为凤鸣台。
演奏前,高渐离特地焚香跪拜,以示对秦氏先祖的崇敬和对音乐的虔诚。真正的目的自然为了麻痹秦王。
他在香烟袅袅中落座,双目微闭,两手缓缓按几,在静穆中调整着微微的呼吸。
但他的心却在愤怒地狂跳。因为他分明感到那暴君已在移席向他近来,甚至那粗大的呼吸声也已隐隐听到。
他还得遏制自己,且用筑弦声把一对少男少女的倩影引上凤鸣台来。
箫声悠悠,有五色祥云从天空飘来。
“凤兮,凤兮……”早已恭立在两廊的宫女低声和唱。
他的按在弦上的手在微微颤抖。他的感觉,准确地告诉他:秦王就在他左侧,近在咫尺。筑声殷勤地向凤凰发出呼唤——
凤兮,凤兮,
泰山之巅风凄;
凤兮,凤兮,
岐山之竹日稀……
当人们都陶醉在音乐的梦幻中时,他的拂弦的左手趁机拨开了筑腹的共鸣箱,那里早就准备着一块沉重且有棱角的铅块,现在已随时可以向仇敌掷去。
凤兮,凤兮,
有女伯益之裔;
凤兮,凤兮,
凤鸣台上可栖……
突然响起了呼喊和混乱。铅块飞向秦王额头,在猝不及防间,却被左旁一个武士扑来用身体挡住。武士倒在血泊中,铅块滚落在台阶上。
高渐离知道没有击中仇敌,又用尽全身力气将手中的筑向目标掷去。筑在秦王胸前撞得粉碎,但它无法造成致命。
当高渐离被推出去斩首时,他已无筑可击,只好仰头高歌。他唱的还是那首《载驰》。头颅已从肩上滚落,嘴唇却还在张合,周围的人分明都清晰地听到了他那生命的绝唱——
载驰载驱,归唁卫侯。
大夫君子,无我有尤。
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
下一章读者将看到大秦帝国的一个轮廓风貌。
这个新生的帝国,如果把它比作一个人,他是那样矫健强悍;比作一座建筑,它是那样嵯峨辉煌。它集中了当时第一流知识精英,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大改革,并运用帝国权威强力推行。又动员起数百万即超过帝国十分之一的人力,一面南征北伐,一面进行筑宫殿、辟驰道直到造长城、辟“地上天国”等众多宏大工程。它何来如此巨大的创造活力?何以一时间拥有如此宏富的财力物力?简直令我们后人难以置信!
在短时间内如此强力运作,如果是一个人就会耗尽精血,如果是一座建筑,也会不胜重负。这样当你切近地去细察这个轮廓画像时,不难从中发现一个悖论:由它的成功可以推出它的灭亡;或者说,正是它的成功导致了它的灭亡。
不过无论如何,秦帝国纵然短命,由它创始的帝王集权专制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举措,都大体为后世所继承,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两千余年。 人生必读经典历史丛书:时代帝国三部曲之大秦帝国(上 下)(套装共2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