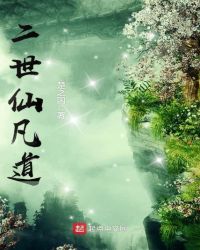把别人铭记在心的人是深情的人——读李致散文集《铭记在心的人》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把别人铭记在心的人是深情的人——读李致散文集《铭记在心的人》
江永长
说李致同志(以下称致公)是个深情的人,一是和他交往中建立起来的一个基本的认识,二是读他的书和文章的一个鲜明的感觉。
我认识致公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他当宣传部副部长,来文联和作协开会,并不坐在主席台上发言,而是和文联、作协的领导坐在一起,讨论事情,我感到这个领导有点个性,有点与众不同,听人说,这是李部长,出版家、作家,就认识了他。其实,那以前还是读过他编辑出版的书的,但一个才从学校里毕业出来不久的乡下小青年,胆子小,见到领导,只远远的看,不敢上前去打招呼,不敢自我介绍,所以那以后的几年,都是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我估计,致公认识我大约是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了。他当省文联主席后,特别关心《四川文艺》报,一次,主动来编辑部看望我们,问过了我的名字,我们就算是互相认识了。这以后,再见到我时,他就能叫出“小江”来,声音是缓慢柔和、尾音带一点轻微鼻音的那种,听着特别慈祥亲切。我也大胆了些,远远的看见了他,就主动过去问候。致公作为出版家,对《四川文艺》报的指导是很专业的,对我们的工作的改进起到了明显的效果,报纸不断刷新面貌,质量也有大的提高。他除了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外,还特别关心编辑部年轻人的进步,职称是否评上了?级别是否晋升了?待遇是否解决了?他还在文联领导面前为我们呼吁,真解决了不少问题。
和致公交往中印象特别深的有这样几件事:有一年,我陪《中国艺术报》的副社长宁静同志到致公家去拜访,宁静同志是成都人,那次他们聊了许多成都往事和人物,后来,他们发现好像还有一点远亲关系,便有人事沧桑之感,离别时,致公送客至楼下。另一次,武志刚老师和我去商业街的医院看望致公,那时致公的夫人在那家医院看病,他自己在那里检查身体。他和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双方都非常快乐,但由于是在医院,不能尽兴,致公就约我们以后到他家去聊。后来,他的夫人不幸去世,他很悲痛,我们不好去打扰他。过了些时日,他打电话来邀我们了,我深感致公是个言出必行的人。这一次,致公用了小半天的时间和我们聊天,他还准备了不少资料给我们看,让我们大开眼界,了解了很多的人物和事情,很有收获,也很快活。致公知道我能写一点小东西,便不时鼓励我不要放下笔,不要荒废了时光。去年,我在《四川文艺》报上发了一篇写母亲的小稿子,之后不久就接到了他的电话,谈了他的读后感,认为我的文字感情真诚,但显得过于拘谨,好几处言犹未尽,该说的话没有说出来,建议我以后作文放开一点,致公对我写作的关心让我喜出望外,他的评价完全说到了要害处,我非常敬服,也非常感激他。
现在来说说我读致公《铭记在心的人》一书的一些感受。
我记得有一次通过网络和致公交流过对他的散文的一个基本印象:真事真情。我感到,读《铭记在心的人》这本书的一个最突出的印象仍然是一个“真”字,真事真情。
先说真事,10年前,致公在《“我的人生”总序》里说“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经历,不论于人于己于事,务求真实,不对事实作任何加工。这是我恪守的原则,不越雷池一步。如有误差,一经发现,尽快改正。”《铭记在心的人》一书有将近60篇文章,全是写的真人,其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贤达,知名文艺家,以及致公的亲朋旧友,等等,发生在这些真实人物身上的故事,致公是自己知道多少、能够核实多少就写多少,道听途说的、核实有困难的、拿不准的都不写。致公写真人真事的依据一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另外,就是靠着他积累的大量资料,包括照片、信件、书籍、电子文件,等等,我几次到致公家去,哪怕就是聊天,当说到某人时,他也习惯出示照片为证,说到某事,往往要拿书信或者笔记为证,不虚妄,不似是而非,不想当然尔。聊天尚且如此严谨,作文时的求真精神自然可想而知了。
真情,首先是建立在针对真人真事,有感而发、有情要抒的基础之上的。致公在《“我的人生”总序》里说“回想自己人生几十年,时代几度变迁。许多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我曾为之喜悦或痛苦。这些人和事,也可以说是时代的某些缩影或折射,也许有一些‘史料’的价值;我有感情需要倾诉,也想借此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剖析自己的过去。”《铭记在心的人》一书表达出来的情感,无疑是致公真感情的倾诉,是他的喜悦和痛苦,这些真感情,甚至大量的直接从文章的标题上就流露出来了,致公的文章标题的浓烈的情感色彩是他的散文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我想这与致公的一贯文风和喜欢是分不开的,他说“我喜欢真诚、朴实、动情、幽默的散文。不无病呻吟,不追求华丽,不故弄玄虚,不作秀,不煽情,不搞笑。”出于真诚而表现出来的感情,自然有感动人心的魅力,在追忆儿时伙伴的《冬娃儿》一文的结尾处,有这样的话:“人世沧桑,以后的事就难说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冬娃儿应该健在。我真想见到他,叫他一声‘冬娃儿哥!’但这愿望能实现吗?”这是这篇文章的最后几句话,也是《铭记在心的人》一书的最后几句话,每当我读到这里时,我总能感到一位老人追忆逝水年华的美好情怀,总能感到青春一去不复返的人世沧桑,想想也是,我才40多岁,但猛然回首时发现,已经有几个儿时的伙伴,有几个同学,甚至还有一个同胞弟弟、一个表哥、一个内弟,皆已去世了。致公比我年长得多,经历也更为丰富,他对人世的认识和理解自然比我练达得多,自然也更加淡定,但我从上面的那段话中却感到了他的火热的心,他想念少年时代好伙伴的那份真诚的心让人动容,一位老人想再见到少年时代好伙伴的善良的愿望是那么的单纯、美好,谁又忍心去冒昧地触碰呢?所以,我也想对致公说“是的,我也相信:‘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冬娃儿应该健在。’”致公就是这样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感情的。其次,致公散文的真情还特别地通过对自己的剖析而表现出来。敢于自我批评和反省的人是真诚的人,是有智慧的人,更是勇敢的人,我觉得,致公的散文中对自己剖析的那些抒情性的话语显得特别有力量,也格外让我受益。在流行自我包装、自我运销的当下,自我剖析,自我反省,无疑是一种日渐稀有的可贵品格了,所以,这些话特别打动我,也特别值得我学习。
读致公的散文,就是在阅读一个经常把别人铭记在心的老人的人生阅历和真情实感,就是在听一个真诚的人、一个深情的人讲述。
2011年5月6日 李致文存:我的人生(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