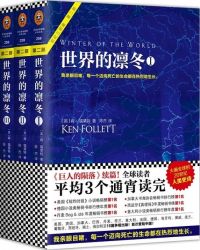第47章 1940年,阿伯罗温(5)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世界的凛冬(全集)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博伊抽完烟的时候,她仍然手足无措。博伊说:“该上床了,你要先洗澡吗?”
黛西不知道该怎么办,站起身走进卧室。她缓缓脱下为劳埃德穿的衣服,洗了把脸,穿上最无趣的一件睡袍,爬到床上。
博伊已经醉得不轻了,但一上床还是向她求欢。她突然觉得害怕极了。“很抱歉,”她说,“莫蒂默医生说三个月不能做爱。”莫蒂默医生没说过这话,他说止血以后就能做爱。黛西感到心里有愧,她本想和劳埃德激情一宿的。
“什么?”博伊生气了,“为什么啊?”
她灵机一动:“很快恢复房事的话,我可能就没机会再怀上了。”
博伊相信了。他很想要个继承人。“那好吧。”他转过身去。
很快他就睡着了。
黛西怎么也睡不着,心里一团乱麻。她能偷跑出去吗?必须得套几件衣服——她不可能穿着睡袍到处乱跑。博伊睡得很沉,但经常起床撒尿。如果撒尿时发现她偷跑出去,之后又看到她着装整齐地回来他会怎么想呢?她又能找出什么样的一套说辞说服他呢?夜里女人在乡间别墅四处乱转只会有一个理由。
只能让劳埃德忍了。想到劳埃德一个人孤独伤心地待在满是灰尘的套房里,黛西就伤心得要死。他会穿着制服在那儿睡着吗?如果不盖条被单的话,他会着凉的。劳埃德会觉得她有急事,还是会以为她在无意中把他晾在一边了呢?也许他会觉得很失落,然后迁怒于她。
泪水从黛西的脸上奔流而下。好在博伊睡得很死,她可以尽情地流泪。
下半夜,她终于睡着了。梦中,她要去赶一班火车,但不断被各种愚蠢的小事耽搁:出租车开错地方;必须拿手提箱走很长一段路;车票不见了;到了月台,却发现搭乘的是一辆好几天才能跑到伦敦的公共马车。
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博伊已经去浴室刮胡子了。
黛西彻底心灰意冷了。她起床穿上衣服。梅茜在为她做早饭,博伊已经吃起了鸡蛋、培根和奶油吐司。吃完早饭已经九点了。劳埃德说九点出发,他也许已经拿着手提箱出门了。
博伊站起身,拿着报纸进了厕所。黛西知道博伊的这个习惯:他会在厕所里待上五到十分钟。她不再犹豫了:匆忙从地下室走上楼梯,朝前厅奔了过去。
劳埃德不在门口,他一定已经离开了。黛西的心猛地一沉。
不过他会走去火车站:只有病人和有钱人才会为区区一英里路叫出租车,也许还能追得上他!黛西连忙冲出了门!
劳埃德在她前方四百码的车道上拿着手提箱举重若轻地行走,黛西的心一下子跳到了嗓子眼。她放下顾忌,撒起脚丫跑了起来。
一辆被军人们称为“蒂利”的皮卡从黛西身旁开了过去。让她失望的是,皮卡在劳埃德身边慢慢停下了。“别上车!”但劳埃德离她太远,没有听见她的喊声。
劳埃德把手提箱扔到皮卡后斗,坐在司机身旁的副驾驶座上。
黛西拼命追赶,但皮卡已经不可能追上了。车一启动,就像离弦的箭一样开走了。
黛西停住脚步,看着“蒂利”开过泰-格温的大门,渐渐消失了。她拼命克制住了想哭的冲动。
过了一会儿,她转过身退回屋子。
前往伯恩茅斯的途中,劳埃德在伦敦住了一晚上。这天是1940年5月8日星期三,劳埃德在下议院的旁听席上旁听了决定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命运的辩论。
议院像剧场一样吵闹而无序:旁听席又窄又硬,楼下的议员们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影影绰绰。旁听席全都坐满了。劳埃德和继父伯尼通过楼下正和比利舅舅一起坐在议席上的艾瑟尔的影响力才好不容易搞到票。
劳埃德没机会问生身父母的事情: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当前的政治危机上。劳埃德和伯尼都希望张伯伦马上辞职。纵容法西斯主义的人缺乏带领英国参战的公信力,挪威的惨败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辩论前一天晚上就开始了。艾瑟尔说,除了受到工党议员的猛烈抨击外,张伯伦同样也受到了本党议员的抨击。保守党议员莱奥·艾默里在辩论中引用了克伦威尔的名言:“不管你们做过什么好事,你们占据此位太久了。我告诉你们,离开吧,别再让我们看见你们。以上帝的名义,走吧!”这席出自同党议员的话简直太残酷了,比两边议席响起的“滚、滚”声还要伤人。
劳埃德的母亲和其他女议员,集中在威斯敏斯特宫的女议员专用房间,决定发起一项针对张伯伦的投票。男议员无法阻止她们,于是纷纷决定加以声援。周三女性议员的议案提出以后,辩论演变成针对张伯伦的投票。首相接受了这个挑战,并号召朋友们站在他这边——劳埃德觉得这是种软弱的表现。
今晚,攻击依然在继续。劳埃德津津有味地聆听着议员们的唇枪舌剑。他痛恨张伯伦对西班牙施行的政策。1937年到1939年的两年间,在德国和意大利不断给西班牙叛军予以人力和物力支援,美国极端保守主义者陆续把石油和卡车出售给佛朗哥的同时,张伯伦却依然协同法国施行“不干涉”的政策。如果有哪个英国政治家能容忍佛朗哥的大规模杀戮,那这个人只能是内维尔·张伯伦了。
“张伯伦不应该为挪威的惨败负责,”伯尼在会场稍稍平静时对劳埃德说,“温斯顿·丘吉尔是海军部的首脑,你妈妈说推动这次参战的人是他。在面对西班牙、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软弱而巍然不倒之后——张伯伦要是因为不是自己犯的错而下台那可是太讽刺了。”
“所有错归根结底都是首相犯下的,”劳埃德说,“做领袖就要担这个责任。”
伯尼干涩地笑了一声。劳埃德明白,继父是认为年轻人想问题太简单了,但出于情面,他并没有明言。
辩论声非常嘈杂。但当前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站起身时,全场立刻安静下来。劳埃德的名字就是来自于这位德高望重的前首相。尽管满头白发的前首相已经七十五岁了,但发言时仍然保持着上次世界大战胜利者所特有的威严。
他的话毫不留情。“这不是和首相交情深浅的问题,”他带着不遮不掩的嘲讽口气说,“这是关系国家社稷的大问题。”
劳埃德欣喜地看到,保守党的议员们和反对党议员们同样发出了附和的声音。
“他说他愿意做出牺牲,”劳埃德·乔治特有的威尔士北部鼻音加强了责难的效果,“如果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只有请这位先生卸任了。”
反对党议员纷纷大声表示同意,劳埃德看到母亲高声欢呼。
丘吉尔结束了这场辩论。他的口才和劳埃德·乔治不相上下,劳埃德担心他的演说会拯救张伯伦。但他发言以后,议员们齐齐发出鼓噪声,大多数时间他的演讲都被鼓噪声淹没了。
晚上十一点,丘吉尔结束了演讲,投票马上开始了。
英国下议院的投票系统非常怪异。议员们不是举手表决,也不是在投票纸上画钩,而是必须离开议席,分别穿过两条代表“是”和“否”的走廊。整个过程大约要耗上十五到二十分钟。艾瑟尔说,这种流程只可能是那种没事可干的人想出来的,她肯定这种流程很快会得到变革。
劳埃德焦灼不安地等待着。张伯伦的垮台会让他非常高兴,但此时一切都还没有确定。
为了分心,他把思绪放在了黛西身上,想到黛西总会让他轻松一点。泰-格温的最后二十四小时是何等怪异——先是那张“书房见”的纸条,然后是关于晚上在栀子花套间见面的匆匆交谈,最后是一晚上在焦心和寒冷中一无所获的等待。他等到早晨六点才放弃希望,不情愿地回到阁楼上的房间里,洗脸刮胡,换套衣服,打好包,恋恋不舍地踏上了前往伦敦的旅程。
不是出岔子就是黛西改变了主意。劳埃德想知道的是,黛西原本的意图是什么。她说她想告诉他一些事情。她是想说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还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以致她连约会都忘了。看来只有等下周二见面再问她了。
他没告诉家人在泰-格温见了黛西。那意味着他得向他们解释他和黛西现在的关系,但他实在什么都没法说,他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关系是什么。他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吗?他不知道。黛西对他是怎么想的,他也不知道。在劳埃德看来,他们最多只能算是错过恋爱机会的一对好朋友。但他不会对任何人承认这一点,因为那听起来太可悲了。
劳埃德问伯尼:“张伯伦一旦失势以后,谁将会接替他的职位?”
“估计是哈利法克斯,”哈利法克斯伯爵是现任外交部长。
“不要啊,”劳埃德激动地说,“这时候再不能让贵族当首相了。和张伯伦一样,这种人只知道息事宁人。”
“我同意你的观点,”伯尼说,“但谁又能担此大任呢?”
“丘吉尔怎么样?”
“知道斯坦利·鲍德温是怎么说丘吉尔的吗?”保守党人鲍德温是张伯伦的前任外交部长,“他说温斯顿出生时,几个仙女在他的摇篮中注入了许多能力:想象力、辩论的能力、勤勉的精神和把事情圆满解决的能力,这时又来了一个仙女,她说,‘一个人不能有这么多种能力’,她抱起温斯顿,用力摇了摇,把判断力和智慧摇了出来。”
劳埃德笑了。“有趣的故事,但这是真的吗?”
“没有判断力确实是真的。上次大战中,带领英军参加达达尼尔海战的人是他,我们在达达尼尔海战中一败涂地。现在他又把英军带到了挪威,我们在挪威遭到了又一场失败。他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但事实证明,他对局势的判断往往太一厢情愿了。”
劳埃德说:“30年代他就说要加强军备。事实证明,这点是正确的——那时,包括工党在内的朝野各界都反对加强军备。”
“当狮子和绵羊一同酣睡时,丘吉尔已经在呼吁加强军备了。从这点上来讲,他是够有先见之明的。”
“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有个怀着抵抗决心的人。我们需要一个能大声呐喊,而不是忍气吞声的首相。”
“计票员回来了,你也许能实现你的愿望。”
投票结果宣布了。赞成张伯伦继续担任首相的为二百八十票,反对的为二百票。张伯伦赢了。议席里喧闹连连。首相的支持者相互祝贺,反对者高喊着要张伯伦辞职。
劳埃德非常失望。“经历了这些溃败以后,他们为什么还要维护张伯伦呢?”
“别这么快下结论。”伯尼在张伯伦离开下议院,喧闹声小了点以后,拿了支铅笔在《新闻晚报》的纸边上计算着,“政府通常有二百四十票的压倒性优势,现在只剩下了八十票。”他写了几个数字,计算起来,“除去缺席的议员,大约有四十个原先政府的支持者反对张伯伦留任。这对一个首相来说打击非常大——近百名他的同事对他失去了信心。”
“但这还不够让他辞职,为什么会这样呢?”劳埃德不耐烦地问。
伯尼摊开双手,做了个投降的手势。“这我就不知道了。”他说。
第二天,劳埃德、艾瑟尔、伯尼和比利一起乘火车前往伯恩茅斯。
车厢里满是参加伯恩茅斯工党年会的代表。一路上,他们用苏格兰高地口音、伦敦东区的方言等各种口音讨论着昨晚的辩论和首相的未来。劳埃德还是没找到机会和艾瑟尔讨论那个让他牵肠挂肚的问题。
和大多数代表一样,他们住不起悬崖顶上的豪华酒店,只能住在郊区的寄宿旅馆。晚上,他们去了酒吧,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了。劳埃德的机会来了。
伯尼替四个人买了酒。艾瑟尔大声说,不知道茉黛在柏林怎么样了。战争中断了德国和英国之间的邮政业务,艾瑟尔已经有很久没能和茉黛通信了。
劳埃德喝了口啤酒,然后斩钉截铁地说:“我想再多了解一些我的生父。”
艾瑟尔决然地说:“伯尼就是你父亲。”
她又在逃避!劳埃德抑制住突然在心头腾起的愤怒。“不要再这样说了,”他说,“伯尼知道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尊敬他,他早就知道了。”
伯尼拍了拍他的肩膀,真诚,但也有些尴尬地对劳埃德表示理解。
劳埃德的声音更决绝了:“可我对特德·威廉姆斯很好奇。”
比利说:“我们要谈论的是将来,谈论过去完全没有意义——我们正面临着一场战争。”
“说得没错,”劳埃德说,“正是因为面临着战争,所以必须立刻找到答案。我不愿再等下去了,我可能很快要上战场,我不愿稀里糊涂就死。”这个理由应该能让他们信服了吧。
艾瑟尔说:“该让你知道的,你已经都知道了。”但是她没敢看劳埃德的眼睛。
“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劳埃德强迫自己保持耐心,“我的祖父母在哪儿?我是不是有堂兄弟和堂姐妹?”
“特德·威廉姆斯是个孤儿。”艾瑟尔说。
“他在孤儿院长大的吗?”
艾瑟尔生气地问:“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
劳埃德提高声调,装作生气地回答:“因为我像你嘛!” 世界的凛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