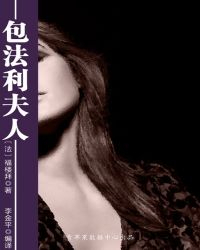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包法利夫人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一
永镇寺是一个距卢昂8法里的小镇,在阿布维尔公路和博韦公路之间,利欧尔河流经的那片谷地的深处。它之所以叫永镇寺,是因为从前这里有一个嘉布遣会的修院,现在没了,甚至连断壁残垣也见不到了。利欧尔河是一条小河在注入安代尔河之前,推动建在河口的三座水磨,男孩们礼拜天就到这里来钓鳟鱼玩。
去永镇寺的人在博瓦谢尔下公路,继续走一段平路到楼泗坡顶,在那里就能看到它了。一条小河把它一分为二:左侧全部是牧场,右侧全部是耕地。牧场沿着绵绵的山丘,与山后的布莱牧区相连,山坡陡峭,上部向外突出在牧场上。右侧的平原微微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开阔,展开一望无垠的金黄色的麦田。小河流淌,像一条白练,擦着草地流过,隔出一边是绿色的牧场,一边是金色的麦垄,使整个乡间犹如一件平铺的大氅,丝绒的披肩式大翻领镶着银色的边饰。走完这段路,面前就是阿盖枞树林和陡峭的圣约翰坡,山坡上沟壑纵横,一道道富含铁质的溪水,泛着砖红色。
这里是诺曼底、庇卡底和法兰西岛三区交界处,三个地方的人都有,说话语调毫无特色。奶酪的质量是整个纳夫夏泰尔地区最差的,另一方面,这一带种地的花费很高,土地贫瘠,需要施以大量肥料才能种植。
1835年以前,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可通往永镇,但差不多在此期间,修了一条“村镇要道”,把阿布维尔公路和亚眠公路连接起来,从卢昂去弗朗德勒地区的车老板有时就走这条道。然而,永镇虽说有了“新通道”,却仍然一点儿也没改变。当地人再穷也不想开发土地,只知死守着牧场不放,以致这个懒人镇一方面落下平原不管,另一方面当然在不断地向河边挤。我们远远地看去,它拉得长长的躺在岸上,像个在河边睡午觉的放牛娃。
过了那座桥,山坡下是一条河堤,堤上栽着欧洲山杨,栽的时间不长。从那地方起有一条直道通往镇口的几幢房屋。房屋的四周用绿篱围成院子压榨机棚、大车库和酿酒房,散落在树丛掩映下,树杈间搭着梯子、钓竿或长柄镰刀。茅草屋顶低低地遮住了矮窗子的三分之一,矮窗上的玻璃非常粗糙,中间还鼓起一个装饰花结,像个酒瓶底。几根黑色的沿墙槁栅梁斜靠在石灰墙头,有时上面还挂着根细细的梨木,底层门上都设着矮矮的转动门栅,以防止小鸡雏到门槛边来啄食苹果酒浸泡过的面包屑。再往前走,院子就越来越窄,房屋越来越密,篱笆不见了,扫帚柄上挑一捆蕨草,在窗户下晃悠晃悠。过了马蹄铁匠铺,是一个大车作坊,门外停两三辆新造好的马车,堵在路上。接着,穿过围栅,就能看到一幢白色的房子坐落在圆草坪的中央,草坪上有爱神的雕像,手指搁在嘴唇上,白房子的石阶两边各有一个铸铁花盆,门上的盾形标识闪闪发光。这是公证人的家,当地最美观的房子。
再往前走20步,离广场不远处的马路对面有个教堂。小小的公墓环绕着它,外面一堵矮墙,里面的坟墓挤得满满的,齐地面高的旧墓石一块接一块,密得像石板铺的路面,墓石间的青草自生自灭,勾勒出十分规则的方格。教堂曾在查理十世王朝的最后那几年里修葺一新。现在,木头拱顶已从上部开始腐朽,蓝颜色的底子上出现黑孔。大门上方,原来放管风琴的地方,为男人们设置了一条祭廊,还有一道螺旋楼梯,在木屐下噔噔作响。
强烈的阳光,透过一块块的彩绘玻璃斜照进来,照在沿墙壁的一排排长椅上,有些地方椅子上钉着一块草编垫子,下面写着几个粗大的字:“某君之座”。再往前,厅堂变得狭窄,那里有一个忏悔室,与之相对应有一尊小小的圣母像,穿着锦缎长袍,戴着绢网面纱,面纱上银星点点,脸颊被染得红彤彤的,像夏威夷群岛出的泥塑。最后就是主祭台,上面高挂着一幅“神圣家族”的复制品,由“内务大臣发送”,供在四个烛台中间。杉木唱诗台保持着原色,没上油漆。
一个个市场几乎占去了永镇大广场的一半。所谓市场,就是一些敞厅,大约20根柱子撑着个瓦顶。镇政府大楼是一位巴黎建筑师的杰作,有点像希腊神庙,在药房边的街角上。它底楼有三根爱奥尼亚柱,二楼一条半圆拱腹长廊的尽头的三角楣上不留空白地绘着一只象征高卢的大公鸡,它一只爪子踩在宪章上,另一只爪子握着公正天平。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要算是金狮客栈对面的郝梅先生的药房!尤其是在晚上灯光照亮后,他用来装饰店面的红红绿绿的广口瓶远远地放射出五彩光芒,这时,透过它们,隐隐可见药房老板俯在斜面桌上的身影。药房里从上到下贴满了用各种字体写成的标签:“维希水、苏打水和巴莱日水、净化糖浆、拉斯帕依药用水、阿拉伯粉剂、达尔塞糖锭、雷纽膏、绷带、沐浴用具、滋补巧克力等等。”而在有整个铺面那么宽的招牌上烫着金字:郝梅药房。在店堂里面的柜台上固定着几架巨大的天平,那里有一扇玻璃门,门上方写着“配药室”三个大字,中间黑底金字重复“郝梅”二字。此外,永镇就再没有什么可看的了。正街(独一无二)长约一步枪射程,两边有几家小铺子到大路转角上戛然而止。出街口往左拐,沿着圣约翰坡脚朝前走不多远就到了公墓。
霍乱流行的那年,这里曾推倒一面墙,又增加了三英亩地,然而这片新坟地却没被采用,坟墓照常,继续重重叠叠朝门口垒去。那个既为掘墓人,又当教堂执事的看守人,在本堂区死者的遗骸身上双倍获利,还利用空地种了些土豆。然而,年复一年,他这块小小的土地也在缩小。所以,当传染病突然流行时,他竟不知道该为死人多了高兴,还是该为土豆收成苦恼。
“莱斯梯布多瓦,您这是在吃死人过日子呢!”直到有一天,本堂神甫对他说。
他听了这句涵义模糊的话考虑了下,一时就不种了。可是现在,他又偷偷地种了,还硬说它们是野生的。
在我们下面要提到的那些事发生时,永镇就还是这个样子。马口铁做的三色旗仍在教堂钟楼顶上旋转,新产品商店门口的两面印花布燕尾旗仍在风中飘扬。药房老板泡在浑浊的酒精里的胚胎日渐腐烂,像一团团白色的火绒;而在客栈大门上的那头金狮,经风吹日晒,鬈毛狗式的鬣毛却仍展现在过往行人面前,风采不变。
包法利夫妇即将到达永镇的那晚,金狮客栈女主人勒弗朗索瓦的寡妇,来回在锅灶间,正满头大汗地忙碌着。第二天是赶集的日子。她得事先把肉切好,给鸡开膛,煨好汤,煮好咖啡。外加她那些包饭人及医生、医生太太和他们的女佣人要吃饭。台球房传出阵阵大笑声,小厅里三个磨坊主喊叫着。柴火熊熊,木炭劈啪爆响;长条案桌上放着大块大块的生羊肉,有人在剁菠菜,震得摆得高高的盘子在晃悠。女佣人正在家禽棚赶时髦抓鸡,准备宰杀。
有一个人头戴镶金色流苏的丝绒便帽,穿着一双绿色的皮拖鞋,脸上长几颗白麻子,正背朝着壁炉烤火。他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就像挂在他头顶上柳条笼子里的金翅鸟。他就是药房老板。
“阿泰米丝!”女掌柜的在喊,“折些细树枝,把大肚玻璃瓶添满水,赶快给客人送酒去!眼看客人们要到了,我还不知道饭后该上什么甜点!老天爷!那帮子搬家的伙计又在台球房里闹开了!他们那辆大车还堵着门呢!燕子到的时候会把它撞坏的!叫希波力特把车子送库里去!……你看看,郝梅先生,他们从早上闹到现在,估计打了15盘球,喝了8坛子苹果酒!……他们会戳烂我那球台毯子的。”她手里拿着漏勺,远远地瞅着他们说。
“戳烂了没关系,”郝梅先生答道,“再买一张就行了。”
“换新球台!”寡妇叫了起来。“这一张不能用了嘛。勒弗朗索瓦太太,我早已跟您说过,您这是贪小失大!失得很大哩!而且,现在那些爱玩台球的人时兴球袋窄、杆子沉,玩的不再是这种球。一切都在变!您得跟上潮流!看看人家泰利耶是怎么干的吧……”
女掌柜气红了脸。药房老板接着说:“他那张球台,没说的,比您这张小巧,而且,他能想得出,为波兰和里昂的水灾、发起募捐,表现一下爱国情操等等的……”
“用不着拿他吓唬我!”女掌柜耸耸胖肩膀打断他的话说,“行了!行了!郝梅先生!只要金狮客栈开门,人们就会来。我们的家底子厚着呢!您走着瞧吧,我们不像法兰西咖啡馆,总有一天它关门大吉,门板上贴一张停业告示!……换掉我的球台,没门儿!”女掌柜接着自言自语道,“用它搁我那些浆浆洗洗的衣服多方便,到了狩猎季节,旅客多了,上面可睡上6个客人呢!……希韦尔这家伙,磨磨蹭蹭的,怎么还不来!”
“等他来了您才给客人们开饭吗?”药房老板问道。“等他?等比奈先生呢!6点钟一到,比奈准进来,您瞧着吧,世上再没有像他这么守时的人了。吃饭还非得在小厅里!别想让他换地方!这个人挺讲究,爱挑剔,难伺候!根本不像列翁先生。列翁先生有时7点钟,甚至7点半钟才来,有什么吃什么,通情达理。多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啊!”
“这就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和一个当过枪骑兵的收税官的差别。”
6点钟一到,比奈走进来了。他瘦削的身子上穿一件挺阔的蓝色燕尾服,戴一顶皮帽,两个护耳用带子系在头顶,翻起的帽檐下露出光秃的前额,由于从前长年戴着帽盔,那地方稍显凹陷。燕尾服里穿一件黑呢马甲,一条马尾衬硬领,下身一条灰裤子,一年四季靴子总擦得锃亮,脚趾使鞋面上弄出两道平行的隆起。长脸上布满修得整齐的金黄色的络腮胡子,一双小眼睛,鹰钩鼻。他精通各种纸牌游戏,是个打猎高手,字也写得很好看。他家里的一台旋床做餐巾杯取乐,餐巾杯堆了一屋子,可他总还怀着艺术家生怕失去的心理和小市民自私的欲望守着它们不放。
女主人先把那三位磨坊主请出来;毕奈就默不作声地坐在小厅的火炉旁,等人家给他摆好餐具。然后,如往常般关门脱帽。
“大家寒暄几句不至于会累着他的舌头吧!”厨房里只剩下药房老板和女主人的时候,老板说。
“他向来话少,”她答道,“上星期,店里来了两个做呢绒买卖的年轻人,晚上讲了许多笑话。我都快笑死了。可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
“是呀,”药房老板说,“没有想像力,没有幽默感,没有社交才能!”
“可人家还说他挺精明呢。”女主人反驳道。“精明呀!”郝梅先生很不认同,“他精明!”随后他又比较平静地补充了一句,“在他那行是的。”他又接着说:“啊!倘若说他是个交际广泛的批发商,或是一位法律顾问、医生或者药剂师,专心扑在他的业务上,结果变得古里古怪,甚至易发火,我能理解。人家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头嘛。比如我就有好多次在桌子上到处找笔,写标签呀,最后竟发现它夹在我耳朵上呢!”
勒弗朗索瓦太太坐不住了,跑到门口去张望“燕子”来了没有。有个穿黑衣服的人突然走进厨房。就着朦胧的光线,依稀可见他红通通的脸和一副强健的体格。
“神甫先生有什么需要我效劳?”客栈女主人一边问,一边忙着去点烛台,“您要吃点东西吗?来点儿黑茶蔗子酒,一杯葡萄酒?”
神甫非常礼貌地谢绝了。前一天,他把雨伞丢在艾纳蒙修院了。他是来找伞的让勒弗朗索瓦太太派人去取来,今晚送到他住处。晚祷钟声一敲响,他就急着赶回教堂。
等神甫的脚步声在广场上消失了,药房老板就批评神甫刚才的表现很不像话。像这样拒绝一杯饮料,他认为,其实是虚伪,最令人憎恶。教士们在背地里全都大吃大喝,都想返回到从前收什一税的时代去。
女主人却替她的本堂神甫辩解:
“除此之外,像您这样的人四个也顶不上他一个。去年,他帮我们收麦子,一次扛6大捆!”
“厉害!”药房老板说,“那您就打发您的姑娘们去向这个壮小子忏悔呀!我可不,我要是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和防止伤风败俗,每个月都要好好抽他们一次血!”
“住嘴吧,郝梅先生!您不敬神明,没有信仰!”药房老板答道:“我有信仰,我的信仰,我甚至比他们都更虔诚,他们都装模作样,拿腔拿调!我可不,我崇拜神!我相信上帝,相信造物主。他要我们在这人世间尽公民和家长的职责。可是我不会进教堂,去吻那些银盘子,去掏钱养活那群饭桶,他们本来就吃得比我们好!我们在林子里、田野上,或者像古人那样仰望苍天,都能膜拜上帝。我的上帝,我的,也就是苏格拉底、富兰克林、伏尔泰和贝朗瑞的上帝!我拥护《萨瓦神甫的信仰宣言》和89年的不朽原则!我才不相信有这么个仁慈的上帝,傻不拉几地拄着文明杖在他的花园里散步,让他那被鲸鱼吞吃的朋友们,三天后又复活了。这种事本来就是胡说八道,何况,跟任何科学都完全不相符,它从而也说明那些教士是无知的,还竭力哄骗老百姓。”
药房老板停住了,他环顾四周,找他的听众,因为他一时兴起,还以为自己是在议会演说。可客栈女老板已不再聆听他的宏论,她正侧耳,啼听远处的车轮滚动声,能听出那是马车声和松动的蹄铁划过地面的声音,“燕子”终于停在门前。 包法利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