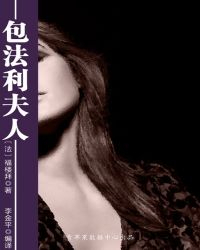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包法利夫人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孩子伸出手臂想搂住母亲的脖子,可爱玛把脸扭开,用颤抖的声音说:“不,不……谁也别碰我!”她又晕了过去。他们把她抬到床上。她直挺挺地躺着,张着嘴巴、闭着眼睛、推开手臂、一动不动、脸色白如像蜡像。两行泪水从她的眼角慢慢流到枕头上。
夏尔一直站在搁床的凹室边上,药房老板站在他身旁,保持着若有所思的沉默,生活中遇上严肃场合理当如此。
“别担心,”他碰了下包法利的胳膊说,“我看已经没有危险了。”
“是的,她现在逐渐平息下来!”夏尔望着睡着的妻子说,“可怜的女人!可怜的女人!……这一次又病倒了!”
郝梅就问起发病的原因,夏尔回答道,爱玛正在吃着杏子就这么突然昏倒在地。
“真是怪事!……”药房老板又说,“杏子引起昏迷也是有可能的!有些人天生来对某些气味非常敏感!这是病理学和生理学上一个值得好好探讨的研究课题。教士们非常了解气味的重要性,他们在各种仪式上总要用些香料,麻痹你的感官,使你心醉神迷,对于女人尤为有效,因为她们比男人更敏感。例如,有的人闻到焚烧牛蹄牛角的气味或者新鲜面包的气味就会晕倒……”
“当心把她吵醒了!”包法利低声说。“而且,”药剂师接着说,“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人类身上,还发生在动物身上。比如俗称猫儿草的荆芥能对猫科动物产生刺激性欲的奇特效应,这您也知道。再讲一个真实的例子,我的老同学布里杜(现住在马尔帕吕街)有一条狗,这条狗一闻到鼻烟味就抽筋。他常常在纪尧姆林场他的小屋里给朋友们做试验。就这么一种引嚏药草竟然能在一种四足动物的肌体里造成这么大的破坏,能不令人怀疑吗?这太奇怪了,不是吗?”
“是的。”夏尔应道,其实他根本没在听。“这就证明,”药剂师洋洋得意地微笑着,接着说,“神经系统的无规律现象多得说不准。老实说,我总认为夫人是属于真正的敏感型。所以,我的好朋友,我真心建议您,不要用那些所谓的特效药,说得好听是对症下药,其实会伤害体质。不要服用无效的药物!只靠饮食调节!用一点镇静药、缓和剂、糖浆。您不认为还应该控制一下胡思乱想?”
“胡思乱想什么?如何控制?”包法利问。“啊!问题就在这里!Thisisthequestion!最近我在报上读到过。”爱玛一醒过就喊着:“那封信呢?那封信呢?”
他们以为她在说梦话。可是,从半夜起,她就一直这样,她得了大脑热。
夏尔在那身边守了43天。他的病人也全然不顾,他睡得很少,不停地给她搭脉、敷芥子泥、换冰水布。他派于斯丹去纳夫夏泰尔去买冰块;冰在路上化了,他就让他再去。他请卡尼韦先生来会诊,还从卢昂请来了他过去的老师拉里维埃尔博士。他感到绝望。最令他担心的是爱玛的虚弱,她不能说话,也听不见声音,甚至连痛苦都感觉不到了,仿佛她的肉体和灵魂全都停顿了。
10月中旬,爱玛能靠着几只枕头在床上坐起来了。夏尔看到她第一次吃下抹上果酱的面包时,激动得哭了。爱玛的体力渐渐恢复,下午她可以下床几小时。有一天,她感到好多了,夏尔就试着扶她去园里散步。沙砾小径上铺满了落叶。她趿着拖鞋,一步步走着,面带微笑依在夏尔身上。
他们慢慢地走到了园子尽头的平台边。她缓缓地直起腰,用手搭在眼睛上观望。她眺望着远方,尽眼睛所能触及的地方;然而,只看到山丘上冒着烟,有几堆草在熊熊燃烧。
“亲爱的,你太累了。”包法利说。他又轻轻地把她扶进葡萄棚架下。“在这凳子上坐一会儿,你会感到舒服一些的。”
“啊!不,不坐这儿,不坐这儿!”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她感到头昏眼花,当晚她的病又犯了,而且症状比以前更复杂,她一会儿心疼,然后就是胸口疼,头疼四肢疼,还会突然呕吐,夏尔认为这是癌症的征兆。
除此之外,这可怜的年轻人还得为经济危机发愁!
十三
首先使他不安的是他从郝梅先生那里拿来了不少药,却不知道如何抵偿。虽然他作为医生,不用付药费,可这份人情总让他过意不去。其次是现在由厨娘当家,家用开支大得惊人。大量的账单送上门来,供应商们总是抱怨,乐乐先生更是纠缠不休。在爱玛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乘机夸大账目,急忙把大衣、旅行袋、两只箱子(而不是原定的一只箱子),外加许多别的东西,统统送上门来。夏尔拒收也没用,商人气急败坏地说这些全都是夫人订的,他不会把它们全收回去。还说,退货会影响夫人身体的健康,请先生慎重。他已拿定主意,宁可打官司,也不把东西收回去。事后,包法利命人把这些东西退回到店里去,费丽希黛忘记了,他由于要操心的事太多,才没有再想起这事。乐乐先生又来讨债,软硬兼施,缠得包法利只好签了张六个月的借据。他刚把字签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何不再向乐乐先生借上一千法郎。于是,他一脸窘相地问乐乐先生是否能弄到这笔钱,并且说,需借一年,利息听便。乐乐急忙跑回店里,取来了这笔钱,并口授了另一张借据,按这张借据,包法利在来年9月1日付清1070法郎,加上已签了借据的180法郎,共1250法郎。就这样6%的利息,加上14的佣金,还有那些货起码给他带来13的盈利,一年下来,乐乐能赚130法郎。他还希望,到时候包法利还不起这两张借据,只好求他延期,他这笔小小的资金养在医生家,就像养在疗养院,等到归还他的时候长得脑满肠肥,能撑破他的钱袋。
他近来真是春风得意。他和纳夫夏泰尔医院签了约,由他供应苹果酒。纪尧曼先生答应给他买到开发格鲁梅斯尼尔泥炭矿的股票,他还想在阿格伊和卢昂之间再开辟一条公共马车路线,这条线估计很快就会使金狮客栈的老爷车破产,因为他的公共马车将跑得更快,票价更便宜,行李装得更多,从而他就能把永镇的买卖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夏尔考虑过多次,来年拿什么还这样一大笔钱。他搜肠刮肚,想找出办法来,例如向他父亲求援或者变卖家产。可他父亲一定装聋作哑,而他自己又也没什么可卖。这时,他觉得实在想不出法子,就干脆不去想。他责备自己不该把爱玛丢在一边。仿佛他的心思全都属于这个女人,稍有一刻没想到她,就像是偷了她的什么东西。
这是个严冬。夫人久久未能康复。天好的时候,他们就把她的椅子推到窗边,让她看看广场,因为她现在特别憎恶园子,那边的百叶窗总是关着。她让人把那匹马卖掉,她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全都让她讨厌。她现在只关心自己的健康。她在床上吃各种各样的点心,打铃叫女佣来,不是询问她的药煎好了没有,就是让她陪自己聊天。窗外,雪去雨来,在窗前等待着天天重复的一件件小事,仿佛还有些焦虑,而这些事跟她都没关系。其中最热闹的事就是傍晚时分“燕子”的归来。这时,人们大呼小叫,希波利特搬下搁篷顶上的箱子,他的风灯像星星似的在黑暗中闪烁。中午,夏尔回家,然后又出去,他走后,爱玛喝一碗肉汤。5点左右,天色暗淡下来,孩子们放学回家,拖着他们的木底鞋在人行道上走成一排,全都用手里的尺敲打着家家户户护窗板上的铁钩。
布尔尼贤先生此时过来看望爱玛,询问她的健康,给她讲些新闻,并试图劝她信教,倒也说得她心动。一看到他这身道袍,爱玛就感到安慰。
一天,她的病势危急,她以为自己快要死了,就要求领圣体。就在大家布置房间,准备这场圣事,用堆满糖浆瓶的五屉柜作祭坛,费里希黛把大理花撒在地板上的时候,爱玛渐渐地感到有一股力量穿过她的身体,帮她摆脱掉病痛,摆脱所有的感知和感情。她仿佛觉得肉体轻飘飘的,灵魂冉冉上升向上帝飞去,就像焚香时发出的青烟,消融在上帝的慈爱里。他们在被褥上洒了圣水,教士从圣体盒里取出白色的圣体饼,爱玛张开嘴唇去接受救世主的圣体,她感到一种几乎令她晕过去的极度快感。凹室床前的帘幔像去轻轻飘起,五屉柜上两支蜡烛发出耀眼的光,使她觉得那就像是基督的光轮。她低下头,恍惚听到天国里天使奏出的竖琴声,她仿佛看到,在碧净的空中,天父光辉灿烂,威严地坐在黄金宝座上,手持绿色棕榈的诸圣侍立左右,他挥了挥手,让长着火焰翅膀的天使飞下来,托起她飞上天堂。
这种壮丽的幻景就像最美好的梦永久地留存在她的脑海里,她那因骄傲而不得安宁的灵魂终于在基督的谦卑中得到小憩。爱玛决心摒弃某种意愿,以得到上帝的怜悯。于是,现在在所有的幸福之外还有一种更崇高的乐趣;在所有世俗的爱之上还有一种连绵不尽的爱,而且还将永恒不断地生长着!在希望的幻觉中,她隐隐看到一个纯净的境地,漂浮在人世之上,与天堂混为一体,那就是她向往的地方。她渴望成为圣女。她买了一串串念珠,佩带护身符,她希望在她卧室的床头上有一个镶嵌祖母绿的圣骨盒,让她每晚都能吻一下。
本堂神甫对这样的安排大为赞叹,虽然他认为爱玛的信仰因为过于热烈,最后可能会进入异端邪说,甚至做出荒诞不经的事情。然而,他对这方面也不是很精通,无法对她进行指导。所以,他写信给主教大人的书商布拉尔先生,请他寄些“佳作给一位聪明绝顶的女士”。书商并不重视地把时下流行在宗教书市的书随便打成一包寄来了,就像给黑人寄五金器材。其中有教理问答小册子,有用麦斯特先生那种傲慢的口吻写成的论战文集,还有一些小说样的东西,粉红色的纸板书壳,酸溜溜的文字,不是到处游历的神学院学生就是忏悔的女才子炮制出来的东西,有《好好地想一想》,获过多次勋章的某某先生写的《玛利亚脚下的上流社会人士》、《青年必读:伏尔泰的谬误》等等。
包法利夫人的身体还未恢复好,不能长时间地读书,另外,她过于仓促地读这些书。她对礼拜的具体规定感到厌烦,论战文章咄咄逼人的笔调让她不高兴,她也不知道它们激烈攻击的对象是怎样的人。那些宗教味极浓的世俗小说,显得作者对人世是那样的无知。她本来在寻找真理,他们却使她不知不觉中离开了真理。然而,她仍在坚持,每当她读完一本书的时候,她都觉得自己被细腻的天主教的忧伤所攫住,这种忧伤只有最纯洁的心灵才能体验到。
对于罗多尔夫的回忆,被她深藏在心底,比埋在墓穴串的国王的木乃伊更庄严肃穆。从这个特殊而不朽的爱情里散发出一股气息,弥漫了那个她想生活在其中的纯净的空气里。当她跪在哥特式跪凳上祈祷时,她把往日在热烈的奸情中对情人低声说的话,也对天主说着。她在试图培养信仰,可她没感到任何快乐,她拖着疲乏的腿站起来,似乎感到这是个大骗局。爱玛想,她如此诚心祈祷,一定会有好报的。她自认为比过去的那些贵妇更虔敬,她曾对着拉瓦利埃女公爵画像向往得到她那样的殊荣。她们拖着镶绦子花边的长裙后摆,神态是那么雍容华贵,却退守孤独,一颗受伤的心在基督的脚下流淌着泪水。
于是,她大行善事。她为穷人缝制衣服,给产妇送去劈柴。有一天,夏尔回家,还看到3个乞丐在厨房餐桌边喝汤。在她生病期间,夏尔把女儿送到奶妈家去了,现在她又把女儿接了回来。她想教女儿读书。贝尔特再怎么哭闹,她都不发脾气。她下定决心凡事忍让,宽容任何人。无论说什么,她的言辞总是至善至美,她时常这样问孩子:
“你肚子不疼了吗,我的天使?”老包法利夫人对她已经无可指责,只是认为她给孤儿们打毛衣近乎上瘾。然而她在自己家里把力气用完了,到这太平无事的儿子家里来还挺舒坦,因此一直待到复活节之后才走,躲避包老头的冷言冷语。老头子每逢耶稣受难日,故意要吃香肠。
婆婆在身边更坚定了爱玛的信念,因为老太太作风端正,办事严谨。其实,几乎每天都有人来陪爱玛。她们是朗格洛瓦太太、卡隆太太、杜百里太太、蒂伐什太太,还有那位很善良的郝梅太太,她在两点到五点之间必到,而且从不相信外面关于她这位女邻居的闲言蜚语。郝梅家那4个孩子也来看她。他和他们一起上楼,他们进房,他就一动不动地默默站在门边待着。包法利夫人常常没注意到他在那里,自行梳妆起来。她抽出梳子,把头猛地一甩,发卷就一个个地散开了,乌黑的头发一直垂到腿弯。可怜的孩子第一次看到,似乎闯进了一个全新而奇妙的世界,惊呆了。
爱玛不可能注意到他那无声的热情和羞怯。她绝不会想到从她生活中消失了的爱情,竟然会在她身边的这个穿着粗布衬衣的少年人心里萌动,这颗心正为她的美而倾倒。而且,她现在对一切都如此淡漠,她的语气那么亲切,目光却那么高傲,态度时好时坏,让人捉摸不透是自私,还是助人为乐,是损坏道德,还是积德行善。例如,有一天晚上,女佣人闪烁其辞地向她请假外出。她开始生气了一会儿,接着突然问她:
“看来,你爱他啰?”
然后,等不及羞得满脸通红的费丽希黛答话,就有点哀伤地说:“行了,快去吧!好好快活一下!” 包法利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