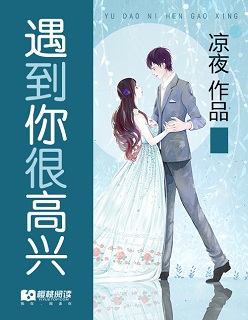江山易改何妨成英雄?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明传奇志之肆羽易天记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宣化,谷王府。
朱橞紧紧盯着眼前人,目光晦明晦暗。
“大汉太子,千金之躯,你真指望他会来见你?啊哈哈哈哈哈——就凭你,也配!”
“一群垃圾货色,竟敢耍弄本王!陈善的计划到底是什么?说出来,本王还考虑让你死得舒服点!”朱橞咬着牙道。
对方赤膊上身,漫目所见遍是伤痕,可却似毫不在意,吐出一口鲜血,阴恻恻一笑。“你和刘璟若是够聪明的,太子自然会和你们合作,可惜——你们都是群蠢货!以为和那什么张之焕通了气,皇帝就能信你们了?哈哈、咳——咳咳咳咳咳、呵呵……朱橞,你想要报仇?想要左右逢源?也要看看自己有没那个本事!你离皇位最近的一次机会,全被你亲手毁了!从今往后……你再也没那个命了!咳咳咳——咳咳咳咳——哈哈……哈哈哈……”
“啪——”朱橞狠狠往他脸上抽了一鞭子,后者半张面皮霎时都翻了出来,血流如涌。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咳咳咳——”鲜血都已呛进了鼻腔气管,他居然还笑得张狂。
“闭嘴!”朱橞原被他笑得浑身气抖,忽而却想起了当年行刺先帝那宫妇——听闻她也是这样,仿佛没有痛觉般,大笑狂叫,整个人疯疯癫癫。难道,关于白莲教妖人的传说是真的?
怎么可能!
“说!陈善到底在哪儿!他还有哪些盟友?朱棣那边呢?陈善是不是也和他通气了?说话!!”朱橞拿铁棍猛一拍对方已被敲穿的膝骨。那人给吊在半空,两条小腿就像丝连的断藕一样晃晃当当。
“你……这蠢货……挥霍良机……再也……不可……呵呵呵……”对方全不理会朱橞施以的酷刑和咆哮。“太子殿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双眼的聚焦渐渐变得浑浊,然而从左腕到肩头的那片陈旧焦痂,却黑得如在发亮,火光掩映下,像极了一幅诡异的莲花焰图腾。
“大……大妹……小仙……我来……你们……了……”
“真他妈的晦气!”走出囚室,朱橞啐骂一声。
“殿下稍安勿躁。如殿下所说,先前陈善从未以真面目示人,只派心腹联络。这么一个人乍然出现,自称陈善,年纪、所述都对得上,殿下又心急不定,难免会落入他毂中。”刘璟道。
“这话长史说给我听有什么用?京中那位难道也能体谅吗!本王现在要怎么办?”
这段时间刘璟早就考虑过了对策,很快道:“殿下莫乱,目下还是应当效仿辽王,照原计划入京。”
“刘长史你在说什么?”朱橞觉得他简直老糊涂了,“如今‘陈善’都没了,本王拿什么去跟皇帝交代?待本王一走,宣府可就任由朱棣他进出了!到了金陵,本王要怎么自辩?”
“下官将留守宣化城,待殿下启程后,便将宣德、承安、高远三门封堵,东西南北但留昌平、广灵、定安、大新各一门以图固守。殿下既已携大军南往,燕王未必会来夺城;就是他来,下官定率驻军志死以抗。无论胜败,谷王府尽忠于职守,陛下自无尤于殿下。”刘璟显然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至于京中,张侍郎应该已收到了下官飞马快书。虽说这次变生肘腋,但只要有他在御前直言,总能澄清原委。殿下只须按原计而行,不必过忧!”
……
建文元年八月十三,耿炳文所率平燕大军已行至真定,在滹沱河南北两岸分营扎寨,并分兵于河间、鄚州,以先锋九千人驻扎在雄县,成犄角之势直逼北平。孰料两天后中秋佳节夜,燕军飘忽而至,趁敌军不备,偷袭雄县,致九千先锋全军覆没。一击奏功后,朱棣又于月漾桥设伏,将接信赶来的鄚州援兵打得措施不及,落水而败。潘忠、杨松两员大将双双战死,剩余的部队尽被朱棣收编,燕军军力日盛。
“大帅!雄县、鄚州均已告破,三万大军十不存一。燕兵不日便将行至真定,连胜之师,士气正酣;而我军千里跋涉,正是疲懈之时,末将担心若直撄其锋,恐怕不易取胜!”宁忠忧虑道。
“莫急。终归敌寡我众,我军兵力尚占优势。传令下去,南营即刻拔寨渡河,全军集结北岸,待与叛军决一雌雄!”耿炳文道。
不到半个时辰,南营便收整了帐棚兵马,六万大军分股渡河。
砰——
“报大帅!东北有警!”
“报大帅!南营人马正迁移过河,可搭桥突然炸毁,叛军还不断向河中投石放箭,我军无法突破!”
耿炳文一怔。来得竟这么快!军队转移之时阵列不齐,最怕半渡而击的突袭,立刻问道:“东北那支为首领兵的是谁?”
“据报是燕王亲自率队!”
“好——那本将便去会他一会!”朱棣手上不过五万人马,必要留守一部分在北平城和大营,能调度的至多三万而已,而他手上光北营兵力除去后勤也有七万近八,二三对一,难道还能输他?“立刻击鼓鸣号,三军随我迎战,全力攻杀东北一线!李副将,你率一支千人队,负责阻截逆军弓*弩和来犯小旅,掩护南营渡河。”朱棣就是想要本军分兵不暇,自乱阵脚,他不能中他的计。
朱棣兵力不足,只要截住了他所率的主力,其他人马势必都要回去援救主帅。一旦箭矢阵撤走,南营就能从容上岸。待整顿集结完毕,他便可将叛军合围一击。
“末将领命!”李坚抱拳受令。
东北方向,耿炳文几乎率领全军迎战朱棣。这边南营将士正奋力争渡,根本没想到敌军来得如此之快。搭桥一毁,用来冒矢突进的冲车都泡在水中,靠举牌防御已来不及。李坚带领着一千余人,为掩护南营冲阵而去,孰料燕军那支弓*弩机械团却如泥鳅似地滑开。另一边,燕军东北先锋似早有了预见一般,很快分了一股出来迎战李坚。
燕军弓*弩手骑的都是快马,投石机又装了滚轮,有马匹驱策拉动,转移神速,不一会儿便重新沿岸排布,易地又射。王军南营人马困于水中,前后左右都是除了急流就是友军,连转向都难,更别说急奔,骑兵步兵都被如雨箭石打得无力招架。
有些胆子大的意图一鼓作气,冒死冲锋,前方将士的浮尸却成了新的阻碍。进退维谷之间,无数人已被射杀于滹沱河中,一时间水波鼎沸,河面如同赤染。
此时,朱棣所率主力如一柄直插的长剑,猛刺进耿炳文所在的北营军中。
“报大帅!燕王正朝这里冲来!率军约有一万人马!”
“报大帅!左翼有敌情!大约有一万人马!”
“全军接战!结阵啊!两万人还拦不住么?令旗都已打出,还在摸什么鱼?!”耿炳文怒吼道。
“大帅!正东方向又来了一支骑兵队!”
“大帅大帅,后军遭袭,无法结阵!一支突进队正往中军冲来,人数不少于五千,带头的武将十分厉害,张保将军正在接战,恐怕也撑不了太久了!”
他为什么还有兵力绕道夹击?难道朱棣倾巢而出,当真要跟他在此决一死战么?
不好!
“快传令旗,叫宁忠领南营军速来支援!能来多少是多少!”“报大帅,宁将军应该已经渡了河,可找不见他踪影!”“左军顾成何在?”“顾都督已失陷,落马被擒!”“什么?!”耿炳文陡然一凛。“速叫回张保,下令全军退守真定!南营停止渡河,一概回撤!”
鸣金声震天而起。张保收拾兵旅,火速赶来与耿炳文汇合,长缨枪上一路血水抖落。且战且退之间,耿炳文回首一望,陡感困惑:“那家伙是燕王手下的朱能?带三十人拼死追截,是要干什么?”难道还想靠这点人拦下他数万大军吗?
“好像是燕王贪进,已在战阵中失踪。朱能是他心腹,怕是以为他被咱们虏获,所以来抢人的!”张保道。
耿炳文定睛一眺。果然,东边的那支叛军已没了先前的冲劲,如无头苍蝇一般在阵中混战,左支右绌全不得章法,显然无人引领,大惑立刻转为大喜:“好!好!真是天佑陛下!马上停止撤退。张保,领军布伏虎阵,引敌围歼!”
他手上北营两万中军几乎完好无损,张保的右军起码也收拢了一万多人,拿来布阵绰绰有余。只要先合围阻住朱能那只疯狗的势头,再收缩包圈,消灭叛军残留在本军的部余——没了帮援,朱棣决计难以突出。
不管眼下朱棣是死是活,不过多时,他就只能死了!
不错,他耿炳文就是黄忠,宝刀未老的黄忠!
“大帅,李副将正和叛军弓*弩队鏖战,末将先领军前去接应!”
“张保?”耿炳文心头一异。
话音刚落,张保已拍马而去,仅留下身边一名顶盔掼甲的从将,兜鍪下露出的眼睛薄带笑意。
“侯爷,别来无恙吧。”
“燕王?!”
朱棣振臂一呼,刚刚集合以布围歼阵的右军劲旅竟全然倒戈,于本军之中一阵掩杀。许多王军将士都未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已被身边臂绑着红布的“同袍”直贯胸背,身首异处。
朱棣打败了潘杨三万先锋,会有本军衣甲不奇怪,可这么多人怎能悄无声息地混进来?耿炳文憬然顿悟,睁圆了眼:“张保!你这贼子竟敢背主投敌!!”
“侯爷,有道是良禽择木,可怨不得我啊!”张保回头见朱棣已与朱能等人合兵,占据了战场优势,而耿炳文有身边亲兵拼死护卫,燕军一时奈何不得,立刻领着从队拖枪直冲而来。
“胜负已分,还请侯爷乖乖束手就擒吧,王爷必饶侯爷不死!”
“放你娘的狗屁!”耿炳文勃然大怒,再不要亲卫保护,拍马怒而迎上。然饶他勇猛过人,毕竟已是六十五岁的老将,如何能是正当盛年的张保对手?□□钢刀兵刃相接,乒乓作响,不过三四击,铜盔就被打落在地,耿炳文发髻披散,双眼赤红。
“大帅!先撤了!退守真定城,咱们还有一战之机!”
李坚一千人马遭张保方才一冲,早已畸零难整,此时勉强回援,只能率自己亲兵一边掩护耿炳文,一边大喊勒令本军撤进永安门。
号角声中,部队溃沙般散乱涌入真定城。李坚有心无力,只顾得上护住主将。其余人马跟随其后,无人主持不能成列,全都困挤在门道内外,堵塞难行。自相践踏的哀嚎声不绝传来,被踩死的兵士不可胜数。后方还有数万大军源源而入。
朱棣趁势掩上,杀人射马,如同砍瓜切菜。
“所有弓*弩齐发,先阻住敌军,掩护我们的人入城!能撤多少是多少!”
“可将军!还有好多我们的人落在后面,那也要被射死啊!”
“难道让叛军攻入真定吗?!还蘑菇什么射啊!!”李坚暴吼着发令。
耿炳文头发乱散面色如灰,推开众人阻拦,跌跌冲冲登上城楼,看着底下乌泱泱的兵士被敌我双方的箭矢屠杀,耳中惨叫震天,一如人间地狱。
“死也要守住了真定城!!!”
天晴骑马跟在三保和马云身后,望着远处情景,呆呆不能言语。
真实到不真实的画面,让她近乎晕眩,连承运门中那六十二颗插杆人头,此时浮动眼前,都变得温和而平实了起来。
这是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明白的残酷。
李坚已放下了城门,数千名士兵被遗留在外背水一战。朱棣兵力宝贵,一见耿炳文已经入城,便放弃了近攻,改为了炮火远射,城门内外全然变成了一场远距攻防战。
几轮炮火过后,永安门所有的楼橹如摧枯拉朽一般毁坏,城外用以阻挡炮弹的木栅和绳网摇摇欲坠地荡着,被逼扑而来的火箭烧得焦黑破败。受令死守城头的将士,不得退却,只能边抵御矢石边勉力反击。有时一箭飞来,恰从胸口直插而入,活人就如同被楔进了着火的木柱,闻着自己身体所发出的焦臭,呼天惨叫,直到四肢都被烧得佝偻起来,才垂垂再无声息。
破碎的头颅、不知是谁的断手残足,随着一声声炮响在天空中齐齐飞舞。血雨漫天而来,一层层洒在尘土之上,却无法给地面染上红色……
土地没有一丝存留的空隙。
城下已经堆叠了太多尸体了……
天晴很清楚,炮弹有限,从无极县奔袭而来的燕军部队更不可能携带那么多弹药,朱棣的目的不是想摧毁这座城。
他是想摧毁耿炳文的心。
在他放弃的时候给他希望,而在他以为能赢的时候——背叛,反转,兵败如山,目不暇给,接踵而来……眼看成功明明已近在咫尺,瞬间,却被砸得粉碎,如同城楼挥飞的炮灰。而他就好像一只被猫玩弄掌间的耗子,徒劳无功地在命运中挣扎。
失而复得,得而复失,没有多少人能在这么短短时间里,承受这样的大起大落——这是瓦解一个人心志最快最有效的方式。
“这就是殿下的攻心之术啊!”马云眼观战况,猛力点头,感佩不已。
攻心之术……
天晴狼狈地跌身下马,扶着一旁树干大口干呕。
她终于明白了爹坚持不让她参战的原因。
耿炳文,那些倒在城门外的人,难道也和义父一样——都是注定要被牺牲的吗?
“呃娘娘?殿下说了让您留在大营的,这可真是……”马云转头看到她像白纸一样的脸色,立刻跳下马来,大感后悔答应了她的请求。
朱高煦撸了一把坐骑的马鬃,撇嘴嫌弃道:“女人就是女人,这点场面就撑不住了,真没用!下次别吵着跟来,拖本少爷的后腿~”
“二公子是殿下特地让来观战历练的,娘娘自不能比。”三保也下了马,走近天晴身边替她拍抚后背。“娘娘还好吗?先回无极县大营吧,有郑姐姐和刘大夫在,帮娘娘稍事整顿一下,徐老爹应该看不出来吧?”
“我又没有上战场杀敌,不要紧。殿下和我爹都不会见怪的。”她擦了擦嘴角,“我还要再留一会儿。”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是黄忠!斩夏侯渊于马下!陛下,臣定不负所托!由臣为陛下,诛尽奸贼!陛下不杀皇叔,不杀皇叔!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帅是疯了吧……怎么李副将也不过来拉一下,别摔下去了才好。”临近黄昏,双方炮火都已停歇。燕军退扎到了数里之外。一受命瞭望敌情的王军步兵小旗抱着自个儿的长牌,看着站在城头摇头晃脑放声长笑的耿炳文,喃喃道。
“也难怪他。不过半天之前,他还道自己能胜呢。”步兵二也叹,“我也以为咱们能胜呢,三四个人打一个,居然打不过?折进了那么多兄弟……”
“那燕王爷可真太厉害了!”步兵三道。
“你还叫他王爷?他现在可是逆贼!叛党!”步兵四立刻瞪着眼纠正。
“你们说大帅这话什么意思啊?陛下不杀皇叔?皇上不让杀王爷、呃逆贼吗?”步兵五插嘴道。
“擒贼先擒王,不让杀敌将,那这仗怎么打啊?”
“哦——怪不得咱们要输!光挨打不还手,这还能不输嘛!”
“不对不对,大帅现在这模样……应该是乱说胡话吧?这一会儿黄忠一会儿夏侯,没准说的是刘皇叔呢?”
“都在议论什么!”
“呃,李、李将军!标下什么也没议论!”众人见李坚走了过来,立刻纷纷起立,把兵器盾牌都执到一边,低头行礼。
“‘什么也没议论’?”李坚扫了一圈众人,面色凝肃,“耿大帅精忠为国,时刻将皇命圣旨记在心中,怎会乱说胡话?糊涂的是你们!”
“啥?”几人都是一凛,胆子最大的步兵三已困惑地抬起了头:“大帅说的……是圣旨?陛下、皇上真的不让我们杀王爷么?”
“哼……”李坚转身大步而去,留他们见他远离,聚在那里哗然议论,心中暗道——他才不做耿炳文那样的傻瓜,为皇帝的名,脏自己的手,如今弄得晚节不保,疯疯癫癫。就算耿炳文真的如他所愿替他斩杀了朱棣,难道最后皇帝会保住他么?
朱允炆,倘若你这么想要他的命——
那就自己来拿吧!
……
“让你不要来的。”见女儿一副郁郁的模样,常遇春忍不住责怪。这丫头一向心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虐吗?
“我不放心你啊。”天晴万没想到,爹会瞒着她主动请缨,领这次五千人突击队的差事,出发前还喜滋滋跟她说,太久没上战场了,光想想就激动!朱棣深知他曾与耿炳文同袍多年,于他的打法最是知悉,自然求之不得,爽快便同意了。
“我只知道耿炳文一向求稳,一定会想以多胜少。终归还是燕王有胆量,一听张保说主帅务求要他的命,就决定拿自己做饵,诱他所有主力都冲自己来。后方薄弱,才给了咱们别动队包抄偷袭的机会,乱了耿炳文的阵脚,最终让他乘虚而入反戈一击,以少胜多……真不愧是九王之首,名副其实啊!”常遇春说着点了点头,像是在肯定自己的判断,“说不定,他还真能赢呢。”
他自然能赢。
悠鸣的箫声,似哀若伤的慨叹,凄柔楚楚,于幽壑孤城之上,羽鸦哜叫之间,乘风往迭回荡,一如挽歌。
“这曲子,叫什么名字?”不知何时,朱棣站在了她的身后。
包括爹在内的燕军大队已从容回营,唯独天晴还留在之前和朱高煦他们伫马而立的大槐树下。
她放下指间洞箫,望着城门外那些无人收敛的尸首,在夕照下残败而卑微地堆叠,如破烂的器皿。唯有风里的血腥气味似萦荡的冤魂,久久不散,提醒着他们曾有过鲜活的生命。
“……《渡津》。”
“以后每场仗打完,你都要吹一遍么?”朱棣淡淡地问。
“吹就吹了,也不费什么力气。”
“渡津……那么多人,你渡得了几个。”
“可能一个都渡不了吧,我不过图自己心安。”
“你认识他们中的谁,耿炳文?还是宁忠?值得你这样上心。”
天晴自树下站起,缓缓道:“我谁都不认识。只道他们都是和我一样的人,是这浩渺宇宙中的一粒埃尘。物伤其类,人同此心罢了。”
朱棣似有似无笑了一声。“我还从来不知道,你把自己看的这么低。”
“不是低,只是平常而已。”天晴轻轻叹了一口气,“人一辈子,到得最后,王侯将相、蝼蚁蚹蠃,又有什么区别?不过成灰成土。正因他们都和我一样,将心比心,我才希望他们迷津有所渡,魂灵有所安,不至于在这片修罗战场迷途辗转,孤孤荡荡。愿来生托世时……他们都能等到一个太平天下。”
朱棣默了默,道:“好,我答应你,或输或赢,很快有个了断。不会让他们等得太久。”
天晴转过去,只看到他肃然的侧脸,不似在说笑。
“很快”,如果能快,哪还需要她开口呢。
正如爹说的,要快,只能是他输了。他何尝不知道?
或许,是她一直误会了他。其实对于这些死去的人,他也是有慈悲心的呢?
“等到一切结束之后……可以放过的人,还希望殿下能够放过。”她不敢过分期盼,只能小心请求。
朱棣眺目残阳如血的真定城,回答依旧无波无澜:“你怎么知道一定是我放过别人,不是别人放过我。”
“因为你是你,不会让别人有抓住的机会。抓不住,又何谈放过。”
“呵……承蒙你看得起。”朱棣一笑之间,忽然顿了顿,“如果有一天战死的是我,希望,你也能吹这曲子给我听。”
从他的话音里,天晴竟难得地听出了一丝忧郁苦涩的意味。一瞬间,她有些恍神。他是怎么了?
“殿下为何一下子悲观起来了?”
“说死就悲观么?救赵楚兵、吞吴越甲,哪个不是向死而生。”他道。
只不过,他死便死了,怕是留不下什么破釜沉舟、卧薪尝胆之类佳话的。
天晴认真地端视朱棣的侧脸,依旧没有见到任何试探的神色,心中不由想,虽是无心之言,但他这么笃定他战死的时候,她一定逃得掉?
即便爹在这里,卢家村所有人都在这里?
他始终还是不相信她的。
恰此时,朱棣突然拧起眉头,不自然地扯了一下嘴角。
“殿下,怎么了?”
“没怎么。”
“有。上次和道衍大师定计松亭关时,殿下就露出过这个表情,光我看到就有三四回了,好像忽然很痛的样子。”
“牙疼罢了。”
※※※※※※※※※※※※※※※※※※※※
最疾速剧烈的成长往往发生在直面最不愿面对的时刻,对天晴也是一样啦…… 明传奇志之肆羽易天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