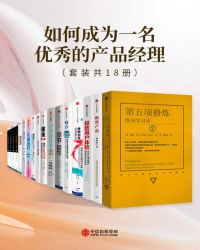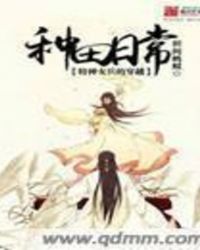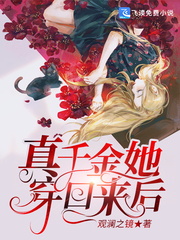第7章 骆驼过针眼:放得下,拿得起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7章 骆驼过针眼:放得下,拿得起
在古代的耶路撒冷有处叫作“针眼”(the needle)的窄门,驮满货物的骆驼若要通过那里,就必须卸下货物。间接引用这个在当时广为人知的比喻,耶稣说:“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
在U形过程的底部往往也有一个内心的门槛,也需要我们把人生旅途中驮带的包裹卸下来。我们一旦过了这个门槛,就能从正在生成的现实的本源之处来观察,并让它通过我们呈现出来,变成现实。在我们采访的人里,有的叫它“隔膜”,有的叫它“门槛”,还有人甚至把它看成一种生死轮回和阴阳转换:放下,舍得,是轮回中的死亡过程,而体悟到一种不同的自我,则属于再生过程的早期阶段。如果是集体通过这个“门槛”,大家会用许多不同的语言来描述这个经历。有的人谈到异乎寻常的创造力,有的人用无限的能量描述它,还有人用深度会谈来形容它:大家不记得谁说过什么,因为发现和创造的流动似乎把所有人都融为一体了。许多人只是说,不能用理性思维去理解所发生的经历,因为表面上看似完全不可能的事却发生了——比如,骆驼穿过了针眼。
内心的疑惑
1998年,世界最大的两家公司刚刚完成关键运营机构的大规模合并重组。合并前的两家公司原本是竞争对手,现在它们则必须共同面对其他对手。对这次合并能否成功,也有许多理由让人怀疑。它们面临的挑战十分严峻,这使公司总裁决定成立一个由所有关键业务部门经理组成的小组,还邀请了外部参与者约瑟夫和奥托加入。小组的任务是领导力开发过程的设计,目标是让各层面的领导者都能有效提高现有业务的竞争能力,并创造出新的业务领域。
小组一起工作了4个月。然而直到日程安排的最后一次会议的最后一天,领导力开发的设计工作仍然没有完成。按计划,首席学习官和小组组长要在第二天向公司总裁报告设计工作,并提出所需要的实施预算。所以,那天结束之前必须完成设计。当时只剩下3个小时,尽管工作任务很重要,尽管每个人都知道当时需要的就是创造性,但小组还是完全没有任何创造力。如果会议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设计,整个项目将会面临失败的结局。
焦虑的情绪在增长,气氛越来越紧张。后来,平时很安静、不怎么爱说话的一位名叫戴维的主要业务部门的副主管,站起身来面对小组成员发言了。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激情,也有一种脆弱——很明显,他是鼓足了勇气才站起来发言的。他看着墙上挂着的小组工作总结图表说:“在这里,我真的感到自己在挣扎。我觉得我真的理解每个局部和细节,可就是无法从宏观看清全局。”然后他转向奥托,问道:“你能不能帮我?帮我解释一下。如果我们能看清整体,我们就能完成我们所需要的突破。”
奥托没有回答,一方面因为他也没有针对戴维的问题的直接答案,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不想干扰正在深入的沉静过程。一时间,房间里都安静下来了。小组里没有人曾以这种方式寻求帮助。于是,约瑟夫看着围坐在一起的小组成员说:“知道吗,我觉得小组一直缺乏的,就是从心里倾诉和聆听的意愿。”过了一会儿,另一位成员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能用戴维刚才那种个人的勇气来引导我们的日常行动,那我们就能完成任何需要的变革。”约瑟夫回忆道,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房间里的每个人似乎都开始在更深层的源头处讲话”,“这个项目的设计也变得清晰起来,似乎没费什么劲儿,就好像在瞬间完成了刚刚还看似不可能的事情”。
尽管小组里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理解那时发生的事,但那个经历的确非常深刻而有震撼力。“好像设计背后的模型一直就在那里摆着,但我们却都陷入各种细节,所以根本看不到它。”一位参与者后来回忆说。另一位说:“那是我所经历的最高效的几小时协同工作时间。”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被称为“领导力实验室”的新领导力开发过程,在两个核心业务部门激发了主要的变革行动,并开始显现出令人鼓舞的成果。两年后,这两个部门在业绩测评中都从“最差”提高到“第一”。同样重要的是,戴维和其他人都看到了戴维所说的“由于我们自身达到了这个不同的境界而产生的能量和激动心情。它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到哪里——并真的到达那里了”。
舍弃控制欲
要到达那个体悟当下的“不同的境界”,就必须先开发一种“放得下”的容纳力,即放弃我们想象中需要的控制欲。瓦莱拉把“放得下”看作是提高意识水平的第三个“基本动作”,排在悬挂观点和再引导之后。“通常是生活境况逼迫你放下:疾病、危险、失恋——某种极端的力量迫使你做出放下的动作,由它去了。”但他还认为,放得下也是一种可以开发的容纳力。
悬挂观点让我们对自己的思维习惯有更清晰的认识,因为我们能够退后一步看,注意到自己的思维习惯。再引导能开启我们新的意识境界,使我们超越以往割断自己与现实之间联系的习惯性的主客体二分法。但我们很容易陷入对这种新意识境界的执着,也许是因为它很惬意,也许因为它很讨厌,也许因为它很新奇,或者只是因为它感觉很“对路”。不管什么原因,这种执着都会让我们脱离当下。而不断地放下,即能让我们保持当下意识。
开发放得下的容纳力,会让我们对正在生成的现实保持开放,保持佛教和其他冥想传统中所说的“无缚无着”的状态。佛教理论中有两个梵文词汇描述内心的微妙的执着和依附状态:“寻”是微微地“寻找”的杂念,它使我们的注意力执着在我们想要促成的事上面;“伺”是细细地“守候”的妄念,尽管它不是想促使事情的发生,但还是在盼望和执着于某种结果。不管是哪一种执着,都会使我们的心灵出现盲点,或者出现对现实中发生的其他某些方面的抵制情绪。要避免“寻伺”的陷阱,就必须不断保持“放得下”的心态。
当戴维提出坦率而又简明的问题:“你能不能帮助我观察整体?”他就已经放下了自己对公司领导力开发项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任何期望值。他还放下了对自己在小组里不需要别人帮助的强者形象的任何执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话代表了小组全体,并让许多人放下了原来执着的观念。通过放下执着,一种真正全新的局面得以出现。
本原觉知
通过“再引导”,我们开拓了意识疆界,包括最终得到一种对生成中的现实的敏感度。由此,我们得以突破主客体分离的观念,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我们就能达到“放得下”的境界。几千年来,哲学家们一直在探索“放得下”的问题,一些接受采访的人,包括瓦莱拉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认知心理学教授埃莉诺·罗施,则从现代科学的角度阐释了这种转变。
罗施是研究辨色和色彩分类的著名学者。她揭示了传统的正式和独立的色彩分类概念的局限性,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孤立的事物”。但是,就在自己的学术生涯达到成功的巅峰时,罗施却开始“情绪低落地四处寻找,并询问自己:‘有没有其他方法研究心理学?’”后来这个疑问引导了她对佛教、道教和冥想的研究,并在20年前促使她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些研究可能会“重塑心理学”。
奥托在采访罗施时请她解释自己的观点,即:科学研究要求“智慧的心灵”。罗施回答说,这一要求不仅限于科学家。“企业高管的工作和艺术家的工作没有本质的区别。伟大的艺术家的工作自然源于这种另外的层面,一直就是这样。”这个“另外的层面”是指一种不同的觉知。罗施认为,这种觉知的基础是“内心与外部世界不能分离”的观点,佛教中“没有自我的观念,没有独立存在的自我或客体。他们只是相互依赖的关系”。
但人心与世界一体的佛教理论是与西方思想格格不入的。罗施用了很长时间才开发了谈论这个问题的语言表达能力。最终她得出结论:只说“内心与外部世界不能分离”是不够的。她现在区分两种类型的觉知,即:“分析型觉知”和“本原觉知”。
在“认知科学提供的分析型图景中,世界由分离的客体和事件组成;人的心识则被看作一种决策机器,它必须为了了解世界而孤立并分辨那些客体和事件,还要找出对偶然事件的尽可能简单的预测,然后在记忆中存储并连接这些结果数据,以便形成对世界和自我的连贯一致的,但却是间接的再现和表述,从而通过对这些表述的回忆来完成唯一的价值创造,即:以成功进化的方式进行繁殖和生存活动”。
与此相反,“本原觉知”源于“各种相互连通的整体,而不是孤立的、偶然发生的局部事件;它源于超越时空的直接呈现”,而不是储存的东西的“再现”。“这种觉知是开放性的,不是确定不变的,而觉知活动本身就带有内在的无条件的价值感受,而不是有条件的有用性。”罗施说。从这种觉知引出的行动,是“自发的,而不是决策的结果”,是“富于同情心的,因为它基于比自我更大的整体”。
罗施告诉奥托,所有这些特点:超越时空、直接性、自发性、开放性、无条件的价值感受,以及富于同情心,都是同时发生的。这种同一性,就是“自然的状态”,就是“本源”。
“它就是‘心中之心之中心’。当我们连接到这个本源时,各种东西都越来越归于一条道路——在那里,目标、身体和心灵合为一体,而不是各奔东西。”罗施说。
按照罗施的理论,本原觉知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内心与外部世界本来就是同一个场中的不同方面。一旦我们与本源连接了,感知就“从整个场中出现。现代科学中最接近于描述这个现象的语言,我认为就是‘场’的概念。
“试想,所有正在发生的事,都是从这一深层的、有觉知的心底源头随时升起的即时的呈现。藏传佛教讲空性、光明和觉性能力,三者密不可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觉性能力实际上就是场自身的觉性,或者说,是这种更大的背景的自我觉知。”
问题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一生都沉浸在分析型觉知中,主体(“我”)和客体(“它”)处于隔离状态。分析型觉知并没有什么不好。它对许多活动来说都是有用和适当的,比如和机器打交道。但如果它变成唯一的觉知方法,那我们就会到处滥用它。
如果我们用分析型觉知的方法来与生命系统打交道,那就一定会出问题,因为生命场“对自身没有觉知”了。“对自身没有觉知的场,就会塌陷到主客体分离的单一维度的知觉里;这也是我们在世界上来去匆匆的行为模式。”其后果是,我们的行动没有得到整体信息的支持。罗施认为,正是这种与本源连通的匮乏,“或对其无知的状态,使我们陷入了糟糕的困境之中——个人、国家和社会文化都是这样”。
陌生的自我
用罗施的话说,当生命场达到“自觉”时,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局部小我”的认同感就消退了,而一种更大、更具生成力的自我的感受就出现了。这不是说个人的意识消失了,也不是说,对局部小我认同的消失,会导致个人责任感的消失。但会有一种“意识中心”的转换。这就是戴维所说的“自身达到这个不同的境界”的转换。
我们采访的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这种自我意识的开拓或“去中心化”的经历。瓦莱拉用“虚拟”或“脆弱的自我”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作为主体的自我”,更好地体验我们个人的、主观的观点。他认为主体“不是一个稳定、可靠的独立实体”。为了应付不断变化的情况,自我在不断“更新或再造自己……所以说这种虚拟性不仅意味着没有中心自我的存在,还意味着一种不断生成和消亡的‘脆弱的漂流’”。
瓦莱拉解释说,这个过程就好像不断重新塑造你自己,使自己在每一时刻都变得看似更真实。“但你知道,不断变得看似更真实,其实是一个悖论,它意味着变得更虚拟化,并因而更缺乏独立的实在性和确定性。”
他进一步补充说:“有智慧的生活就意味着不断放下自我,并让自我的那种虚拟性或脆弱性显现出来。和一位真正完全掌握这种能力的人在一起,你就会受到感染。和这样的人见面,会引起你的共鸣。你会很放松——这种生命状态有一种轻松愉快的内涵,有那种生命的愉悦。
“修为完美的人会不断地体悟当下……就是常处于事情正在发生的当下时空。但如果有个小我在那里说,‘啊哈,我正在体悟当下呢’,那就显然不能达到这种状态。”
研究20世纪日本著名禅学家西田几多郎(Kitaro Nishida)的学者大桥良芥(Ryosoke Ohashi)曾用“陌生的自我”来描述小我消失后出现的情况:“一种陌生的东西在支撑着我的存在。”东方传统往往把这叫“空无”:“这种空无在支撑着我的存在,以及我的所有关联。”但“在基督教传统的词汇里,这个绝对的陌生的东西也可以说是上帝。上帝与我同在,尽管西田几多郎并没有直接用‘上帝’一词。而那个非常陌生的东西就在我的自我里”。
斯坦福大学的迈克·瑞认为,这种自我感受的转变对创造性至关重要。他坚信,帮助学生开发深层创造力源泉的关键,在于以下两个问题:我的‘大我’是谁,以及我的使命是什么。瑞指出,当我们谈论“大我”时,“就指向更高的自我,也就是自己的神圣本体,最高的未来潜能。而问‘我的使命是什么’,就是在追问生命的志向目标,或自己生存的意义或天命”。
瓦莱拉补充说,去中心化的自我,就会自动转变与他人的关系。“脆弱的自我主体越能疏散开去,同情心就越发广泛……于是就打开了空间,来装下对他人的关爱。在去中心化的状态下,“他人变得更近了。团结友好、同情关爱,以及各种不同的相互关系的品质,都在去中心化里出现了。对我来说,那是宇宙给予我们的伟大礼物。因为我们并非独立的实在,不是私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也就更接近我们的真实自我……(那是)既有你,又有我。不是仅有我,而是一种‘我们整体性’”。
去中心化的自我的诞生,并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常态的局部小我是我们理解自己经历的方法,超越这个小我就会带来深刻的迷失感,而且在发生这种经历的时候,又很难用语言来描述。局部小我会发现很难把握去中心化的、脆弱的自我,并会试图把它降低到自己的标准上。即使有人试图用语言描述,也仍会感到很困难。在最初那次领导力开发项目设计研习营之后很久,戴维对约瑟夫说:“我和许多人谈到在那种不同的状态下的感受,身体上的感觉,耳朵里有声音,意识高度清醒,周围一切似乎都放慢了。别人和你谈话时,你能看到对方心里的想法,大家的谈话好像是一个整体。
“当我和别人描述这些经历时,就会发现对方身体在明显震动,因为他们也回忆起自己的经历,并会说 ‘没错!我也有过这种经历!’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回避?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描述它,或者因为害怕。这像是那种‘骗人的把戏’,但这又的确是我们的经历。我们只是害怕打开这扇窗户,因为别人可能会说三道四。”
服从于承诺奉献
当局部小我对自己意识的禁锢得到松绑以后,就会有一种瓦莱拉所说的“注意力的质变”,即“从‘追逐’转变到‘由它自然来’或顺其自然的‘拿得起’”。这里,“放弃控制欲”会演变成约瑟夫所说的“服从于承诺奉献”,即从自己的深层志向目标出发的、与整体大局协调的行动基调。
约瑟夫和奥托采访企业家时,请他们描述了自己创造历程中的深层体验,特别是为什么在各种逆境中能够锲而不舍。他们都回答说,自己感到被推动着、不能不继续前行,不可能“不做”。这种回答揭示了与通常意义上的意志力推动有所不同的承诺投入状态。
理解这种穿越针眼的方法之一,就是把它看成是从“感知”开始的、自我与外部世界关系转换的延续。我们从U的左侧开始下行时,会把外部世界看成某种既定的东西,某种“外在”的存在。逐渐地,我们会转变感知方法:到现象背后的生命过程的内部去观察。然后,从U的右侧上行时,我们会经历通过我们自己而呈现的现实世界。在U的左侧,世界先是“外在的”,后来是“外在生成中的”;在U的右侧,世界是“通过我们而生成的”。在左侧下行时,自我是外部世界的旁观者,世界是过去历史的创生物。而在U的右侧,自我变成从中生成未来的活水源头。
在U的底部发生了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这是个神秘的现象。这种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网的倒转,不能简单用语言来表达清楚,而且大家对它也会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这种经历包括像奥托家中失火而导致的一种“释然和自由”的感受;像彼得对“我就是听众,听众就是我”和“某种宝贵的礼物将呈现给我们”的经历;像贝蒂·苏感到出现“早已存在,但仍未创造出来的设计,自己以某种方式也成为其一部分”的经历;以及像约瑟夫的“深层的心灵开放”的经历。
这些都是体悟当下的第三个动作层面经历的例子,即如奥托所说的:当下体悟“正在通过我而生成的现实”。这个陈述中蕴含着正在生成的现实的意愿,并与罗施的另一段陈述相互对应。作为有长期学佛和修道经历的修习者和冥想者,罗施说:“如果你能顺着自己的本性走,当本性动时,你跟着它动,跟着它走足够远,真正放得下一切,那么你会发现,你其实就是那个本命元神,或原始自然……本命元神有知也有行,还有自己的行事方式,其实还有自己的伟大意愿。它是会这样做的,如果你能顺其自然——拿得起的话。”
引用道家本源的概念,罗施说,“这个意识知觉,这个小小的闪光,完全独立于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重要的事:我们的辉煌成就或碌碌无为,甚至生或死、醒或睡的状态,等等。这个想象的世界其实是从那里放射和展现出来的。这就是事情发生的方式。因而,行动也就变成支持整体的行动了,它包含一切,也成就一切需要做的事”。
从连通“本源”而发出的行动似乎“没有有意识的控制,甚至没有感觉到‘我’在做。它是整体的自发的产物”。而这种行动,用罗施的话说——“可能惊人地有效”。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产品经理(套装共18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