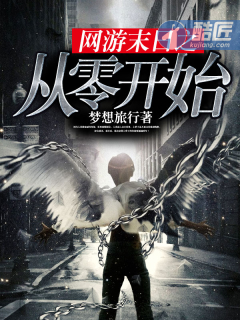第十章 价格的魔力:为什么我们喜欢买贵的东西?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十章 价格的魔力:为什么我们喜欢买贵的东西?
神奇的安慰疗法
如果你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胸口疼痛,心脏病专家很可能建议你接受一种叫作胸廓动脉结扎的手术,来治疗心绞痛。在这种手术中,医生给病人全身麻醉,从胸骨处切开胸腔,把胸腔内的动脉结扎起来。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心包膈动脉的压力增大,心肌血流得到改善。
很明显,这种手术很成功,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整整流行了20年。但是1955年的一天,西雅图的心脏病医生伦纳德·科布和几个同事对此产生了怀疑。这种疗法真的有效吗?真的起作用吗?科布决定采用一种非常大胆的方法来求证这种疗法的有效性:他要对1/2的病人实施真手术,对另外1/2的病人实施假手术。然后,他要看一看哪些病人的疼痛减轻了,哪些病人的健康状况真的改善了。换言之,对病人进行手术像切鱼片一样,硬生生一直切了25年,心脏科的医生们终于要对这种手术做一次科学的、严格控制下的检测,以判定它的有效程度究竟如何。
为了进行上面所说的这一测试,科布医生按照传统的方式给一部分病人实施了手术,对另外一些人则实施了安慰性手术。真正实施手术时,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实施麻醉,切开病人胸腔,结扎胸腔动脉。施行安慰手术的,手术医生则只是实施麻醉,用手术刀把病人胸部肌肉划开两道,然后缝合,留两道细微的缝合痕迹,仅此而已。
结果令人惊异无比。做过胸腔动脉结扎的和没有真正做过手术的两组病人都说疼痛减轻了。两组病人的手术效果都持续了大约三个月——然后又开始抱怨胸口疼痛复发。同时,心电图显示,做过真正手术的病人与做过安慰性手术病人的状况没有区别。换言之,传统的手术治疗好像起到了短期减轻疼痛的作用,但安慰手术也是这样。到头来,两种手术疗法都没有产生长期疗效。
近年来,医生们又对另一种医疗方法做了类似的测试,结果也惊人相似。早在1993年,J. B. 莫斯利,一位整形外科医生,对于某种针对膝部关节痛所实施的关节镜手术越来越感到怀疑。这种疗法真的有效吗?莫斯利医生和他的同事们从休斯敦退伍军人医院招募了180名关节炎患者,并把他们分成了三个组。
第一组实施传统疗法:实施麻醉,在膝盖部位切三刀,置入关节镜,切除软骨,矫正异常软组织,用10升盐水清洗整个膝部。第二组的疗法是:麻醉,膝部切三刀,置入关节镜,用盐水清洗膝部,但是不切除软骨。第三组用的是安慰疗法,看起来就像前两组一样,既有麻醉又有切口,手术过程的时间也相同,但是关节内没有置入关节镜,换言之,这只是一次模拟手术。
在手术后的两年里,医生对三个组的病人(就像其他的安慰疗法实验一样,其中也包括志愿者)都做了跟踪测试,以确定疼痛是否减轻及减轻的程度,并且检测了所有参与者恢复正常行走和爬楼梯所需要的时间。效果怎么样?实施全套手术和单独置入关节镜的两组病人非常满意,纷纷表示要向亲戚朋友推荐这种疗法。但奇怪的是,出了一条爆炸性消息,实施安慰疗法的那个组,也同样减轻了疼痛,同样恢复了正常行走,就和真正做过手术的那两组病人一样。针对这一使人惊诧的结果,莫斯利实验小组成员之一的内尔达·雷伊医生写道:“对于膝部关节炎患者,实施关节镜置入和软骨组织清理手术的效力,竟然与安慰疗法不相上下。这一事实让我们质疑,在这种手术上花的10亿美元是否应该用到更需要它的地方。”
如果你能预料这一结果会引发原子弹爆炸般的效果,那你可就猜对了。自从这篇研究报告被刊登在2002年7月11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以后,有些医生就大吵大嚷,声称该报告造假,在不同场合利用各种形式对研究的方法和成果提出质疑。莫斯利医生争辩说,这一研究是经过详尽安排、严格实施的。“作为医生,最重要的不是操刀技术如何精湛,而是手术后患者的康复情况。那些一年到头经常实施关节镜手术的医生,毫无疑问,对安慰疗法的效力感到尴尬。你们可以想象得出,他们会动用一切力量,寻找一切理由来否定我们的研究成果。”
不管你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一研究的结果,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应该给这些特定患者的关节镜手术打个问号,同时加强对各种医疗手段有效性的求证。
在第九章里,我们看到,预期可能会改变人们对体验的认识与品评。在本章中,我们不但将看到信念和预期对人们视觉、味觉及其他感官现象认识与解析的影响,还会看到人们的预期能够改变他们的主观,甚至客观体验,从而对他们施加影响(有时这种影响非常巨大)。
最重要的是,我想探索安慰疗法目前尚未被人们了解的一面,也就是价格在这一现象中的作用。高价的药品是否会比低价的让我们感觉更有效?高价的药品真的从生理学意义上比低价品牌有更好的药效吗?那么,高价的医疗手段,新一代的医疗器械,例如,数字化心脏起搏器和高科技支架,又会怎样呢?价格真的影响疗效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岂不是表明美国的医疗保健费用支出还要继续飙升?好吧,我们从头道来。
“安慰疗法”的英文单词“placebo”来自拉丁文——“我会让你满意”。这个词在公元14世纪专指丧礼上雇来在死者灵前号丧的假哭者。1785年,它出现在《新医学词典》中,指的是“非正规的边缘医疗方法或药物”。
安慰疗法的效力最早见诸医学文献记录是在1794年,一个名叫杰尔比的意大利医生发现了一桩奇怪的事情:在疼痛的牙齿上抹一种昆虫的分泌物可以止疼,这种止疼效果能够持续一年的时间。杰尔比陆续给牙疼病人使用这种昆虫分泌物,并且对病人的反应做了非常详尽的记录。抹过这种“药”的病人中有68%对他说,一年之内他们的牙没有再疼过。我们没有关于杰尔比医生和昆虫分泌物更详细的资料,但可以相当肯定,他使用的昆虫分泌物与治疗牙疼无关。但问题在于,杰尔比相信它有用,而且他的多数病人也这样认为。
当然了,市场上的安慰剂不仅仅是杰尔比医生的昆虫分泌物。近代以前,几乎所有的药品都是安慰剂。蟾蜍眼睛、蝙蝠翅膀、晒干的狐狸肺、水银、矿泉水、可卡因、电击器等,所有这一切都被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方在市场上兜售过。当年,就在林肯躺在福特剧院大街的对面奄奄一息的垂危时刻,据说他的医生在他的伤口上涂过一种“木乃伊膏”——将埃及木乃伊磨成粉末制成的膏状体,据说可以治疗癫痫、脓疮、皮疹、骨折、麻痹、偏头痛、溃疡,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疾病与创伤。甚至到了1908年,“正宗埃及木乃伊”还被印刷在默克公司的销售宣传册上供人订购——直到今天,世界上可能某些地方仍然在使用它。
木乃伊粉其实还算不上最恐怖的药。17世纪有一个“包治百病”的药方是这样写的:“红发新亡男尸,生前未受伤,无表皮损害,年龄24岁,死亡时间一天之内,以绞刑、轮刑或尖桩处死者为佳……放置于日光和月光下一天一夜,然后切为片状或粗条。撒少许芦荟于其上,以减轻苦味。”
我们可能认为自己与那时的人已经大不相同了,其实不然。安慰疗法对我们仍然具有魔力。例如,多年来医生一直采取切除腹部疤痕组织的方法,认为这样做可以消除慢性腹痛——直到后来,研究人员在严格控制下做了模拟手术,患者同样反映说疼痛消失。恩卡胺、氟卡胺,还有美西律,这些都是医生经常开给心律不齐病人的标示外使用药物(off–label,即用于药品说明书范围之外),但最近有研究发现,它们可能引起心脏停搏。研究人员对6种最常用的抗抑郁剂的疗效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其中75%的药品用安慰剂代替亦可以取得相同疗效。治疗帕金森的脑部手术也同样如此,医生给几个患者的颅骨上钻了孔,并没有实施全部手术,以检测其疗效,结果发现真假手术的效果相同。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有人可能争辩说,这些现代医疗手段和药物都是依据最良好的意图发展起来的。这话不假,但过去人们在使用埃及木乃伊粉时也是如此。有些时候,木乃伊粉具有与当时其他所有药品相同(起码不亚于)的疗效。
安慰疗法与安慰剂的作用靠的是暗示的力量,它起作用是因为人们的信任。只要你看见医生,就会感觉好一些了。你服下一片药,就会感觉又好了一些。如果医生是一位有名的专家,或者你吞下的是某种疗效卓著的名药,你的感觉就更好了。不过,暗示是怎样影响我们的呢?
总的来说,有两种机制能够形成预期,使安慰疗法与安慰剂起作用。其一是信念——我们对某种药品、某个手术或有关人员的信赖或信任。有些时候,只要医生或护士来到我们面前安慰鼓励一番,不仅会让我们精神上感觉好一些,还会真的激活我们体内的康复功能。仅仅看到医生对某一治疗方案或手术表现出的热情,就可能使患者未经治疗就产生某种有效的感觉。
第二个机制是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著名的条件反射实验(狗一听到铃响就流口水)一样,经过重复的体验,人的体内就能建立起一种期望。假如你每天夜晚都打电话预订比萨饼,那么送外卖的人一按门铃,还没有闻到比萨饼的香味,你的消化液就开始分泌了。或者你正在蜜月中,和你新婚的妻子偎依在沙发里,你眼看着壁炉里噼里啪啦的火苗,耳鬓厮磨的爱欲会促使你的大脑释放内啡肽,为你们下一步的亲热做铺垫,把你的这种幸福感推向爱河深处,温柔乡里。
关于疼痛,良好的预期能够释放荷尔蒙和神经传递素,诸如内啡肽和镇静素,不仅能抑制疼痛,还能产生强烈的快感(内啡肽能激发与可卡因相似的感受体)。例如,我清楚地记得当年躺在烧伤病房里,疼痛难忍,但只要一看到护士走过来,手里的注射器针尖还在滴着止痛剂,我就会长长地松一口气,止痛剂终于来了!我的大脑马上就会开始分泌抑制疼痛的阿片肽,尽管针头还没有扎进我的皮肤。
价格越贵的药越有效吗?
熟悉未必产生轻视,但它的确能产生预期。品牌、包装还有关爱之人所做的承诺,都能使我们感觉舒服一些。但是,价格又怎样呢?某种药品的价格能够影响我们对它的预期吗?
一说到价格偏见,我们很容易想到4 000美元的沙发肯定比400美元的坐得舒服;设计师款的牛仔裤肯定比沃尔玛的普通货缝制得更好,穿着更舒服;高级电动砂轮机肯定比低档货好用;皇朝大饭店的烤鸭(每只19.95美元)肯定比王老五面条铺的烤鸭(每只10.95美元)强得多。但这些隐含的质量差别会影响实际的体验吗?这种影响能进而延伸到主观体验——诸如我们对药物的反应之中吗?
比如说,价格低廉的止痛片就不管用,价格高的就立竿见影吗?冬天感冒,在折扣店买的感冒药就不见效,而大药房的高价药吃了就觉得管用吗?你患哮喘病,普通药品不见效,著名厂家刚上市的新药真的更好吗?换言之,药品也和中国菜、沙发、牛仔裤、工具一样吗?我们能够断定高价格等于高质量,我们的预期可能被直接转换成产品的客观功效吗?
这一问题特别重要。事实上,即使你穿的是低价牛仔裤,别人也不会说什么。只要自制一点儿,我们也能对那些价格昂贵的名牌敬而远之。但是,事关身体健康,你还能够讨价还价吗?普通感冒先放下不说,如果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刻,我们还有多少人会锱铢必较呢?不会的——我们会为自己、为孩子、为亲人竭尽全力,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一定要选最好的药。
如果我们想选择最好的,那我们会不会感觉价格高的药品比价格低的有效?价格的高低真的能让我们感觉不一样吗?几年前,我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生丽贝卡·韦伯、斯坦福大学教授巴巴·希夫、济夫·卡蒙做了一系列实验,决定将问题弄个明白。
实验
假设你正在参加一项实验,测试一种名叫维拉多尼–RX的新型止痛药的效力(在实际的实验中,我们找了大约100名波士顿成年志愿者,现在我们让你来代替他们)。
早上,你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传媒实验室。塔娅·利里是一位年轻女性,身着整齐利落的职业套装(这与麻省理工学院学生们的着装形成鲜明对照),她热情地接待了你。她说话带着点儿俄罗斯口音,胸前带照片的识别卡标明她是维拉制药公司的代表。塔娅请你花点儿时间阅读一下维拉多尼–RX的简介资料。你向周围扫了一眼,注意到房间的陈设布置就好像医院的办公室:被人翻旧了的《时代》和《新闻周刊》散乱地随意放着;几份维拉多尼–RX的简介资料摊开放在桌面上;旁边有一只用来当作笔筒的杯子,上面印着公司的徽标,徽标设计得很漂亮。“维拉多尼是阿片肽家族一种疗效卓著的新药。”你从简介里读到:“在实验者与被实验者双方都不知情的条件下,临床实验证明,服用维拉多尼的患者中,92%以上的人在服用10分钟内报告疼痛显著减轻,止痛效果可持续8个小时。”价钱呢?简介中说,2.5美元一粒。
你刚一读完简介,塔娅就把丽贝卡·韦伯叫进来,自己出去了。丽贝卡穿着一件白大褂,脖子上挂着听诊器。她询问了几个有关你本人病史和家族病史的问题,又拿起听诊器检查,听了你的心音,接着测量了你的血压,然后把你固定在一台样子很复杂的机器上。她从机器上拉出带电极片的电线,电极片上面涂了绿色的电极膏,缠到了你的手腕上。她解释说,这是一台电击发生器,用来测量你的疼痛敏感度和疼痛忍耐力。
丽贝卡把手放到你的手腕上,通过电线向电极片输送了几股电流。开头的几下电击,你只感到有点儿不舒服。后来就感觉疼了,疼痛越来越厉害,最后你睁大双眼,心跳加速。她记录了你的反应。然后她又给你施行了一种新的电击。这一次,她操纵电击强度从小到大不断变换频率以随时改变疼痛强度:有时非常疼,有时只是稍微有点儿不舒服。每一次电击过后,她都要求你做记录,记下你感受到的疼痛强度。屏幕上有一道从左到右的显示条(直观疼痛量化显示),从左端的“无疼痛感”到右端的“非常疼痛”,你点击鼠标在上面选择。
这一番折磨告一段落,你抬起眼睛向上方看。丽贝卡站在你面前,一只手中是一粒维拉多尼,另一只手里是一杯水。“服药后15分钟,药效达到最高值。”她告诉你。你把药片一口吞下,到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翻看那几本过期的《时代》和《新闻周刊》等待药片发挥效力。
15分钟以后,丽贝卡又一次把绿色油膏涂到电极板上,笑容可掬地问:“准备好继续实验了吗?”你有点儿紧张,但还是说:“没问题,开始吧。”你抬起眼睛看着机器,电击再次开始。和刚才一样,每次电击以后,你都会记录下疼痛的感觉。不过你现在的感觉可大不相同了。一定是维拉多尼–RX的作用!疼痛不再那么剧烈难忍了。你带着对维拉多尼非常高的评价离开了实验室。实际上,你正盼望着你家附近的药店赶快卖这种药呢。
一点儿也不错,多数实验参与者也都得出了这一结论。在服用维拉多尼并接受电击后,几乎所有人都说疼痛减轻。但是,如果所谓的“维拉多尼”只不过是普通的维生素C胶囊,意义就非同一般了。
从这一实验里,可以看到我们的药片发挥了安慰剂的效力。但是,假如我们把维拉多尼的定价改了,比如说,我们把它的价格从每片2.5美元降到10美分,参与者的反应会有不同吗?
下一个测试,我们把药品简介上原来的价格(每片2.5美元)划掉,添上新的折扣价10美分。这样能够改变参与者的反应吗?非常正确。价格是每片2.5美元时,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声称该药能减少疼痛;但是当价格降到10美分后,这样说的人就只剩1/2了。
不仅如此,我们还发现价格与安慰疗效的关系因人而异,近期备受疼痛折磨的人,对价格与安慰疗效的关联有特别深刻的体会。换言之,人们受疼痛折磨越多,对止痛药品的依赖也越大,这种关联感也就越强烈:价格越低,他们感觉受益越少。在药品方面,我们发现的是,一分钱,一分货,你付多少钱,就有多大疗效,价格能够改变体验。
我们从另外一项实验里也不约而同地得到了同样的结论。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在艾奥瓦大学做了一项实验,对一部分学生进行跟踪调查,以了解他们在患了感冒以后,是会花全价买药,还是会到折扣商店买降价药,以及在两处买的药的效果是否有差别。到了学期末,13个参与者说他们买的是全价药,16个说买的是降价药。哪些人买的药更有效?我认为你们应该猜到了:13个花全价买药的学生认为他们比那些从折扣店买药的人痊愈得快多了。你们看,非处方感冒药的疗效取决于你付了多少钱。
从我们的医药实验中可以看到价格是怎样驱动安慰疗效的。那么,价格是否会影响日常消费品呢?我们找到一种绝好的实验物——SoBe(肾上腺素功能饮料),一种号称能“提高运动能力”,并且提供“超常机能”的饮料。
实验
第一次实验,我们把售货柜台摆在大学健身馆入口处,出售SoBe。第一组学生按正常价格付款。第二组学生也付款购买,但付的大约是正常价格的1/2。锻炼结束后,我们问他们与正常运动后相比,现在感觉怎么样,是感觉更轻松一些还是感觉更累?喝过饮料的两个组都说感觉比平常轻松了一些。这种回答似乎有些道理,尤其是考虑到每瓶SoBe中都含有相当比例的咖啡因。
但我们关心的是价格的影响,而非咖啡因的影响。较高价格的SoBe比半价的更能减轻疲劳吗?你们通过维拉多尼的实验就可以想象到,结果是这样的。买较高价格饮料的学生比那些买半价饮料的学生感到更加轻松。
这个实验很有意思,但是它是以参与者对自己状态的印象为基础的,这是他们的主观意见。怎样才能更直接、更客观地对SoBe进行测试呢?我们想出一个办法:SoBe宣称有“提高大脑活力”的功效。于是,我们决定用一系列单词组合测验来对这一功效进行检验。
测验是这样进行的。1/2的学生花全价买SoBe,另外1/2则以半价买入(我们要求他们用信用卡付款,实际上是由家长付钱)。喝下饮料后,我们让学生们看了10分钟的电影(我们解释说,这是为了让饮料在体内充分发挥效力)。然后我们发给他们每人15道单词组合题,要求他们在30分钟内把给出的字母组合成单词,越多越好,最多者为胜出。
我们事先已经让一部分没有喝SoBe的学生做过摸底测验,并有了平均的成绩标准。这些学生在15道题中平均答对9道。用这些题来测试喝过SoBe的学生,结果会怎样呢?花全价买饮料的学生平均做对了9道——与根本没喝过SoBe的学生相同。更有意思的是,花半价买饮料的这些人的平均成绩为:答对6.5道题。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什么结论?价格确实决定成绩,在这一案例中,两组学生组词的表现有28%的差别。
这样看来,SoBe一点儿也没有使人的大脑更灵活。这能说明该产品就像银样镴枪头——中看不中用吗?为了得出确切答案,我们另做一项测试。我们在单词组合测验小册子的封面上印了如下信息:“SoBe显示出改善思维功能的效果,饮用后可以提高,例如组词测验的成绩。”我们还编造了一些数据,说SoBe网站声称已有50多项研究成果肯定了该产品的功效。
结果怎么样?花全价买饮料的学生的平均成绩仍然比花半价买饮料的好。但同时,试题封面所印的有关信息也发生了作用。全价组和半价组的学生,读到了这些信息,受到提高成绩的“启动”,他们的成绩要高于试题封面上什么都没印的那两组。这一次,SoBe真的使人的大脑更灵活了。我们吹嘘说有50多项研究结果表明SoBe能够改善思维功能,那些付半价买饮料的人平均每人多答对了0.6道题,但是同样被我们忽悠了的付全价的学生,竟然平均每人多答对了3.3道题!换言之,饮料瓶上的信息(还有试题封面上的)与价格相加的威力,比瓶子里饮料本身的威力要大得多(当然,这一点可能还有争议)。
那么,我们在价格上打了折扣,注定得到的东西就差更吗?如果我们依赖自己非理性的直觉,实际上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到半价商品,我们本能地断定它的质量就比全价的差——事实上,是我们把它看得差了,它也就真的变差了。怎么纠正呢?如果我们定下心来,理性地拿产品与价格做一番比较,就能克服那种无意识的冲动,不再把产品的销售价格与内在质量挂钩了。
我们在一系列实验中对此做了测试,结果是那些能够平静地考虑价格与质量关系的消费者,不大可能认为半价饮料的效果一定就差(那么,他们做起组词测验来也比这样认为的人的成绩要好)。这一结果不但给我们指出如何解决价格与安慰疗法、安慰剂之间关系,还指出了“便宜没好货”的说法其实是对低价的一种无意识的反应。
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了价格怎样驱动安慰疗法、安慰剂、止痛剂和能量饮料的功效。但是还有一点需要考虑:安慰疗法和安慰剂有作用,我们是否就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了?或者说,安慰疗法和安慰剂就是有害的——是江湖郎中的骗局,不管人们感觉有用没用,都应该一律摒弃吗?在你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跟你打个赌。如果你发现了一种安慰剂或安慰疗法,不仅能使你感觉有效,还真的能治好你的病,你以后还会再用它吗?你如果是医生,会怎么办?你明知是安慰剂或安慰疗法,你还会给病人用吗?我再讲个故事来把话说得更明白一些。
安慰疗法的去与留
公元800年,教皇利奥三世为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加冕,建立了神权与政权的直接联系。从那时起,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以及后来欧洲各国的国王,都被笼罩上君权神授的光环。由此引申出所谓的“御手触摸”——能治愈百病。整个中世纪,历朝历代的史学家都在编年史中记载,伟大的君主经常驾临他的臣民中间,用触摸的方式为他们治病。例如,英王查理二世(1630—1685年)在位期间曾为大约100 000人实行触摸治疗,记录中甚至有名有姓地记载了几名美洲大陆的殖民者,不远万里从新大陆赶回欧洲,为的就是在查理二世经过的路上接受触摸,治愈疾病。
“御手触摸”真的有效吗?如果经过御手触摸,没有人病情见好,那么这种做法应该就逐步消失了。但从历史记录来看,据说医好有数千人之多。淋巴结核病,那时经常被误诊为麻风病,此病会损毁人的容貌及皮肤,病人必须与外界社会隔离,据说,它就是因为国王之手的触摸才得以绝迹的。莎士比亚在《麦克白》第四场第三幕里写道:“得怪病的人们,全身肿胀溃烂,惨不忍睹……(陛下)念着神圣的祈祷词,为他们的痊愈祝福。”御手触摸的传奇一直持续到17世纪20年代,那时人们不再相信君权出于神授了——而且(我们可以想象)“新的,改进了的”埃及木乃伊膏之类的“先进”疗法使御手触摸相形见绌。
人们一想到诸如御手触摸一类的安慰疗法,一般都会斥之为“仅仅是心理作用”。但是,安慰疗法的力量不是“仅仅”两个字就可以说完的,事实上,它显示了我们大脑对身体的神奇控制方式。大脑如何实行这种神奇的控制,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当然,其中某些作用肯定与降低压力,改变荷尔蒙分泌,调节免疫系统等有关。我们对大脑与身体的关联了解得越多,过去一些黑白分明的事物反而变得模糊不清。最明显不过的就是安慰疗法和安慰剂了。
现实中,医生一直都在使用安慰疗法和安慰剂。例如,2003年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医生给患咽喉炎的病人使用抗生素,后来发现其中超过1/3的病例是病毒引起,抗生素对这些患者毫无作用(同时说明了为什么对抗生素产生抵抗的人越来越多,这对我们大家都构成威胁)。但是,你认为医生对病毒性感冒的患者就不再使用抗生素了吗?即使医生知道某些感冒是病毒性的而不是病菌性的,他们也仍然认为患者需要某种安慰。最常见的情况,病人想拿到一张处方,但是如果内科医生用这样的方式来满足病人的心理需要,正确吗?
事实上,医生一直在使用安慰疗法和安慰剂,但这并不代表他们真的想这样做,我猜测,这种做法使他们心里也有些不舒服。职业的训练使他们自认为是科学一族,有问题应该到现代医学的最高技术中寻找答案。他们以白衣天使自诩,而非巫医骗子和江湖郎中。所以即便扪心自问,他们也很难承认,他们在行医过程中竟然会使用安慰疗法来增进患者的健康。假如一个医生,不管多么不情愿,但他可以使用一种有效的安慰疗法来救治病人,那么,他应该积极热心地去开这个处方吗?说到底,医生对一种治疗方案是否热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实际疗效。
还有另一个问题,有关美国的医疗保健事业。美国的医疗保健投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已经是西方国家中最高的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人们感觉高价药品(50美分的阿司匹林)比低价药品(1美分的阿司匹林)更有效这一现实呢?我们是该放任人们的非理性,继续提高医疗保健的成本呢,还是坚持要求人们使用市场上最便宜的普通药物及医疗手段,而不采用那些疗效更好、价钱也更贵的新药呢?我们该如何建构成本与共同负担的医疗机制使其发挥最大效能,如何让需要的群体能买到廉价药品而不降低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医疗水平?这些都是建构医疗保健制度最关键、最复杂的问题。
安慰疗法和安慰剂也令市场营销人员左右为难。职业道德要求他们创造可预期价值,但如果过度宣传某个产品的客观价值,根据夸大的程度,就可能成了歪曲事实,甚至成了散布谣言。我们看到,对医药、软饮料、大众化妆品和汽车来说,预期价值可能成为真正价值。如果人们从某一产品中获得了比较大的满意度,是否就是营销人员炒作的结果呢?我们对安慰疗法想得越仔细,对信念与现实之间的模糊界限考虑得越多,这些问题就越难回答。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认为,对我们的信念和各种医疗方法的疗效所实施的实验都是有价值的。同时,我很清楚上述实验,特别是关于医学上安慰疗法的实验,引发了很多伦理问题。的确,我在这一章开头举出的胸廓动脉结扎手术问题就引起了伦理方面的争议:很多人强烈呼吁,反对给病人实施假手术。
为了弄清楚某一疗法是否应该继续使用,就把它暂停下来,这样很可能牺牲眼下一些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一想到这里就让人很难接受。例如虽然一个患癌症的孩子正在接受的是安慰疗法,为的是几年以后患同样病症的其他人可能会有更好的治疗方法,但这仍令人难以接受。
同时,如果因此而停止安慰疗法的实验,同样令人难以接受。这种疗法可能会让成千上万的人接受无作用(有风险)的手术。在美国,各个步骤都经过科学测试的外科手术很少。因此,我们实际上并不了解很多手术是否真能治愈疾病,或者像从前的一些手术一样,是因为安慰疗效才取得效果。由此,我们会经常想,是否应该先更仔细地研究某些疗法和手术,在真正弄清楚它们之前不要行动。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关于一种治疗方法,我觉得我是受了虚假宣传的引诱,但实际上,我不过是经历了一次痛苦的体验。
应该让烧伤病人穿紧身衣吗?
那时我在医院里住了漫长的两个月,我的专业理疗师告诉我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有一种叫作“Jobst”的高科技理疗紧身套装,是专门为我这样的严重烧伤病人设计制造的,它的质地像丝绸一样柔滑,会对我仅存的少许皮肤施加压力,增进皮肤生长。她告诉我全世界一共有两个生产厂家,一家在爱尔兰,另一家在美国。我可以量身定做。她还告诉我,这套紧身服包括裤子、上衣、手套,还有面罩,因为尺寸完全合身,所以能一直紧贴我的皮肤,活动的时候,它会轻轻地按摩我的皮肤,使皮肤上的红斑和过度生长的疤痕逐渐消失。
我是多么兴奋!我的理疗医师舒拉告诉我,这套紧身服有多么奇妙,还有不同的颜色,我立即想象我从头到脚都包在紧身服里面,像电影里的蝙蝠侠,但舒拉马上给我泼了点儿冷水,说其实只有两种颜色,棕褐色的是专门给白人的,黑色的是给黑人的。她还说,过去曾有人穿这样的紧身服去银行,被人们误以为是抢银行的强盗,打电话报警。现在你再订紧身服,工厂会在胸部印上特别的说明,用以解释你的身份。
她的话并没有扫我的兴,相反更增加了我的兴趣。我暗自发笑,想到穿上它走在大街上,人们都不认识我,那有多好。除了我的眼睛和嘴巴,别人什么也看不到,他们也看不到我的伤疤了。
我想象着这套丝绸般的紧身衣,认为在它到来之前,一切痛苦我都能忍受。时间一周一周过去,衣服终于送到了。第一次穿,舒拉过来帮忙。我们先穿裤子:她把裤子打开,带着棕褐色的光泽,开始往腿上穿。那种感觉可不像柔滑的丝绸在轻轻地按摩我的伤疤,而是像帆布一样又粗又硬,仿佛要把我的伤疤扯开。但我还是不甘心,还在想着从头到脚全穿上了,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几分钟以后,事情很明显,从度身定做到紧身衣到货,这期间我的体重增加了(他们每天给我喂7 000卡路里的食物和30个鸡蛋以增进我康复的速度)。紧身衣不太合身。不管怎样,我已经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了。最后,又拉又扯,大家一起耐心努力,我终于把它全部穿上了。长袖上衣紧紧地压迫胸部、肩膀和胳臂,面罩紧紧裹在脸上,长裤从脚趾一直向上套到臀腹部,另外还有手套。全身只有脚趾尖、眼睛、耳朵和嘴露在外面,其他部分都被包裹到了棕褐色的紧身衣里面。
紧身衣的压力似乎每一分钟都在增加,里面燥热难忍,伤疤处血液循环不畅,热量使伤疤部位充血,变得又红又痒。胸前解释“我并非强盗”的标志也不顶用,它用的是英文,而不是希伯来文,因而毫无价值。我的美梦没有成真。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它脱下来,理疗师又重新给我量了尺寸,把详细资料寄到爱尔兰,再定做一套更合身的。
新的紧身衣的确合身了,但除此之外也好不到哪里去。我被这种疗法折磨了好几个月——又痒又痛,得拼命挣扎才能穿上,一不小心就会把刚长出来的嫩皮磨破(新皮磨破了之后得很长时间才能长好)。最后,我知道这套紧身衣根本没有效果,起码对我是这样。我身上被它覆盖的部分和未覆盖的部分没有任何区别,我从它那里得到的只有受罪。
你看,让烧伤科病人参加实验,用来测试紧身衣的效果(它的不同材质、不同的压力水平等),这种做法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若要让某个人参与有关安慰疗法的实验就更加困难了。如果没有充足的理由,让那么多病人多年来忍受某些疗法引起的痛苦,在道义上也说不过去。
如果将这种合成材料紧身衣与其他方法做对比测试,如与某种安慰疗法做对比测试,后者可能更有利于减少我的日常痛苦。它或许还会激发新的实验方式——真的有效的方式。他们没有做这样的实验,代价是让我和其他跟我一样的病人白白遭受痛苦。
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对安慰疗法、安慰剂进行实验呢?对医学方法和安慰疗法进行测试和实验,牵涉道义上的两难困境,这是客观现实。我们应该对这种实验可能带来的好处与实验的成本和代价加以比较,因此,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无休止地对安慰疗法一直实验下去。但就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实验还远远不够。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