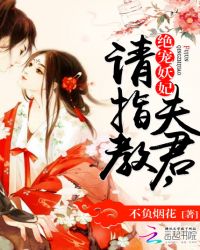第二章 暴众心理学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第二章 暴众心理学
是什么驱使一个接近900人的团体决定集体参与谋杀和自杀?这是1978年在圭亚那发生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大屠杀之后,人们不得不提出的质疑。在邪教组织人民圣殿教的创立者,自封为“族长”的吉姆·琼斯(Jim Jones)的唆使下,他的信徒们先是谋杀了一名美国国会议员、三名新闻记者和一名叛逃者,接着又将“枪口”对准他们自己。父母喂自己的孩子喝下含氰化物毒药的果汁后,集体喝下混着氰化物和镇静剂的毒药自杀。吉姆·琼斯于同一天开枪自杀。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想象怎么有人会被操纵并集体犯下如此极端残暴、令人发指的罪行。琼斯于195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立人民圣殿教,这个邪教不断壮大并随后迁址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一系列的纪录片曝光了其内部的虐待和剥削行为。1974年,琼斯离开美国并建立了看似是农业合作社项目的宗教基地“琼斯镇”。许多信徒都加入了琼斯镇,但仅在4年之后,这些信徒就在至少表面上看是自愿的“革命自杀”中过早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为什么这么多原本是循规蹈矩、遵纪守法的人都听任一个人的摆布呢?这个问题不仅和琼斯镇大屠杀这个独立的暴力事件有关,也能和诸多的历史事件联系起来。鉴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和其间的种种暴行,许多社会科学家都曾思考过为何如此之多的普通人在大屠杀的暴行面前,不仅袖手旁观,而且还积极地参与其中。而这种极端的偏好和暴行在历史的长河中还并非个例。我们在后面的章节里会看到,其他社会心理学的实验观察了在社会影响驱动下的破坏性暴力行为,尤其是许多人不假思索地屈从于强权的倾向性。原本普普通通的人可以在其领袖的唆使下犯下诸多残暴的罪行,例如,对他人施以高压电刑和其他非人道手段。这些行为都无法用常规的经济学模型来解释,因为这些模型中的人应该都是理智地选择群聚的理性、自律及利己的个体。现实的人类经验要混乱得多,而抽象的经济学模型无法模拟和描述现实世界社会和心理层面的复杂性。在本章中,我们将超脱于井然有序的经济学世界,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观察和研究盲从者与叛逆者。
集体型从众和群体的智慧
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了经济学家将从众行为解释为一种明智的策略。利己型从众也许会给团体、经济和整体社会带来麻烦,但是从个体的经济视角来看,跟随他人常常是一种明智的策略。另一种颇为不同的从众行为是集体型从众(collective herding)。集体型从众和利己的个体的所想、所需没有关系,而是关乎驱动团体的整体激励及目标。团体的构成方式通常是无法通过单个个体的视角来解释的。
虽然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形成的基础截然不同,但是两者也有共通点。在研究群体智慧的文献中,一些关于集体型从众的观点能够解释为何一个群体能够好似单个理性个体那样运转。相较于个体独自决策,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人有时能够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群体智慧这一概念脱胎于18世纪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尼古拉·孔多塞,其分析奠定了“孔多塞陪审团定理”(Condorcet’s jury principle)的基础。作为我们是怎样将希望寄托在集体判断的智慧上的真实例证,这条定理时常被应用在陪审团身上。但是孔多塞最初的分析和陪审团可没有任何关系,而是非常抽象的数学公式推导:孔多塞最初假设有一对决策者,其中每个人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都略高于其犯错的可能性,即假设每人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略高于50%。接着他将其他决策者加进决策过程中来,并分析会发生的情况。孔多塞的数学推导显示,决策者的数量越多,整个团体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也就越高。最终,随着最初的两名决策者变成了一整个决策群体,这个群体做出的集体决策的正确率将接近100%。如果这个群体中的决策者的数量无限大,那么这个群体的集体决策几乎一定就是完全正确的。看起来这是个完美的结论,但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与之相反的例子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孔多塞的数学推导同样显示,如果单个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略低于其犯错的可能性,即假设每个决策者做出正确决策的概率略低于50%,那么集体做出的决策就没那么美好了。随着决策者的数量从最初的两名变成一大群,这个群体的集体决策的正确率将接近0,在第二个场景下,决策者数量无限大的群体的集体决策几乎一定就是完全错误的。
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在我们的群体中的个体都是更有可能做出正确选择的人呢?美国心理学家大卫·布德斯库(David Budescu)和伊娃·陈(Eva Chen)罗列了一些策略,利用更加睿智的一批人的智慧优化集体的决策。如何能将一个群体设计得符合孔多塞假设的理想状态,以确保群体的智慧得以施展呢?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将所有不够睿智的个体排除在群体决策之外:忽略那些以前犯错次数多过正确次数的人的决策判断。布德斯库和陈博士通过分析综合应急评估(Aggregate Contingent Estimation,ACE)项目的数据来支撑他们的假设。ACE项目的数据库网站汇集了被称作“法官”的预测者的判断结果,这些自愿参与的预测者并不一定得是传统意义上的专家,他们被要求对一系列事件进行预测,话题覆盖经济、政治、医疗和科技等领域。布德斯库和陈收集和分析从ACE项目网站获取的数据以评估1 233名预测者从2010年1月至2012年1月期间对于104个事件的预测结果,并根据预测者的预测准确性对这些“法官”进行打分。通过识别出表现最好的预测者,并淘汰预测准确率低于平均水平的预测者,布德斯库和陈显示他们的选择机制可以将预测的准确率提高约28%。
然而,将群体的智慧融入现实生活中的决策过程并不容易。在他们的研究中,布德斯库和陈是以历史预测成绩为标准筛选出更优秀的“法官”的,但是在一个充满极度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我们并不能轻易找到区分谁对谁错的客观评判标准。孔多塞陪审团定理的另一个理论缺陷是它的初始假设,即所有个体的初始决策判断都是独立和没有相关性的,但考虑到人类效仿他人的倾向性,这也只能是一个理想化的测试假设。事实上,人们的观点更多时候是彼此存在相关性的,而非各自独立。这种相关性形成的原因有很多:专家和其他人可能已就某一既有定式达成了共识(例如认为“地球是平的”),彼此存在身份共识的人可能不需要客观理由就会彼此认同,而我们的思维偏好可能会导致我们无视客观的反面例证而对他人表示认同。
勒庞的心理群体
孔多塞的群体智慧是对复杂人类心理的简化数学分析提炼,它绕开了我们社会生活中重要的心理学驱动因素:个性和情感。趋同型人格的人会更多地跟随团体、群体和群众行动,性情乖戾的人叛逆的倾向性更强。情感也很重要。我们在感到不安时会选择群聚,或在担心做出错误选择而焦虑时会选择随大溜。在音乐会、派对和检阅游行时,我们加入“大部队”以感受喜悦。情感和性格会共同左右我们的选择,性格的特质事先决定了我们的情感导向,而这些情感进而决定了我们更倾向扎堆还是单飞。一个内向而容易焦虑的人可能会在感受到威胁时加入群体,但是他们可不会那么愿意参加一个盛大而热闹的派对。
古斯塔夫·勒庞是研究效仿心理在群体和大众身上的展现方式的先驱者之一。他1895年的著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经久不衰,一直是大众心理学研究的典范。勒庞是一名法国医生,对社会科学范畴的各类学科都有强烈的兴趣,尤其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他对暴众心理学的痴迷源自他对于在特定因素促使下乌合之众形成方式的好奇。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本书中将群体心理和政治运动强烈相关起来,这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不确定性。勒庞生于1841年,当1848年象征着西方民主转折点的重要革命爆发时,勒庞还是个孩子。随着推翻封建旧制、倡导民主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法国二月革命将革命的浪潮推向了其他欧洲国家。成年后,勒庞居住在巴黎,并经历了1871年短暂的巴黎公社革命政府的统治。作为对他亲眼看到的暴行的回应,他对政治起义运动始终持保留态度。在对暴众心理的描述中,他展现了对集体政治行为的一种反乌托邦式的观点,但即便如此,他的心理学著作还是有着很强的政治影响力。荷兰心理学家、前激进主义者兼记者雅普·梵·吉内肯(Jaap van Ginneken)认为,虽然勒庞的观念基本都是借鉴前人,但从西奥多·罗斯福到阿道夫·希特勒,20世纪的政治领袖(无论好坏)都深受其观念的影响。
勒庞曾受到法国社会学家让-加布里埃尔·德·塔尔德(Jean-Gabriel De Tarde)观念的启发。塔尔德认为我们受到有意识及无意识的诱因驱动而彼此效仿。基于塔尔德的这一洞见(效仿对于我们社会互动至关重要),勒庞描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群体,即“有组织的群体”(organised crowds)和“心理群体”(psychological crowds)。一个有组织的群体是随机聚集在某处的一群个体,一群按部就班、并无明显的共同诉求的普通人。有组织的群体规模可以很大,但却是无害的。但是有时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可以转化为勒庞笔下的“心理群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暴众。暴众和有组织的群体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暴众自有一种危险的集体人格,而这种集体人格无法从单个群体成员的角度加以诠释。暴众中的个体都丧失了他们原有的个性和个体身份意识,个体的智力不复存在,因而暴众都展现出一种低于个体水平的低下智力:
构成这个群体的个人不管是谁,他们的生活方式、职业、性格或智力不论是相同还是不同,他们变成了一个群体这个事实,便使他们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这使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若不是形成了一个群体,有些闪念或情感在个人身上根本就不会产生,或不可能变成行动……(在集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 注释标题 Le Bon (1895), pp. 11–12.
暴众的行为是鲁莽的,冲动和本能不受约束。对个体来说,他的“意识人格消失了”,一个一般情况下理智和沉稳的人将变得狂野和不守规矩,也更加容易受到鼓动,仿佛是这个暴动的群体正在对身在其中的个体进行催眠一般。另外一位维多利亚时期描述人群和暴众的著名作家查尔斯·麦基(Charles Mackay)对关于我们如何在群体中丧失理性的表述同勒庞的洞见如出一辙:“众所周知,人总是在人群中思考,也在人群中发疯,而后只能一个个地慢慢恢复理智。”
勒庞对于暴众生动的描述引人入胜,但是关于如何理解和分析集体型从众,他究竟能告诉我们些什么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诲就是,暴众并非个体的简单集合,所以试图用个人层面的动机和激励因素来解释暴众背后的动因是很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实现。
弗洛伊德论归属
如果不是利己心,那么是什么鼓励我们加入某个团体或是一群暴众呢?我们无法利用传统经济学分析的逻辑、具体动机和激励因素来诠释。结群从众能带给我们一种妙不可言的心理满足感。精神分析学的鼻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展出了一些关于我们同他人的关系如何影响我们精神生活的早期理论,包括冲动和本能是如何促使我们结群从众的研究。弗洛伊德的分析集中于潜意识在塑造我们的情感和选择上扮演的角色。在1920年的著作《超越快乐原则》(The Pleasure Principle)中,弗洛伊德认为我们的人格发展受制于我们的生存本能(Eros)和死亡本能(Thanatos)的冲突。如他在1923年的著作《自我与本我》(The Ego and the Id)中所论述的,这些都与我们人格中潜意识的各个层面,即“本我”“自我”“超我”有关。弗洛伊德对于有意识和无意识驱动人们行为的力量的分析显示,人格并非同质性的一个整体,在我们意识表面之下运作的心理能量引导着我们所有的决定,包括我们效仿的选择。在做出利己型从众选择时,也许是最为理性和审慎的“自我”在起主导作用;而在做出集体型从众选择时,也许是更加贴近原始本能、不那么理性的“本我”占了上风。
弗洛伊德将他的部分理论直接应用于对暴众和群体的分析中,显示出了他对于群众运动政治心理学的兴趣。在1921年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和1929年的《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两本书中,他进一步阐释了勒庞的一个论点,即我们在群体中寻求安全的同时也失去了个体的个性。同勒庞对“有组织的群体”及“心理群体”的区分类似,弗洛伊德也将“有组织的、人为的群体”和“普通群体”区分开来,而前者即是勒庞的“心理群体”概念的推演。当人们加入同一个群体时,就更容易受到共同的情绪和本能的影响,并同时失去他们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主观能动性及存在感,即他们对群体的认同掩盖了对自身个体的认同。弗洛伊德接受了英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威尔弗雷德·特罗特(Wilfred Trotter)在其著作中发展的观念,即群聚从众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特罗特认为群聚从众是一种和自我保护、进食和性交类似的原始本能,而弗洛伊德则宣称我们想要属于某个群体的需求源自我们的家庭关系。我们想要加入团体或结群从众的动力都反映了我们归属感的需求,在我们的潜意识里,质疑群体和离群索居一样糟,而离群索居则意味着焦虑。
特罗特观察到,独处会使人感到不安和不完整。在此基础上,弗洛伊德认为这种焦虑感在幼儿时期与之类似的恐惧中就已有表现。根据弗洛伊德的解释,这种对于分离的焦虑以及更广义层面上的社会本能,其根源都是孩子对于父母的依赖。一个刚有了新的弟弟或妹妹的孩子会产生忌妒心,但是孩子随后会意识到,他们的忌妒心会有损他们与父母的关系。因此他们会将忌妒心转化为对新弟妹的亲情。孩子同新弟妹建立一种认同感,以调和忌妒心和对父母的依赖这两种情感间的冲突。弗洛伊德认为,成年人是将这种孩童时代的冲突泛化为我们与其他成人之间的社会情感。我们将自己对他人的敌意转化为更加积极的纽带感。因此也许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忌妒心让我们与竞争对手彼此产生认同感。这也成了群体精神(Gemeingeist或group spirit)的基础。弗洛伊德用一个粉丝行为的例子来对此加以阐明:
我们只需想到这样一群妇女和少女,她们都以痴迷的方式爱着一位歌星或者钢琴演奏家,当他表演结束后她们紧紧围绕着他。她们每个人肯定都容易忌妒其他的人;但是当意识到她们人数是如此之多,不可能得到她们想要的爱时,她们便放弃了这种忌妒心,不是去撕扯彼此的头发,而是联合为一个群体行动,用她们共同的行动对她们崇拜的英雄表示敬意,还有可能高兴地分享他的几丝飘垂的秀发。原先的竞争对手,现在通过对同一对象相似的爱而成功地把自己和他人关联并互相认同起来…… 注释标题 Sigmund Freud (1921), ‘The Herd Instinct’, in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in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Vol. XVIII, London: Vintage,pp. 117–21.
要想确保这些无意识的冲突得以发生,群体从众的所有个体追随者都必须是平等的。对弗洛伊德而言,这又和儿时的经历类似。如果想要确保孩子的忌妒心不过分膨胀,家庭中就不能有任何一个孩子得到过多的偏爱,弗洛伊德甚至认为这是我们对平等理念痴迷的根源所在。
格式塔心理学及心理社会学
弗洛伊德的理论启发了一批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去探寻团体和群体的本质。我们在前文中已强调过,暴众群体本身有自己的人格,这种集体人格与群体中个体的独立人格截然不同。只有首先清楚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集体从众。像经济学家那样,将团体、群体和暴众理解为其中的利己个体决策的简单集和,是行不通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论著《形而上学》中写道:“总体不再如前仅是堆砌,全部也和部分毫无关系。”这一理念在格式塔心理学家库尔特·科夫卡(Kurt Koffka)的论述中也得到了验证:“整体不同于其部件的总和。”这一格式塔心理学的核心原则最初应用于关于视知觉的完形(visual perception)的讨论。当我们看一张图片时,看到的不仅是大量的像素和色点,还能在此之外看到一个(相较于像素及色点)颇为不同的物体的整体图像。视觉假象的工作原理是我们的知觉会随着视角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整体不同于其部件的总和”的观念也和群体现象有关:一个群体就好比是一幅画,而其中的个体就好比是一个个单独的像素,我们仅通过观察其中的个体是无法理解整个群体的。
弗洛伊德的学生、精神分析学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将格式塔心理的原理应用在了一个不那么知名的社会科学范畴——心理社会学中。赖希生于1897年,和古斯塔夫·勒庞一样,对政治运动中的大众心理学——包括20世纪初期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颇感兴趣。赖希期望将政治科学和心理学的理念结合起来,他认为我们性格构成是社会制度和流程的产物。他借鉴了马克思的某些理念,相信精神疾病并不是像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仅和个人的性情有关,而是受到了他所处的家庭及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赖希和勒庞不谋而合,赖希认为社会团队对我们个体会产生影响,团体将我们塑造得超越了独立个体本身,在团体中,驱动我们的是团体的整体目标和欲望,而非其中具体个体的利益。团体和个体在相互影响中演进,反映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张力。团队改变着个体,而个体同时也在改变着团体,琼斯镇的大屠杀事件即显示了这种互动反馈的过程,人民圣殿教也改变了加入其中的信徒个体:每个信徒入教伊始仅是普通的基督教徒,但是入教的这个选择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身份和命运;也许没有那么明显的是,这些教徒也同时改变了教派本身。如果没有办法蛊惑除了其亲信小团体外的其他人,也许人民圣殿教就会被历史轻易地遗忘,但是随着大量的个体教徒加入,并做好了牺牲一切维护教义的准备,这个邪教的本质和身份也随即发生了变化,没有它的广大信徒,人民圣殿教没有任何力量和影响可言。在教派转化信徒的同时,信徒也改变了教派。
赖希的理论和某些经济心理学的分析结论是类似的,例如在现代经济心理学先驱之一乔治·卡托纳(George Katona)的论著中,卡托纳关注我们的诸多个人目标是如何同团体目标产生互动的。团体的力量取决于其成员对该团体的认同感有多强。卡托纳的理论是,这种认同感的强弱决定了个体在群聚从众和社会学习的过程中是如何彼此互动的。个体和团体之间会有相互反馈,随着团体成员之间相互模仿,这实质上也强化了整个团队的凝聚力和一致性。足球球迷即是这种现象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例证,当他们模仿自己的球队和其他同队球迷,例如穿上同样的球衣时,就强化了整个球队俱乐部的凝聚力。球队对自家球迷的依赖可一点不少于球迷对球队的需要。
暴众的身份
如果集体型从众并不是由我们的利己心所驱动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呢?身份是决定团体和集体型从众的力量大小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关于身份的理论存在于众多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可以借助从心理学、社会学及经济分析中获取的例证来对身份进行反思。
如勒庞指出的,我们对身份的理解不应局限于经济学理论允许的范畴。如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说到的,阿克洛夫和克兰顿等经济学家发展出的经济理论,重点关注身份的交易属性,将其描述为一种社会交换。一个理性和利己的个体向某一团体释放信号,证明他与这个团体共享着某种身份,以获得这个团队给予个体的支持。因此在经济学范畴中,身份归根结底取决于个体成本收益计算,即个体加入某一团体能获取的收益。而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理论,身份并不一定关乎利己的个体净收益,将团体捆绑在一起的身份构建和个体的利益关系不大,而是更多关乎团体作为一个整体如何能通过这种身份认同感获取力量。身份决定了我们如何同周围的团体互动,用社会心理学的术语表述,即我们同“内团体”(in-groups)产生认同并倾向于优待后者;反之,我们同“外团体”(out-groups)不会产生认同并倾向于歧视后者。我们面对我们的内团体时会感受到强烈的社会纽带的羁绊,我们会模仿团体内其他成员的行为,甚至不惜通过文身或其他在外人看来会带来肉体痛苦的行为实现模仿的目的。我们同特定团体建立身份认同感的决定也可通过较为良性的方式展现出来,如特定的着装或购买特定种类的物品。我们的消费选择不仅关乎自身满足感的提升,也关乎我们建立身份认同感的尝试。只有确保建立了强有力的身份认同感,团体才会有活力。
是什么驱使我们同某一团体建立身份认同感,而非选择其他团队呢?我们如何决定哪些人属于我们的内团体,哪些人归为外团体?波兰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Henri Tajfel)的研究就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和威廉·赖希一样,泰弗尔的研究受到了法西斯毁灭性力量的启发。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泰弗尔在求学期间被踢出了波兰的大学,在法国完成学业,并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军服役。他随后被德国人俘虏,并在战俘集中营生活了一段时间。战后回到故乡的泰弗尔才知道全家和大部分朋友都在大屠杀期间遇害。这些经历激发他进行深入的思考,种族主义、偏好和歧视是如何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中生根发芽的。他发展出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尝试理解纳粹战犯和非纳粹的普通德国老百姓为何迫害犹太人。为何大部分的德国人都如此轻信并受控于希特勒及纳粹党的号令?为何如此之多的普通人都如此轻易地认同令人发指的暴行?
泰弗尔的研究关注身份的两个维度。第一,他发现我们很容易并很快就能和他人建立认同关系,促使我们选择认同某些团体(而非其他团体)简直易如反掌,甚至都不需要我们与这些团体之间有太多的共通点。这就是泰弗尔的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 group paradigm)的理论基础,帮助我们解释为何能快速和下意识地形成暴众心理。实际上微小的决定能够释放强有力的信号,帮助建立与内团体成员间的忠诚关系。不需要什么激励我们就愿意加入我们认同的团体,即便这个团体建立在一派谎言之上。第二,我们倾向于对外团体进行歧视。与某些团体的亲密和对其他团体的反感滋养了内团体和外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鼓动和激励之下,我们能够模仿身边的其他人对其他团体的歧视性偏好行为。
泰弗尔和他的研究团队发展出一系列开创性的实验,以探究通过离间和建立嫌隙使人变得极端化是多么容易,且这种离间无须有力的支撑即可实现。研究者将64名彼此熟悉的男孩聚在一起,这些孩子都来自英国布里斯托尔的一所寄宿学校,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这些男孩每8人分成一组,在实验第一阶段,每人都看到40组黑点,每组中黑点的数量各不相同,接着所有男孩都被要求猜测看到的每组图中黑点的数量。同时研究者还给这些男孩提供了一些该实验目的的虚假信息。接下来,这些男孩被告知他们将参与另一个完全无关的实验,而这第二个实验的真实目的其实就是了解这些男孩同某一特定团体建立身份认同的难易程度。研究者告诉男孩们,为了省事,他们被分到两个大组中,分组的依据是他们在第一个实验中猜测黑点数量的答案的相似程度:猜多了的男孩分为一组,其他的男孩被分在另一组。而事实上,这些男孩是被随机地分配到了两个大组中。但仅是基于这个无足轻重且虚构的分组标准,男孩们就已经形成了他们的内团体和外团体的观念。
现在男孩间的团体纽带关系已经建立,接下来的实验测试了他们在歧视外团体时展现出来的偏心程度。男孩们被要求将一定的财务奖励和惩罚额度分配给其他男孩,被奖励者或被惩罚者的身份并没有公开,但是能够知道他们是属于“猜多了的男孩组”还是“猜少了的男孩组”,每个进行分配的男孩都不会从分配中获得任何好处,因此这些分配决策不会受男孩们的利己心所驱动。实验结果表明,男孩们持续地偏袒内团体的成员,给属于内团体的男孩的奖励份额总是多于给属于外团体的男孩们。
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定性,泰弗尔及其团队接下来又根据所谓的“对外国画家的喜好倾向”将男孩们进行了分组,更喜欢保罗·克利的为一组,更喜欢瓦西里·康定斯基(虽然孩子们并没有被告知这两位画家的名字)的为另一组,实验的结果和此前的实验基本一致。当孩子们可以选择是给所有人最大收益,还是仅给内团体的成员最大收益时,男孩们倾向于偏袒他们的内团体成员。泰弗尔的实验显示了要想营造一种对团体的忠诚感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即便是建立在看似荒诞的黑点组合或艺术喜好的基础上。至少从利己的角度上,我们看不到明显可以解释为何在如此脆弱的基础上能建立某种亲近感的原因。这强化了勒庞及赖希的理论,即我们必须从团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视角来观察,才能理解群体或暴众的行为。我们不能仅靠观察个体成员的行为来试图理解集体型从众,因为个体成员随时愿意歧视性地对待外团体的成员,虽然这么做对这些成员个体而言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可以说,对集体型从众来说,团队的目标才是至高无上的。
泰弗尔的发现是否适用于更普通的场景,如选择留胡须或者在头上梳一个发髻呢?这些简单的选择对于建立身份认同很有帮助,这个事实本身就和泰弗尔的最简群体范式理论不谋而合。现代嬉皮士就是鲜明的例子。看起来这些嬉皮士不拘一格,事实上他们是在抗拒外团体,并强烈地认同和顺从着某个特定的内团体。他们仅是在模仿一个内团体小圈子中相同的穿着打扮,遵守着(非主流的)准则罢了。带着泰弗尔的发现,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在前一章中介绍的经济学家口中的身份概念。我们在前文中已经看到,经济学家关注高成本的信号,例如痛苦的永久性面部刺青。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如果对自己没有好处,谁会愿意承担巨大的(身体上的、经济和/或金钱上的)代价呢?在身份认同经济学模型中,内团体成员相信,那些承担了肉体上和经济上的代价、花大力气在脸上留下刺青的人是真心实意地重视其团体成员的身份。总之,代价高昂的信息更有经济价值,因为他们的可信度更高。然而,泰弗尔的发现削弱了这一经济学模型的可信度,因为泰弗尔及其同事证实,即便个体不向他们认同的团体释放信号,也可以在个体间建立团体身份认同感。虽然嬉皮士和其他叛逆者希望将自己标榜得与众不同,但要做到这一点不意味着他们必须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以说服他人。更宽泛地说,身份的建立并不一定需要基于鲜明有力的政治或道德说辞。通过装模作样地效仿叛逆者的穿着打扮,其实就可以实现和在脸上刺青差不多的效果。当记者兼博主埃兹拉·克莱因在回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对嬉皮士在音乐节上的行为的评论时,克莱因如是说:
克鲁格曼认为,嬉皮士通过蔑视传统的着装规范,来表达对普通资本主义世界的抗拒。但我认为事实可能正好相反,嬉皮士是在通过对传统着装规范的蔑视,来显示他们对普通资本主义世界的掌控……正如风险投资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写道:“永远不要投资给一个穿着西装的科技创业公司CEO(首席执行官)。” 注释标题 Ezra Klein (2015), ‘On Paul Krugman’s Theory of Hipsters’, Vox, 27 July. http://www.vox.com/2015/7/27/9049025/paul-krugman-hipsters(accessed 7 September 2017).
至少表面上看,嬉皮士可以不花什么代价就向潜在投资者传递一个信息:他们是充满创意的非主流。在商业社会之外,当我们想要加入某些由其他盲从者组成的团体时,我们可以向他人释放信号以证实我们加入该团体实至名归,而这并非难事,我们无须花费任何有形或无形的成本就可以成功加入某一团体。这样,集体型从众行为就可以顺势而起,而其中的任何一个成员甚至都不用费神去仔细思考,他们到底加入了什么团体,又是为何加入。
夜晚的暴徒
身份构建对于团体心理和暴众心理有着怎样的影响?学者及政策制定者都对这个课题有着经久不衰的兴趣。我们的夜间生活常常都和潜在的暴力和反社会团体行为有关。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心理学家马克·莱文(Mark Levine)对于人们在夜间(尤其是酒吧关门打烊后)发生的经济互动行为产生了兴趣。在过去,政策制定者假设,酒吧都同时打烊会带来室外暴力的升级,例如2003年,托尼·布莱尔执政的英国政府就放松了一些许可法令,允许各酒吧每天逐个地关门打烊,以减少同一时点街上不守规矩的醉汉的数量。政府官员们认为,如果许多醉汉同时涌上街头,那么发生暴力事件的概率就会大增。
莱文和他的同事重点关注了一个假设,即夜晚发生的暴力事件常常并不是单个暴徒之间的斗殴,而更多是和内团体同外团体间的冲突有关。挑事的人常常是为了向他们的内团体成员炫耀,或是对外团体成员进行威胁,而这种诉诸暴力的冲动欲望往往在酒精的作用下变得越发强烈。换句话说,这些暴力行为是一种从众的集体之间矛盾的爆发,相互冲突的集体都有各自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无法轻易地在团体个体成员这个层面得到解释,但是在暴力冲突的产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种从众行为是集体性的,而非以利己为导向,任何个体能否从中获得个体层面的收益,与这些暴力冲突的发生并无明显的关系。
为了测试他们的假设,莱文及其同事将目光集中在英格兰西北部的三座城市中,他们邀请了53名受访者,举行了20场聚焦小组的访谈。受访者包括学生、手工作业者及零售工人和几名假释在外的犯人。通过访谈,研究者收集了共计77个受访者作为参与者或旁观者亲身经历的暴力冲突事件,研究者希望获取第一手信息,因此只采纳了亲身经历者的叙述。他们的发现可以说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发生在陌生人之间的暴力冲突比较罕见,反而在同一个内团体的成员之间的斗殴更是司空见惯。一个受访者评论道:“彼此之间太熟悉了……他是你兄弟,而你又喝多了,然后就起了冲突动起手来了。”群体内部的纷争一般被诠释为善意的戏谑行为,很快能得到解决,而一旦解决便被忘诸脑后。
当与外团体的人发生争斗时,情况就严重得多了。团体间的暴力常常是由暴众心理及团体利益所驱动的,与团体内个人的独立行为无关。莱文的受访对象之一描述道:“不是某一个人的事,而是一帮子人的事。”另一个有趣但也许出人意料的发现是,许多的受访者都认为警方干预在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必要的。这些从众聚集而成的团体某种程度都有自我约束的机制,体现了人们强烈地想要帮助受困的他人的社会本能。通常,一场斗殴的旁观者都能在干预和避免暴力升级上起到有效的正向作用。莱文及其同事也注意到,在夜晚外出时,人们会互相照应,看着自己的朋友不让他们喝得过多。因此,尽管暴众和盲流会部分导致暴力升级,但他们也有自我监督和约束的能力。莱文及其同事总结认为,群体可带来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在夜间聚集的群体并非一边倒都是坏的,事实上警方在发生冲突时的介入也许只会扩大暴力和冲突发生的概率,因为此时警方可能只是加入争斗的另一个外团体罢了。
同伴压力
我们已经看到,暴众心理反映了个体和团队之间的互动和反馈关系。身份构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我们认同内团体和排斥外团体的程度解释了不同团体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我们可以轻易地与我们的内团体建立纽带关系,但是否有其他的心理学原因可以解释我们如此轻易顺从的倾向性呢?是什么促使个体选择模仿他人的行为举止,即便这种选择和个人的道德准则或个体利益都不相符?团体需要想方设法强化其行为和准则,以确保成员将团体利益置于个体利益之上。在这个过程中,同伴压力在确保团体、群体和暴众集体的凝聚力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施(Solomon Asch)进行了一系列颇有影响力的开创性实验,以显示同伴压力对团体的作用。和泰弗尔一样,阿施也是犹太裔的波兰社会心理学家,但是阿施全家在大屠杀之前就离开了欧洲,20世纪20年代移民到了纽约。阿施在美国完成了高中和大学的学业,并成了一名杰出的社会心理学学者。到了20世纪30年代,阿施了解到了希特勒对德国民众催眠式的影响力,并猜想纳粹的宣传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它触及了人们潜意识里的恐惧和无知。进而让阿施产生研究兴趣的是,我们在面对社会影响,尤其是在消化包括政治宣传在内的新信息时,是多么容易受影响。阿施曾向同事叙述他儿时的经历,解释他对顺从性这一课题的独特兴趣。在一个逾越节(Passover)的晚上,还是孩子的阿施被允许不像平时那样早早就上床睡觉,他看到祖父单独倒了一杯酒,而阿施的叔叔则解释道,这最后一杯酒是用来敬献给先知以利亚的。信以为真的阿施感觉真的看到那杯子里的酒就这么凭空消失了一部分。在潜意识里,他对来自家庭的集体压力做出了回应,相信了关于先知的迷信说辞,以为先知以利亚真的就从那杯子里抿了一口酒,事实是他的想象力滋养了他服从家族共同信仰的本能。
阿施及其团队为了测试“同伴压力”而设计了一个叫“直线判断测试”(见图3)的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探究人们是否会因为感受到来自身边同伴的(真实或是臆想的)压力而被误导,从而在简单的问题上犯错。阿施的实验之后又被广泛复制和调整,其实最初的实验设计相当简单:研究者找来7~9名男性大学生,将这群人聚在一间教室里,并给每位大学生展示两张卡片,我们姑且称作卡片A和卡片B,其中卡片A上画着一条直线,而卡片B上画着三条长短不等的直线。被测试的学生被要求从卡片B上的三条直线中选出那条长度和卡片A上的直线一样长的线,并且他们需要逐一向所有人公布自己的答案。接着同样的动作被多次重复。
最开始两轮,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正确的(任务本身真的没什么难度)。然后从第三轮开始,场景发生了变化,其中一名学生惊讶地发现,他从卡片B上选出的直线竟和所有学生的选择都不同。他不知道的是,研究者已经事先私下叮嘱了除他外的所有学生,统一给出一个错误的答案。这样一来,这名落单的学生就面临着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其他人的两难选择了。
一名实验对象被要求判断纵向的三条直线中哪条和横向的直线一样长,当所有人都回答是B时,这名被实验对象会如何作答呢?
图3 直线判断测试
阿施及其团队选取了三所不同的高校反复进行这组实验,共计123名学生被置于落单选择的场景下,研究者在实验结束后也会和落单的学生进行沟通,以更多地了解他们是如何应对这种两难场景带来的困惑的。有37%的学生改变了他们的答案,以和其他人的答案保持一致。学生们的反应因人而异,这也表明性格和情感在决定我们是否坚持己见、是否跟随效仿或选择叛逆时起到了关键作用。阿施及其团队根据情感回馈,将受测试的学生大致地分为几个类型:有些学生极为勇敢独立,似乎毫不担心成为落单的少数派,他们对主流观点没有很强的反馈,似乎很容易就能消化和快速适应他人的质疑,并且能够平静地保持信心和坚持自己最初的(也是正确的)判断;其他一些学生在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时,表现出了强烈的不安和困惑;另一群“持异见者”并没有更改他们最初的选择,但还是表现出了作为少数派的焦虑情绪,他们迷惑和不确信,仅是不太情愿地维持了最初的判断;最后,有一群阿施称为“极度易屈从人群”的学生,在大多数人的选择面前选择跟随改变,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在实验结束后的访谈中,这些屈从的学生给出了不同的诠释,有些将他们的错误归咎于其他学生,认为他人软弱盲从的举动误导了他们;有些学生以为这个实验也许是为了用视觉假象的伎俩迷惑他们;一组易于自责的同学将他们最初的(正确但和他人不一致的)答案归结为他们自身的愚蠢错误。阿施及其团队注意到,也许是潜意识的影响在作祟,屈从于多数人观点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低估了他们跟随多数群体并做出错误选择的频率。
对研究者而言,诠释阿施的实验结论并不容易。阿施及其同事观察到的顺从行为可以归因为两类社会影响中的一种。回顾我们在本书序言中论述过的内容,信息性影响指我们因认为他人行为中包含了有用的信息而跟随他人;规范性影响指我们更加隐性和下意识地屈从于同伴压力和社会习俗的需要,不屈服则意味着尴尬、冲突和困惑。顺从和保持一致则容易得多,尤其是当这种顺从可以最小化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可能性时,至少可以带来心理上的慰藉和满足。
所以阿施的实验参与者是在回应信息性影响还是规范性影响呢?他们是否是因为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并因为社会习俗和某些社会心理因素而与集体保持一致?抑或如我们在前一章的利己型从众模型中提到的,实验参与者实际上是在试图观察和学习他人的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希勒(Robert Shiller)教授认为,在简单的问答中跟随他人给出错误答案,这同理性社会学习的理论并不矛盾。从理性的角度看,如果看到很多人都给出了和自己不一致的决定,人们或可弱化自身判断的重要性。如我们在第一章中讨论的,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学生们使用了贝叶斯逻辑推理的原则以平衡获取不同信息。掌握了社会学习工具的利己从众者也许会合理地推断,所有人都犯错而唯独他是正确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希勒援引了阿施实验的一名参与者的表述:“在我看来我似乎是对的,但是我的理智告诉我,我一定是错的,因为我觉得不可能这么多人都是错的,而偏偏我是对的。”尤其当存在不确定性,人们对自己的判断又信心不足时,人们往往会高估他人判断的准确性。
希勒也提到,和阿施的实验类似的结论也存在于人同电脑的人机互动研究中。如果实验参与者的类似行为不仅限于人和人的互动场景中,那么也许这意味着个人社会压力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实验参与者实际上可能是在使用逻辑和推理工具去平衡他们自己的判断和他人的选择。但是万一这些实验参与者把电脑也当作真人一般对待呢?那希勒的解释就变成了一个无法被证伪的假设,我们可以用类似的逻辑将任何行为解释为理性之举,而没有任何实证依据对其加以检验。我们仅根据人机互动的经验,也无法客观地驳斥任何基于潜意识社会心理学动机而做出的心理学解释。也许我们很难想象怎样的实验可以彻底地将经济学诠释因素同心理学诠释因素区分开来,但神经学家给出了更深入的见解,以帮助我们解答眼前这个问题以及其他决策冲突的问题。我们在下一章中会探讨,诸如脑断层扫描等神经学工具将如何为我们所用,以揭开这些难题的谜底。这些工具也能为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信息,以探究盲从者与叛逆者的选择及行为是出于本能及情感,还是由认知及深思熟虑所驱动的,或二者兼而有之?
了解社会习俗
另一种社会心理学范畴的影响因素来自社会习俗。相较于同伴压力,社会习俗的影响力更加多样和持久,黏性更强,更难被改变。此外,即便我们不直接与团体接触,也可以感受到社会习俗的影响力。问题是,如果社会习俗也可以在团体之外产生作用,那这种影响力源自何处呢?答案是它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深层潜意识,也反映了我们儿时所受到的影响。孩子通过观察他人而进行学习,因而他们的行为常常是身边成年人的翻版,这种观察式的学习方法归功于我们根深蒂固的模仿天性。心理学家阿尔波特·班杜拉对这一观点进行了研究,并据此发展出了他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班杜拉专注于探究认知在模仿,尤其是孩子对他人的模仿中扮演的角色。他发现孩子所表现出的侵略性的行为和孩子在早期观察到的成年人的类似行为存在关联。在他的实验中,班杜拉及其团队将一群幼童安顿在一个满是玩具的屋子里,并让他们经历了三个场景:在第一个“侵略性”场景中,与玩耍的幼童们身处一室的还有一个成年人,这个成年人在暴力地摔打玩具;在第二个“非侵略性”场景中,同处一室的成年人安静平和地玩着玩具;在第三个“控制组”场景中,屋子里没有任何成年人。班杜拉及其团队发现经历了第一个“侵略性”场景,有机会观察到成年人的侵略性行为的幼童们更有可能在玩耍时模仿成年人的暴力行为。孩子攻击性的行为和身边成年人的行为如出一辙,这显示了孩子的模仿天性对他们的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将社会压力作为政策工具
我们已经看到,经济诱因、心理学影响均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助长我们效仿和群聚的本能,但是这又如何呢?为什么理解这些能对我们有所帮助呢?它们的功用之一在于,人们容易屈从于同伴压力的倾向性可用作一种政策工具,以中和我们的一些行为给社区或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无论是通过效仿他人进行社会学习还是集体决策,群聚从众都能带来对个人和集体都更优的决策。我们是社会性动物,一般情况下我们支持社会的行为会受到鼓励和褒奖,因此社会习俗对我们行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那些效仿身边伙伴选择和习惯的少男少女更有可能受邀参加最酷的派对。从纯粹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有时我们遵从群体习俗对个人利益是有好处的。社会习俗是建立在他人行为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身边的其他人为我们展示了行为举止的标准。我们将自己的行为和他人的行为做比较,因为他人的行为会为我们提供行为经济学家所谓的“社会比较参照点”(social reference points)。我们将自身的决定同我们认为是团体平均、常规的决定进行比照,这么做也许是因为我们相信如果大部分人就某个决定达成共识,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是正确的;还有可能是因为成为某个团体的一员能强化我们的归属感。
从市场营销人员到政府政策制定者,许多组织都将同伴压力和社会比较参照点当作撬动盲从者顺从天性的工具。一系列的研究,包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针对节能数据分析公司OPower客户的一项大型调研,表明许多人(尽管不是所有人)如果认为他们的能源消耗量超过了他们的朋友和邻居的平均水平,都会倾向于减少他们的能源用量。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发现,如果纳税人被告知他们是极个别迟缴税款的人之一,他们就更有可能缴清欠款。尽管不能算屡试不爽,但类似的群体行为信息经常能起到敦促纳税者遵纪守法的作用。
在低收入国家,人类的这一本性还可以用来改善公共卫生状况。卫生习惯是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人们都能使用公厕,杜绝随地便溺,那么疾病也可以得到控制。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尝试,将同伴舆论对人们既有习惯的影响力作为政策工具,以改善卫生环境,尤其是在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的欠发达农村地区。一个由社会研究员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团队认识到,当社会习俗及传统根深蒂固时,诸如补贴或罚款这样的正向或反向经济刺激政策对改变卫生习惯而言收效甚微。研究员也认为仅仅靠传授相关知识信息不足以改变当地人的行为。为了论证这些观点,研究员在印度的奥里萨邦地区开展了一个实地试验。他们将目标锁定在20个村子的1 050户居民,针对他们实施了一个关于卫生环境、清洁水源和个人卫生的科普宣讲活动。为了证实仅靠普及相关知识并不足以改变固有的行为,研究员在试验中又加入了一层测试场景。他们将科普宣传活动和一个专门设计的环节结合起来,这个环节的目的就是试图直击人们的潜意识本能,撬动人们的社会情绪。他们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社区引导公共卫生计划”中嵌入了一个“耻辱之旅”的环节,社区内的所有居民都一同绕社区走一圈,沿途点出所有卫生状况欠佳的地点。研究团队还绘制了一个“排污地图”,由村民协助识别出污物在村子里的分布情况,计算出污物量并与村民共享和讨论这些信息,同时向村民提供与这些污物的危害相关的信息。
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耻辱或补贴”(shame or subsidy)政策由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多边组织资助,借助心理影响的力量以鼓励人们使用公共卫生设施。这个政策虽然备受争议,但实施效果很好。在某些村子里,公厕使用率从原来的6%上升到了约30%。公开的羞辱激发了人们的社会情绪,而同伴压力则改变了人们根深蒂固的对自己和他人都有害的习惯。这个案例被世界卫生组织当作典范,用来推广基于“社会营销”手段改善人们卫生习惯的政策工具。这里的“社会营销”是指把社会压力和同伴监督作为政策工具的委婉说法。但是这一做法从道德和政策后果的层面来看是值得商榷的。无论初衷多好,政策制定者通过利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其行为进行操纵是否合适?不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至少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还是证明了,我们的盲从本能和易屈从于同伴压力的倾向性都可以被当作有效的工具,用来与包括税收和补贴在内的传统经济政策工具形成互补,共同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这些解决方案的力量不在于抓住我们利己的一面,而是在于利用与我们潜意识社会心理相关的驱动力,包括我们易受身边他人影响的倾向性。
在本章中,我们探讨了许多暴众心理能致使我们行为扭曲的方法,也探讨了这和集体型从众这一概念的关系。在集体型从众中,集体的行为是无法由其中个体的利己动机来解释的。心理学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从众聚集的群体似乎有着自己的意识和目标;为何个体在加入群体后,便会失去自我的意识。
我们效仿他人的行为,是基于逻辑推理和利己的考量,还是受到了某些潜意识的心理本能的驱使去模仿和顺从?关于利己型从众和集体型从众的区别比较,考虑到我们在本章和上一章中讨论过的各式解释,我们对于经济学诠释和社会心理学诠释孰优孰劣有了什么结论吗?是否有其他社会学科能比经济学更好地解释集体行为?是,也不是。相较于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多地关注个性、情感和社会习俗是如何以及为何驱动我们加入各类群体的。他们能够对集体型从众给出诠释,他们也探讨一系列其他更加发散和潜意识的力量。这些影响威力巨大,不仅体现在诸如琼斯镇那样集体性癫狂的极端例子中,也同样体现在更加稀松平常的场景中,我们为了加入某个团体而选择放弃个体自主权,无视我们的个人利益。但是,即便同伴压力、身份构建和团体影响对于理解暴众心理至关重要,我们还是不应该将经济学家的利己型从众模型抛之脑后。在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他人的选择是由更加直观、符合逻辑的动机和激励因素所驱动的。此时,经济目标和激励因素也是重要的推手。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将介绍一些行为学和生物科学的研究,涉及领域涵盖认知神经科学、进化生物学和行为环境学等。这些领域的科学家为我们提供了极好的全新视角,能帮助我们理解盲从者与叛逆者。他们也为我们展示了如何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不同诠释结合起来。一旦我们有了一个更加海纳百川的通用理论,我们将对人类(决策和行为)的动机和驱动力有更广泛的认识,也就可以消除一些传统经济学利己型从众模型和社会科学集体型从众模型间表面的矛盾和冲突。 行为经济学系列(套装共9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