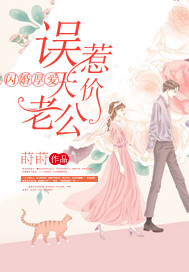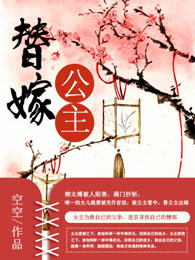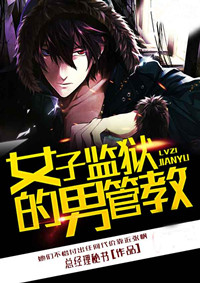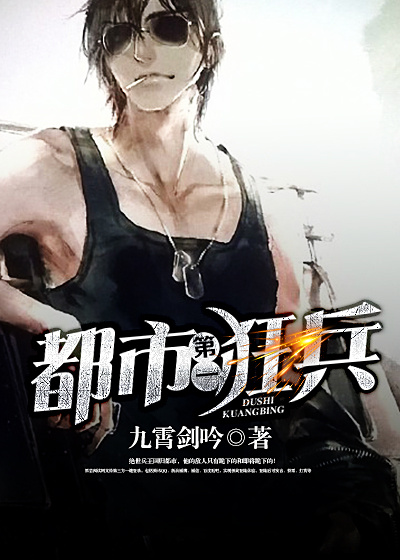九十老翁何所求
您可以在百度里搜索“啸天说诗.周啸天谈艺录 艾草文学(www.321553.xyz)”查找最新章节!
九十老翁何所求 注释标题 本篇作于2013年。
——评李维嘉《冰弦集》
曩读《革命烈士诗钞》至“何当痛饮黄龙府,高筑神州风雨楼”(李大钊)、“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杨超)、“不作寻常床箦死,英雄含笑上刑场”(李少石)、“昨夜洞庭月,今宵汉口风。明朝何处去,豪唱大江东”(熊亨瀚)等,未尝不临文嗟悼。既觉摩罗诗力,移人至深,又憾其人之多才,不得以吟业称也。蜀中李老维嘉,若人之俦也。早年投身革命,有诗云:
少年子弟江湖老,旧梦恩仇肝胆倾。
拼得相思到头白,宝刀不负负柔情。(《少年游》,1948年)
李老曾任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常委,领导《挺进报》工作,是烈士陈然的直接上级。陈然遗诗《我的“自白”书》,新中国成立后选入中小学课本,知名度甚高。《挺进报》一案,重庆地下党遭遇毁灭性打击,李维嘉是幸存者。恰如邓小平所说,在革命生涯中从未受伤,没有被捕,这是一种幸运。(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李老虽不免遭到组织审查,甚至政治迫害,最终结论是清白的。“向使当初身便死”,所作录入烈士诗钞,跻身前引数诗之中,殊无愧色。然而不死,方有《冰弦集》及续编之成——两集共录李老平生诗词四百余首,岂不幸哉!
一个本色诗人,首先须是诗性之人。诗性之人,即读诗、爱诗、懂诗之人。李老正是这样一个人。他上过八年私塾,念过四书、《左传》,也念过《声律启蒙》,对诗词韵对有一些感性认识。一度喜欢新诗,尤喜七月派诗人杜谷,及徐志摩、林徽因、废名等。也写过新诗——“四十年前榛莽里,我曾燃炬夜行吟。”(《重游峨眉山清音阁一线天》)《夜行》就是一首新诗的诗题。在那个年代,写新诗等同“左”倾,容易招致盯梢。只能以唐诗宋词随身,他由此爱上李杜诗、苏辛及二李词,以为精神寄托——“半卷唐诗,三更灯火,话到鸡鸣。”(《柳梢青·酬黄建治、戴万泽》)一次,需要写信通知沪上朋友,出事了,勿再寄信,但不能明言,便以宋词致意:“此后锦书休寄,画楼云雨无凭。”(晏几道《清平乐》)1948年被追捕,临难脱险,离渝赴蓉。流亡道中,成五律一首:
风雨江干路,空山泣杜鹃。劳生惊卅岁,亡命闯千关。愁结无眠夜,鸡鸣欲曙天。雄师何日至?一为挽狂澜。(《亡命途中三十初度》,1948年)
是其处女作。立题有杜意:逃亡途中,三十而立——怎不感喟万端!全诗起承转合,结构谨严,音情顿挫,词旨老当,可谓出手不凡。
他辗转到达崇庆安顺乡,自称川大中文系学生。别人赠他一首词。他不得不回赠一首,好在词牌还熟:
几许春秋忙里度。不解悲秋,不惯伤春暮。月缺花残由你去。掉头我自趋前路。这世风流应已误。遍地哀鸿,几对神仙侣?面对刀丛无反顾。无情正是多情处。(《蝶恋花·答人》,1948年)
此词于流畅之中,寓跌宕之致,写出了革命者义无反顾的取舍。他的诗词就这样排了头,陆续写了十几首,日后辑为“刀丛小诗”——作者自称“战士诗”,此正其可贵之处。唐人边塞之作,即有战士诗。没有战斗经历的人,是写不来的。没有相当的诗歌修养,也是写不来的。“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
改造社会,革命如同外科手术,无疑是迅速而有效的手段。毛泽东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时,又是耗费社会成本最高的手段。有一种牺牲,叫作累及亲情。这亲情,不必是同志情,如“我失骄杨君失柳”者,却一定是鱼水情,是同情过、支持过、掩护过自己,甚至李代桃僵的亲情。在这个题材上,我想不起还有谁的诗词,写到这个份上:
毁家也罢!纵儿女啼饥,慈亲悲诉。柔肠寸断,阿嫂一肩担负。那更分羁燕侣!但放眼、谁家不苦?应惭累你千般,念我天涯何处!回顾。云乡鄂楚。向锦里飘流,强颜歌舞。绮罗金粉,旧梦泪珠难数。寻遍人间道路。望北斗、倾心相许。听取午夜荒鸡,隐隐秣陵鼙鼓。(《双双燕·念嫂》,1949年)
愧我长相累,犹来入梦频。轻财恩义重,多难弟兄亲。见在边荒地,流为刑役人。问家家已破,一恸觉清晨。(《梦兄》,1949年)
《梦兄》题下自注:去年四月兄为我入狱,生死莫卜。滕伟明《读维嘉老〈冰弦集〉》云:“征夫白发晚归来,鸡试牛刀亦快哉。盾鼻新磨扬子墨,箭壶改插杜邻梅。重寻漂母芦花尽,欲报朱家墓木哀。吟罢心潮安得止,挂弓取拨撼天雷。”注:“漂母之恩指其婶、嫂,朱家之义指其兄、友。”专就此种作品立言,是有眼光的。李老于众多诗友的品题中,尤喜滕诗,是有道理的。
新中国成立后,李老先后从事土改和农业领导工作,在“大跃进”中执行一些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做法,后来有了一些省悟,敢于讲真话和抵制浮夸风,曾经受到过错误的批判。但他胸怀宽广,总把个人不公正的遭遇压在心底,不作计较,一旦形势好转,他便欢欣鼓舞地歌唱美好的农村。
焦石人如烤,雨豪酷暑消。山青枯涧活,土润夕阳娇。扶犁风细细,牵蔓影摇摇。翘首长虹现,凌空驾彩桥。(《喜雨》,1961年)
作者心态是阳光的。阳光出现在雨后,正如著名新诗人木斧所言:“浓厚的乡村泥土气息,搅拌着庄稼汉一年辛勤盼望丰收的心情。”(木斧《从〈冰弦集〉说开去》)尤其可喜。
夜合花开正插秧,声声布谷送斜阳。
篱边遥唤催归去,胡豆麦羹扑鼻香。(《夜合花》,1962年)
诗有农村生活实感,从视觉、听觉、嗅觉多个感觉写来,令人如临其境。诗人之心和农民是相通的:“秋江荻岸寻常过,只恐含苞晚稻迟”(《秋江》,1960年)、“打桨送公粮,趁此夜深凉爽。摇漾,摇漾。灯火城关相望”(《如梦令·送公粮》,1961年)、“半湿征衣泥滑路,喜看关水抢犁田”(《雨途徒步口占》,1962年),很难想象,一个不干农活,没有亲自送过公粮的人,写得出如此诗句。不过,那时他写诗不多,一方面因为工作忙,另一方面因为“左”风甚盛,不得不回避则个。多年以后,他写道:
戎州栖息意阑珊。搔首茫茫厨灶寒。
知己莫如重碧酒,微醺还醒独凭栏。(《忆“跃进”年》)
古人论七绝体:须正面不写写旁面,须即事微挑。写到“搔首茫茫厨灶寒”“微醺还醒独凭栏”这份上,足矣。杨析综《鹧鸪天·登岳阳楼》云:“先忧后乐关天下,拍遍栏杆感慨多。”异曲同工。此之谓含蓄。
“文革”时期,李老一度被定为“三反分子”。这一次,他尝到了铁窗滋味。有诗明志:
长驱方纵马,中道阻波澜。门锁千重雾,窗窥万里天。光辉瞻北斗,坦荡咏南冠。后笑心弥静,逆风养浩然。(《南冠吟》,1968年)
李老诗词写作生涯,以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为界,可分前后两期。以上讲的,便是前期。用五个字概括,即“余事作诗人”。三十年间存诗词三十余首,不及平生所作之什一。这有一个大背景:五四运动以来的七八十年中,传统诗词日趋边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诗词一家独大,偶有作者,亦不甚为人所知。改革开放之年,由于思想解放,创作环境宽松,诗人兴会无前,传统诗词写作,才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李老与三五同志乘时而作,搭建平台,创办诗刊,总揽人物,最后使四川成为国内瞩目的诗词重镇。他本人也迎来了创作的丰收,成为全国著名诗人 和四川诗词的领军人物之一。
话要从头说起。早先,李老从别人的扇子上看到一诗,览之,大喜。原来作者是他先前的顶头上司——大名鼎鼎的马识途。从马老处得知,时任四川省副省长的何郝炬亦能诗。省上开会,三人就聚在一起,交流诗作。日积月累,篇什渐多。1980年,邓小平回成都,在金牛宾馆看望一批蜀中画家,即兴讲话说:“四川是个大省,书画家又多,应该建一个书画院。”张爱萍到成都时,得知其事,又在“书画”前面加了一个“诗”字。1984年,原省委书记杨超筹建四川省诗书画院,将诗社之筹建,委之何、马二公。二公即找李老,请其串联诗家。李老先后串联刘传茀、章润瑞、黄稚荃等人,共为《岷峨诗稿》之中坚。李、刘具体做事,办起《岷峨诗稿》——这是国内迄今为止仅有的一本竖排线装、公开发行的传统诗词刊物。李老后期创作,就与这本刊物紧密联系在一起。
《岷峨诗稿》的办刊宗旨和编辑原则,见于第十四辑编后记:“诗歌应为时而作,为事而作。”“诗人永远保持着对时代、对社会问题的高度敏感,对色彩斑斓的社会现象作深沉的洞察与严肃的思考,这是诗人应有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它提出的两不取:“来稿中也有一些趋时应景之作。或赓韵酬答,累牍联篇;或感濡沫而发颂声,或俨华缨而参曲宴;虽雕绘满眼,乃以言人,无采风之义,不在遒人之职。这类篇章,我们不取。至于浮华交会,闻风慕悦,嘘枯吹生,因缘攀附,以行卷为贽敬,比诗歌于商品。这类篇章,我们不取。”(这篇编后记的执笔人为刘君惠教授)李维嘉的诗词写作,就是这种主张的实践。
李维嘉肯定了《岷峨诗稿》某些作品“及时反映时代风云变幻的动向,给予艺术的描绘,敲响了警世的钟声。这足以证明,中华诗词并非夕阳艺术,不是遗老遗少的吟风弄月,不是老有所乐的风雅玩意儿” 。在红珠山,他写下了《怀陈俊卿烈士》。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写下了一批怀念烈士、悼念同志之作。
斜江盟会弟兄亲。腰插短枪不帝秦。仓内慨输千斗粟,座中洋溢五湖春。麻鞋夜袭穿榛莽,茅舍朝藏藉草茵。面缚高呼频报警,霜钟朗朗动峨岷。(《怀萧汝霖烈士》,1992年)
横眉英气仰风华。杯酒纵谈豪士家。耐得祁寒冰入骨,忍听残夜鼠磨牙?电波油墨传春信,灯影鸡窗露晓霞。一掷头颅人往矣,半江凉月漾悲笳。(《怀陈然烈士》,1992年)
毛泽东说:“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想到这些,就令人心里难过。”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然而,无情的事实是——人们正在忘却。在一次烈士纪念会后,一位老同志意味深长地说:“看来烈士也退休了。”这话的一层意思是说,参加纪念会的人大多是退休人员;另一层意思是说,烈士正在淡出人们的记忆。鲁迅有一篇《为了忘却的记念》,而李老的这批诗,构建了一个不占地的纪念馆,又像是一个历史画廊,风格沉郁顿挫,或许可以叫作“为了不忘的纪念”吧。
李老却说:“我没有以诗纪史的自觉,无此宏图大愿。我只是怀念我的一些战友、好友、亲人,特别是一些和我共过患难的烈士。我以诗词写这些人,表达思念之情,带出他们那些感人的事迹,从而在客观上反映了历史的一鳞半爪。”(李维嘉《冰弦集续编》前言)
白发临风,青衫浥露,晚来忧愤难平。问一池波皱,底事干卿?忍赋铜驼荆棘,多少话,欲说谁听!新来病,销愁淡酒,遣闷骚经。铮铮!几根瘦骨,撑一副皮囊,犹自峥嵘。念井冈人去,高树凋零!惟有龙华血裔,应不负、金石前盟。孤吟罢、沉沉夜空,几点寒星。(《凤凰台上忆吹箫·白发吟》,2001年)
元日花灯歌管喧。惊心又是甲申年!闯王遗恨千秋鉴,显宦争搜万选钱。西柏挥师终定鼎,北京赶考未完篇。如椽巨笔拈谁手?怕道生儿不象贤。(《甲申三百六十年祭》,2004年)
《岷峨诗稿》面世十余年后,从中产生了一批佳作,因而在2000年出版了二十六位诗人的选集,总其名曰《岷峨诗丛》。由滕伟明起草的前言中,提出了“岷峨风骨”这一概念,对《岷峨诗稿》十多年的实践,作了准确概括,如实反映。在该刊百期纪念活动前夕,李老接受访谈说:“《岷峨》百期,诗词万首以上,留下了一些可传之作。在思想理念上,形成了‘岷峨风骨’。有两种精神——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意识——忧患意识和平民意识。滕伟明认为岷峨风骨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就是:刚健、质朴、活泼、清新。”这番话虽然是总结集体智慧,在很大程度上,却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反腐而外,如“捕鼠何分猫黑白,行船能不问东西”(《小平同志百龄冥诞》,2004年)、“瞻罢辉煌广安市,清风零雨过仪陇”(《瞻仰小平故里后过朱德故里》,2004年),都是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此之谓“党人情怀” 。
到过李老府上的人都知道,其客厅常设一案,供奉着夫人徐香稚遗像。李老夫妻共同生活近半个世纪,患难与共。夫人亦能铸韵,《岷峨诗稿》刊名,就出自她的提议。亦可谓文章知己。《冰弦集续编》所附夫妻合影,望之如神仙眷侣。集中言情、悼亡、纪梦、遣怀诸作,无不情真意切。不惟“宝刀不负”,并柔情亦不负矣。
寒夜严霜,栅子街深,寂寥少城。正蛰居寄迹,宵行昼伏,同仇聚义,初识娉婷。何处君家?欲归未得,尘海茫茫聊隐形。芸窗静,听喁喁细语,黄叶青灯。一旗突起榛荆。关百丈、铙歌娘子兵。任硝烟障日,血流凝碧,岂甘人后,绿鬓红缨。岁月悠悠,倏将半纪,回首依依难了情。卿和我,庆白头偕老,仍自峥嵘。(《沁园春·赠香稚》,1996年)
紫红茄克旧衣衫。消尽遗香意惘然。惟怜温暖仍如故,此物从来相互穿。(《睹遗物》,2007年)
谚云:“少年夫妇老来伴。”人怕老年丧偶,即怕失伴。有诗纪事:“君知时限至,相对默无言”,“夜半叮咛女,为余早续弦”。(李维嘉《悲诀别》)十多年过去,偶逢老人再婚,他替别人高兴,有诗云:“紫燕穿空独自飞,凄凉心事有谁知?偶遇新交如旧识,香巢重筑共衔泥。”(《贺友人花烛之喜》)但自己却未续弦。大抵“曾经沧海难为水”,同时也为了家庭和谐。他之得免于孤独,端赖有《岷峨诗稿》之存在。
李老是现任的四川省诗词学会会长。早在学会成立(1988)之前,即任《岷峨诗稿》编委,实际操持编务。学会成立后,李老任常务副会长,操持会务。《岷峨诗稿》的班底即成为学会的核心,包括几位热爱传统诗词的老同志,加上诗学造诣颇深的一批专家学者,还有一大批中青年实力派诗人(其中不少是李老物色罗致的)。这三股力量,不同而和,形成了一个优化的组合,使得刊物与学会得以健康成长,避免了走弯路。《岷峨诗稿》百期纪念会上,我作过一首绝句:“一生伯乐二生骅,蔡郭滕杨各作家 ;犹及匆匆归队晚,物其多矣维其嘉!”乃是由衷之言。
李老论诗,首重思想性:“我一生甘苦备尝,爱憎执着,多有感触,激情涌荡纡郁,不吐不快,酝酿反侧,发而为诗,若蓄洪夺闸而出,倾泻尽致,灵魂始得慰藉,精神为之奋发。为时为事而作,以血性和心声为诗,冀补天填海,献一石一木,非附庸风雅,打发闲岁月也。”(李维嘉《冰弦集自序》)同时,强调诗歌本位。《岷峨诗稿》发刊词朴实地写道:“写诗总须是诗,要有诗情、诗境和诗味。”他编诗刊,是认诗不认人的。见到真诗就高兴。曾对张健说:“你和赵洪银两个,是不写‘老干体’的厅级干部。”张健每次说到这件事,都要自嘲道“而已而已——”,意甚得之。李老诗云:
模山范水寄游思,图貌遗神枉费辞。
漫咏千篇行万里,山川不要应酬诗。(《读某些山水诗有感》,1991年)
他不客气指出:“当今写景之作颇多,但佳作甚少,多流于模山范水和一般化。”(《体会隔与不隔》)诗人俏皮地说:人事难免应酬,连山川都得应酬吗?基于如此认识,他本人特别不喜吟风弄月。登览入咏,必是有感而发:
半城湖水迷濛,画船疏雨轻烟里。衰杨几树,败荷数叶,晚秋况味。漱玉凄清,稼轩慷慨,聊斋恢诡。任游情怅惘,览今怀古,收拾起、骚人意。高阁重台雄丽。试登临、风前眼底。围棋一局,指挥若定,陈郎才气。破此金汤,全歼顽虏,义师青史。甚荒唐陷诟,满腔悲愤,至今难已。(《水龙吟·游济南登解放阁》,1986年)
济南战役是华东野战军打的胜仗,为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揭开了序幕。“解放阁”由陈毅题写。登上此阁,联想“文革”中老帅的遭遇,心潮兀自难平,由于作者把自己放了进去,故读之沉痛,非泛泛之作可比。以围棋拟战局,自是妙喻。虽然济南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是粟裕、许世友,但作词不比实录,词中“陈郎”固不必改为“粟郎”(按陈毅有“稳渡长江遣粟郎”之句)。此外,“漱玉凄清,稼轩慷慨,聊斋恢诡”几句,对历下人文的概括,亦可圈可点。
虽居诗坛之上游,李老从不以高明自居。有“大跃进”的痛苦经历,他对居高临下、长官意志、瞎指挥那一套,概不买账。尝著专文,对诸如“诗词走向大众”“实施精品战略”之类颇有来头的口号,一一驳斥:“诗词是有严格的艺术规范的,但不能认为这是诗词的‘缺点’,甚至是‘弊端’,而应认识到这是诗词的特点、优点,但它有自己的局限性。任何严肃的艺术都有严格的艺术规范,如像诗词、戏曲、绘画、芭蕾舞、交响乐等等。它们的严格的艺术规范就表现为它们的艺术美,如像诗词的格律美、芭蕾的脚尖舞。其局限性是,它们并不适宜于大众都来写格律诗和跳脚尖舞。……被格律声韵难倒的人就根本写不出什么诗词精品力作来。”(李维嘉《精品战略杂谈》)可谓一语破的。
诗歌是语言艺术。写诗就是写语言。什么是好的语言?李老认为首先要做到“不隔”。“不隔”与“境界”二说,出自王国维《人间词话》。李老认为:“不隔是基础,境界是升华。”“今天讨论隔与不隔是练基本功。”(李维嘉《体会隔与不隔》)此论颇具新意。其实,诗词语言的隔与不隔,要害在于假借与否。思想是陈腐的,语词是食古不化的,藻绘满眼,了无新意,此即假借。钟嵘谓之“补假”:“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钟嵘《诗品序》)沈德潜则说:“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远。”(沈德潜《说诗晬语》)这两段话,已经讲清了什么是“不隔”和怎样做到不隔。诗语不隔,始能轻松、流畅、有张力,以李老之句为例:“穷忙浑不老,清瘦正宜秋。”(《江行》)“云绕飞车驰绝壁,风吹蹑步过悬桥。”(《访黄荆原始林区》)“艳艳红椒金玉米,檐前屋顶垒成秋。”(《羌寨杂诗》)“想象神犀沉碧海,红衣人在木兰船。”(《犀牛海》)“寒夜忽归来,仍是幼时娇女。留住,留住!无奈月圆人去!”(《如梦令·赠女》)“一角丧师成异域,百年雪耻仗同仇。”(《偕香稚赴港探女》)“林壑犹余劫后身,春风轻抚斧斤痕。看它直干仍千尺,清影萧疏碧入云。”(《负创楠竹》)读者过目成诵,首先好在不隔。李老却说:“至于拙作,病不在隔,而在过实。”(李维嘉《体会隔与不隔》)意思是,有些作品在境界上,还可以提升。这是明白人说明白话。
李老与人切磋,则从善如流。与人为善,好直言奉告。他说:“写诗不要随手拈些现成的词句加以拼装,一定要苦心经营,别出心裁,反复推敲锤炼。”“不要只求过得去,……而应检查不足之处,请高明指正,……诗友间应推心置腹地切磋,不要一味客套恭维。”(李维嘉《接受批评 三改诗稿》)每个诗人都有偏长独至。毛泽东说:“我对五律,从来没有学习过;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毛泽东《给陈毅同志的一封信》)李老擅长的体裁,则是近体——包括律诗、绝句和词体。形成了以悲怆稳健为基调的沉郁不失清新、追琢复能自然的个人风格。早期对古风、歌行,较少染指。后来出于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激愤和口述历史的需要,写下了《恶吏行》《贪狼行》《巴女行》《追星行》《芒溪行》等一批五七言古体的叙事诗。
因为写得比较自由,李老曾自嘲道:“我写的不叫古风,就叫‘今风’吧。”李老之有“今风”,恰如唐人之有“新乐府”。白居易概括“新乐府”的精神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寄唐生》)。又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李老的古体,就继承了这一诗歌传统。毋庸讳言,白居易有的缺点,如“意激而言质”(白居易《与元九书》)、“意太切而理太周”(白居易《和答诗十首序》),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骨鲠在喉,须一吐为快,也就在所不惜了。
唐诗云:“七十老翁何所求!”(王维)李老以九十四岁之高龄,而仍有所求。这不能不让人钦佩。唐诗人普遍享年不高,未及暮年,鲜有变法。今则不然。暮年变法,意味着向更高境界冲刺。杜牧《李贺集序》云:“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意思是李贺继承了楚辞的衣钵,假如他能活得更长一些,变一变法,就有可能超越楚辞、睥睨楚辞。
其实,不必“奴仆命骚”。
日新其德,足矣。 啸天说诗.周啸天谈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