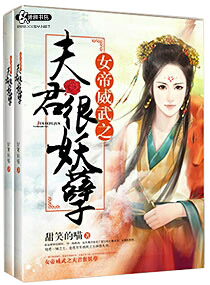第十四章
杨少君去服了两年的兵役。很快他就在部队里结识了新的朋友——睡在他上铺的丁承峰。
丁承峰是广州人,和杨少君同年,因为高考考砸了而被家长送来服兵役,为了以后能容易的获得公务员的身份。因为上下铺的关系,两人互相照应,没多久就混熟了。
有一回部队里放假,十几个要好的兵聚在一起出去大吃一顿。酒足饭饱后,仗着酒劲,有人提议每人说一件过去最不堪的事情。有人说自己曾经偷过老师的内裤;有人说自己曾经在公交车上摸过女人的屁股;杨少君回忆自己前十八年的不堪,最后给出的答案是:“我曾经偷偷跟踪一个女人回家,趁她上厕所的时候从窗户往里丢炮仗;连续一个礼拜半夜三点摁完她家门铃就跑。”
众人哄堂:“那女的谁啊,你跟她有仇啊?”
杨少君摇头:“没有。那女的,现在是我后妈。”
轮到丁承峰的时候,他一口干了半杯二锅头,笑的醉眼迷离:“我高中,暗恋我班主任,”竖起三根手指手指,“三年。”
一片哄然中有人问他:“你班主任比你大多少岁啊?”
丁承峰干完了剩下那杯二锅头,被呛的涕泗横流。他抹掉眼泪擤掉鼻涕,笑呵呵地说:“十三岁吧。”
人们都在起哄或是喝倒彩,只有杨少君若有所思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摁住了他再去开新酒的手。
这出闹剧中,得到起哄声最多的是一个一向腼腆内敛的男人。他喝了三杯酒,突然变得沉静冷酷,在轮到他的时候,他面无表情地说:“我被男人插过屁.眼。”
说完这句话后酒桌大概静默了两三秒,然后爆出的是前所未有巨大的起哄声。每个人都充满好奇或敬畏地看着他,或纯洁或别有所图地问着:“有什么感觉?爽不爽啊?”
那个男人依旧面无表情地用最平淡不过的口吻说:“很痛。也很爽。”
在接下来的酒局里,每一个人都竭力展现自己最豪放的一面,有的为了消除尴尬,有的是真的喝醉了,还有些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别有用心。
晚上一群醉兵勾肩搭背回程的路上,走着走着就少了两个人。
杨少君和丁承峰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并肩站在荒郊一片隐蔽的树丛里了。
一阵凉风吹过,杨少君哆嗦了一下,忽然就回头问道:“你班主任……男的女的?”
丁承峰眯着醉眼看了他半晌,猛地激灵了一下,然后就扑上去开始啃了。
这是杨少君第一次和男人发生关系。就在一个月下无人的树丛里,两个喝醉酒的新手莽撞地用这种方式宣泄。
当丁承峰因为疼痛而惨叫时,杨少君眼前却清晰地突然浮现出一张人脸来。
和苏维很像,只可惜仅仅是像而已。一张总是微微仰着,用冷漠和不屑的表情来看他的,欠揍的脸。
杨少君因为这个想法,在感到罪恶和畏惧的同时,心底又升腾起一股一样快感——如果有一天能骑在那个该死的狗眼看人低的混蛋身上,把他弄得惨叫连连的话……
带着这个新奇的幻想,他只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就成功缴械了。
--------------------------
卢老先生说:“按照你目前的描述,我怀疑他得了卡普格拉妄想症,属于精神分裂症的一种。这个病很罕见啊,我老头子干这行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实例,只从书上看到过,听朋友说过。”他顿了顿,“我只是听你说,没有亲眼看到,也不能对他的情况下结论。”
杨少君试着重复:“卡拉……普格?什么玩意儿?”
卢老先生笑了笑:“卡普格拉妄想症。患者会认为自己的爱人被相貌相同的人冒名顶替了。如果症状更严重的话,他甚至会认为身边所有的人都被人顶替……”
杨少君想到苏黔昨晚的话,心里一沉:完了!看来他真病的不轻了!
卢老先生说:“真是精神分裂症的话就比较麻烦了。他除了怀疑你们的身份之外还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有没有攻击他人的倾向?如果有攻击行为的话,可能还是送到精神病院比较好。”
杨少君脱口而出:“不行!”
卢老先生看着他。
杨少君咬牙用力地说:“他目前还没有攻击行为。老前辈,你能不能开点药给我?”
卢老先生叹气:“年轻人啊,你知道就算是身体生病也不能光吃药不看医生,何况是心理生病了呢?”
杨少君有点烦躁地把手伸进兜里掏烟,拿出烟以后又停下看了眼卢老先生。卢老先生摇摇头,又点点头:“你抽吧。”
杨少君弹出烟点上,一言不发地深深吸了数口,弹掉烟灰,说:“我今天没带他过来,就是怕刺激他。老前辈,你要是有时间,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我带你过去看看他。不过——你最好能不要刺激他。”
卢老先生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什么叫不刺激?”
杨少君说:“关于他的病。”
卢老先生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怕他知道自己的病?”
杨少君又吸了口烟:“你、你不懂他。他这个人,很自以为是,很要强。你跟他说,他也不会信,他只相信他自己。你要是跟他说破了,你会觉得我们在威胁他,然后……反正肯定会更糟糕。”
卢老先生哈哈大笑,挪过去拍他的肩:“你倒是很了解他。做得很对,年轻人,像他这样的情况,现在是最没有安全感的,不能再让他受刺激。放心吧,我是精神分析师,怎么做我比你要清楚啊。”
杨少君把卢老先生带回了苏家别墅。因为昨天的事情,苏黔给自己放了三天假,所以呆在屋子里没出门。杨少君带着卢老先生去找他,敲了门,里面半天没回应,自己试着开,却发现门居然从里面反锁了。杨少君吓了一跳,拼命拍门大喊苏黔的名字,差点就要撞门的时候,门总算被打开了。
苏黔黑着一张脸把门打开,先瞪他一眼,看到旁边的卢老先生时居然受惊地往后跳了一步,用一种很是质疑的目光把卢老先生从头打量到脚:“你是谁?”
卢老先生笑的很和蔼:“苏先生,您好,我是新民日报的主编。我今天是来采访您的,可以抽出两个小时的时间给我吗?”
苏黔眉头直皱,双手抱胸,一副拒人于千里外的姿态:“你有预约?”
卢老先生还是笑眯眯的:“有啊,苏先生,我三个月前就跟您秘书预约过了,她说您今天放假在家,我就来碰碰运气,不知道苏先生肯不肯给个面子啊?”
苏黔根本不记得有这么件事,于是走进房间给秘书打了个电话。在此之前杨少君就给他的秘书传过口讯了,搬出自己的身份来说这是警方的一些安排,秘书不敢多问只能按照他说的做。苏黔挂了电话以后还是有点将信将疑的,不过人都站在这里了,他只好把人放进来。
杨少君和卢老先生一进屋,立刻发现屋子里一团乱,明显有被翻动过的痕迹。苏黔以前是最要求整洁干净的,秘书偶尔理错一份文件的顺序都会差点被他辞掉,杨少君要是拿了什么东西不放回原位也能被他用极有杀伤力的眼神瞪的毛骨悚然,苏黔是绝对不允许别人翻他房间的——很显然,在他们进去之前,苏黔正在房间里乱翻。
事实上,如果杨少君打开抽屉和衣柜看一眼的话,一定会吓一跳——里面的东西被翻得一团乱,几乎所有东西都曾被苏黔拿出来丢到地上,他们敲门之后,苏黔才慌张地把所有东西全都草草塞进去合上。
不一会儿,杨少君又走出房间,替他们掩上门,把空间留给卢老先生和苏黔单独谈谈。
两个小时以后,卢老先生总算从房间里出来了。杨少君掐灭手里的烟迎上去:“怎么样?”连老孟都从从房间里走了出来,很是忧心地看着卢老先生。
卢老先生看了眼桌上的烟灰缸,里面装了七八根烟蒂。他摇头:“不太乐观啊——比我想的情况还要糟糕一点。不好说,我跟他约了时间,明天再来。”
杨少君不知该喜该忧,只能努力往好的方向想:“那他还算是信任你?”
卢老先生笑:“老头子干了几十年的心理辅导,要是连门都进不去,我现在只能出去开导流浪小猫喽!”
把卢老先生送出门,杨少君坚持要他开点能缓解苏黔病情的药给自己。卢老先生很为难:“杨警官啊,精神类药物真的不能乱吃。”
杨少君苦笑:“卢医生,有些情况我没有跟你说——很抱歉有些事情我不得不隐瞒,但他的情况可能比你想的还要糟糕。”他下意识看了眼自己胳膊上的伤。
卢老先生为难地左思右想,只好回家给他拿药,本来拿了半板,想来想去,又割掉四分之一,把剩下的几粒药丸给他,再三叮嘱这个药有镇定效果,不到苏黔发病的时候绝对不能让他乱吃。如果苏黔有什么情况,让他赶紧通知自己。杨少君这才肯放过他。
当天晚上杨少君乖乖滚去客房过夜。
他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苏黔把他从废墟里推出去的画面。有时候他想的暴躁了,从床上跳起来要去找苏黔算账,恨不得能把他骂骂醒,但是自己在房间里毛躁地走了几圈,又乖乖地躺回床上。
他握着手机,想给苏维打电话,却一个号码也按不下去了——当苏黔的病只是隐隐约约露出冰山一角的时候,他恨不得小题大做,能用跟绳索把苏维从异国他乡套回来。可现在真的出了状况,他却不能这么做了。不能,也不愿,更不敢。
最后,他喝了两杯热牛奶,逼迫自己到床上躺尸去了。
凌晨两点左右的时候,客房的门被人轻轻打开,一个黑影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他走到杨少君的床边,在床边默默地站了三四分钟,突然抬手,冰凉的双手扼上杨少君的脖子。
床上的人一动不动。
双手慢慢地收紧,越发清晰地感受到手掌下滚烫的皮肤和蓬勃跳动血脉。那双手开始颤抖,力道越来越松,就在快要离开杨少君脖颈的时候,手的主人突然神经质地一抽搐,又猛地跳上去扼住,狠狠地扼,所有的压抑和仇恨都发泄在此刻。
几秒钟后,那人又弹簧般松开手,跌跌撞撞冲了出去。
黑暗中,杨少君默默睁开眼睛,微不可闻地叹息一声。他坐起身,拉开抽屉,摸到里面的药,犹豫了很久,又把药放回去,重新躺下。
※※※※※※※※※※※※※※※※※※※※
科普一下,很多人搞不清楚精神分裂症和人格分裂症。网上很多时候说一个人批多个马甲是精分的行为,这其实是错误,这种属于人格分裂症。简单地说,人格分裂症很好理解,就是一个人分裂出多种不同的人格,大黄和苏维都是这个情况,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其实和正常人是没有差别的。但是精神分裂症的话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人们说的疯子,他们的心理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揣测他们。
喜欢卡普格拉妄想症候群请大家收藏:(321553.xyz)卡普格拉妄想症候群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