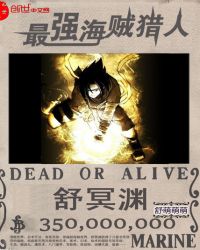回到府内已是入夜, 李庆成吩咐不可走漏了消息, 便将逐风关在边房中,脱得赤条条的,捆住双手双脚,给他喂了点药, 便不再搭理。
“你要怎么处置他。”方青余在房里伺候李庆成。
李庆成身着薄衣短裤, 刚洗澡后换下的单衣有股好闻的日晒气味,混着肌肤上的皂荚气,于这夏夜间十分舒爽。
“熬鹰。”李庆成看着铜镜里的方青余,开口淡淡道,一副惫懒模样。
方青余一怔。
李庆成爬上床趴着, 方青余站了许久, 问道:“你都想起来了?”
李庆成嗯了声,侧枕着看墙壁色。
“想起不少, 你出去罢, 我困了。”李庆成迷迷糊糊道。
方青余:“庆成, 你还喜欢青哥。”
李庆成翻了个身:“喜欢你又怎么, 别催我选, 滚。”
方青余笑道:“好, 不催你选,你想青哥了就在房里叫一声,青哥就在斜对着那屋里。”
李庆成没吭声, 看了一会帐子顶, 慢慢睡了。
翌日起来时, 韩沧海与张慕、方青余的声音在院里传来。
李庆成穿着夏时的薄袍,洗漱后出外,院落分东西二停,一停是李庆成与两名侍卫住的厢房,另一停则辟出柴房,兵器间,外有收拾干净的小小一块演武场。
李庆成以一根木簪挽着头发,站在武场一旁呼吸吐纳,翻掌飞扬,人随掌法而行,步履站位,颇有点雏鹰展翅的架势,腾挪横行,脚步打圈踏出,单掌侧推,收回,一套鹰翼掌打得竟是比张慕教时更潇洒些。
韩沧海背持磐龙棍,正与方青余切磋,此刻三人都停了动作,朝李庆成看来。
李庆成目光专注,始终盯着掌式。
韩沧海笑道:“张慕,你教的?”
张慕怔怔看着李庆成那套掌,正是昔年逃亡郎桓时自己手把手所教的。然而那武功章法却较之张家鹰武带着略微不同。
韩沧海收棍环臂,好正似暇地看着,李庆成掌法一出一收,摒除了鹰武中的狠戾之气,化为蕴天地造化的朗朗苍空之意。
“强身极好。”韩沧海点评道:“杀敌不成。”
李庆成收了掌,笑道:“杀敌不正有小舅么?”
韩沧海欣然点头,抡棍虚点,道:“讨教。”
方青余抽出腰间长剑,抖开一道水似的银光,剑尖斜斜朝地,以示讨教。
韩沧海大喝一声,磐龙棍带着开山裂石之势当头落下!
方青余抽身而退,剑客袍掠起一阵清风,武靴于桩上一踏,云舒剑叮叮叮叮四声轻响,韩沧海抽棍回守,方青余每一剑都点在韩沧海不得不回救的空门,然而韩沧海每一棍都准确无误地收回,点中剑尖!
“好!”黑甲军兵士们已纷纷涌至庭院内。
方青余第一剑客之名无虚,当年带着一把锈剑下山,尚且能挑遍梦泽无敌手,倚仗的本非削铁如泥的云舒,此刻有意在李庆成面前卖弄,更是将剑法发挥到了极致。在韩沧海那密集黑风般的棍阵中穿梭来去,大有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衣的潇洒意境。
韩沧海一声大喝,棍带风雷之声,以腰马之力背驰,觑方青余身在半空之机,惊天动地的一棍横扫出去!
方青余不避不让,持剑在棍端轻轻一点。
叮一声轻响,削铁如泥的宝剑被压上内力,身重,棍威,三重层层巨力涌至,成为一轮闪烁日光,不可直视的银弧。
云舒剑一弹,方青余借力斜掠出去,数步踏上院墙,转身又是一剑!
“好——!”彩声雷动。
那一剑已隐有天人造化之境,万景消湮,众音隐去,韩沧海瞳中只映出一抹如雪剑锋,将磐龙棍一立,横掌扣指,轻响声中妙到毫厘,弹正云舒剑身,一招弹得剑刃偏转了个极度漂亮的角度,紧接着金铁嗡鸣犹若龙吟,一声巨响,云舒剑带着方青余全身内力,擦着磐龙棍斜飞过去!
刹那间满院俱寂,再下一刻无数人疯狂喝彩。
李庆成抹了把汗,他在凝神观战,一旁的张慕却始终看着他。
李庆成眼角余光瞥见,侧头道:“又怎么?”
张慕:“你都记起来了。”
李庆成道:“是,你想我说点什么?”
张慕看着李庆成,缓缓摇了摇头。
那一刻李庆成眼中有种炽烈的意味,仿佛动了情,然而又是一敛,转头望向校场中。
方青余踉跄收步,摇头苦笑,收剑转身朝韩沧海鞠躬。
韩沧海也不谦礼,笑道:“有进境,再学五年,沧海不是你的对手。”
方青余笑道:“谈何容易,今天已是超然物外,比平日好得太多。”
韩沧海侧身,一棍直挥,唰地把棍端指向张慕。
“到你了。”李庆成推了推张慕,笑道。
张慕说:“我不与你打。”
韩沧海收棍而立,沉声道:“不与我打?”
张慕沉默,转身离去。
韩沧海冷冷喝道:“站住!是我要与你打,你与方青余俱是殿下身前侍卫,你身负重责,却连我这一关都过不了,来日该如何自处?我又怎能将庆成放心交给你们守护?!”
张慕背对韩沧海,听见这话,抽出背后无名刀,决然一挥,嚣张指向韩沧海。
韩沧海虽仅三十余岁,却在中原武道中辈分极高,与张慕之父同辈,然素知其性格乖张暴戾,未依足后辈之礼也不怪罪。
张慕发得一声喊,挥刀横削,韩沧海持棍横挡,刀棍互撞,登时一声巨响!
说时迟那时候快,方青余马上以双手食指堵住李庆成耳朵,恍惚间依稀有股音波横扫出去,兵士们纷纷避让,退出院外!
李庆成只觉胸口气血翻涌,险些被这音波震得吐出血来,所幸方青余虎口牢牢贴着他的耳下,内力源源不绝传来,心神才略定了些。
张慕停得一停,抖开无名刀,大开大阖竟是毫无畏惧,狂风暴雨般撞上韩沧海的棍招。
“好!”韩沧海运气爆喝,使出近半狮子吼修为,那一声又震得士兵们两眼发黑。
刀棍互撞,张慕不似方青余以灵动御敌,却使尽全身气劲,以力撞力地横削直砍,韩沧海双足牢牢驻地,巍如山峦,以棍格挡!
每一刀下去,与棍相圻时李庆成都恍惚看见刀棍相撞之处,无形的气劲与音波横扫开去。观战兵士们耳膜剧痛,无法抵御这巨响,尽数退了出去。
院内张慕狂风骤雨般的一通猛攻,韩沧海原地防守,举棍格挡,上百式过去,张慕竟是撼不动韩沧海分毫。直至最后韩沧海猛地挥出磐龙棍,双方同时出招,李庆成看着这无声的比武,骤然听到嗡一声传入耳鼓。
方青余脸色煞白,竟也是颇为吃不消。李庆成拉开方青余手指,听到一阵琐碎的,密集的叮叮响。
韩沧海以天外陨金棍抵住张慕无名刀锋,二人俱是微微喘息。
张慕扬手持刀,手臂脱力不住颤抖,几乎就要拿不住刀,那阵琐碎响声正是手抖时长刀反复磕碰在磐龙棍上。
反观之韩沧海手持磐龙棍,点住张慕咽喉,却不现气力不济。
韩沧海收棍,张慕收刀。
“你心有旁骛。”韩沧海道:“这么下去危险得很。”
张慕的左手发着抖,勉强将刀归于背后刀鞘。
韩沧海又道:“你须得从心魔中走出来,否则杂念逾盛,你对武道的进境便离得越远。习武之人若全凭一己喜好,出刀受仇恨,痛苦所驱策,不但终生难以突破武技巅峰,更有走火入魔之险。”
“你父昔年对你寄托厚望,何以张家独子竟是坠了魔道?言尽于此。”韩沧海说完归棍于背,搭着李庆成的肩膀入厅。
张慕在院中站了一会,回房去了。
李庆成道:“小舅怎么过来了?”
韩沧海道:“来陪你一天,和你说说话。”
李庆成本疑心韩沧海知道了什么事,听亲舅这么说才放下心,笑道:“也想和小舅聊聊了,开早饭罢。”
开饭时方青余在一旁伺候,李庆成道:“慕哥呢,唤他来一处吃。青哥也坐。”
下人来回报道:“张将军在花园角落站着,也不答话。”
李庆成哭笑不得道:“又发愣了。”说毕起身要亲自去寻,韩沧海却道:“由他,他在面壁。”
李庆成笑了起来,见方青余目中有股幸灾乐祸神色,便即笑容一敛,冷冷道:“你也好不到哪去。”
方青余忙赔笑道:“那是,换了青哥与韩将军硬碰硬,只怕三招就得被扫趴下。”
韩沧海无奈莞尔,甥舅二人用过早饭,韩沧海方到书房案前坐定,李庆成在一旁坐着,方青余知他二人有话叙,便出外带上了门。
少顷江州府的兵士将军册捧回府上,韩沧海与李庆成手边各一杯茶,随口闲聊。
李庆成道:“小舅功夫现在是天下第一了吧。”
韩沧海以手指沾了刚毅的唇,拈着书页边角推开,漫不经心道:“当年论武败给张孞,如今故人已去,自然是天下第一了。”
李庆成趴在案上看韩沧海,后者又打趣道:“好汉架不住人多,纵是天下第一,还能单枪匹马杀进京城不成?”
李庆成嗯了声,隐约拧起眉,想到个大胆的念头,不防韩沧海却以指来抹,舒开李庆成的眉头,说:“你这眉毛和你爹像得很。”
李庆成握着韩沧海的手指头,说:“李珙什么时候来玉衡山祭天登基?”
韩沧海道:“快了,就在这几天,怎么?”
李庆成道:“要么咱们带一队兵,小舅你领上张慕和方青余,上玉衡山去把他绑回来?”
韩沧海哭笑不得,随手一弹李庆成脑门,李庆成大声呼痛,韩沧海便撤回被这色迷迷小外甥揪着不放的收。
“谈何容易。”韩沧海解释道:“玉衡山你道天险是白来的?壁立千仞,中空两峭,是为玉衡,两山环抱深远峡谷,足有万丈,咱们在南岭,祭天台在北岭,虽道玉衡山是一线天,然则两峰间距离近千步,除非化为鸟雀,否则怎么过去?咱们就算出兵,也得从江南绕过去,不可能翻山越岭地爬过玉衡山。”
李庆成缓缓点头,要把桥架在两峰之间也不可能了,过桥易守难攻,又有拆桥之险,遂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李庆成又问:“方皇后要来祭天,给你传信了么?”
李庆成打死也不相信方皇后会放弃拉拢韩沧海的打算,果然韩沧海道:“自然传了,一封接一封,陈衡利弊,许以重利,方家除去这些不上道的蝇营狗苟心思,还会说什么?”
李庆成附和道:“是呵,如果以天下大义挟之,万民福祉动之,小舅说不得还会动动心思。”
韩沧海看也不看李庆成,随口答:“那就更假了,一个能将驻边大将派去送死的人,满口天下大义,你觉得可信么?”
李庆成又赞许点头道:“如果方皇后开始不走错了那步棋,不定还万事好商量,那如果方皇后不弄死辽远,再谈天下大义,小舅你会……”
韩沧海不悦道:“有这么多如果?”
李庆成哈哈大笑,只觉与韩沧海在一起说不出的轻松。
韩沧海正色道:“于我,你是亲情;于天下,你是大义。哪来的这许多如果?”
李庆成:“那么如果……罢了,如果亲情与大义难以取舍呢?”
韩沧海道:“以小舅的本事,不会有这种事发生,否则为何习武?人生而在世,读书习武,一展抱负,便是为了守护重要的人,为了不让这两难的境地发生。”
李庆成:“我仅作个假设,小舅,如果庆成是个废物呢。”
韩沧海合上书,想了片刻,而后道:“小舅得知你的消息时,第一个念头便在想,你活下来了,皇天庇佑,可见天命尽在你身。”
“待得有你消息后,小舅又想,有张慕随身保护你,想必不会再有危险了,但你凭籍一己之力,能否杀回京城去?”
李庆成:“若不能呢。”
韩沧海看着李庆成双眼:“那时候该怎么办,怎么出兵,怎么打,小舅都想好了,打算派人先去接你,再集合江州军,出玉衡关,打进京城。自古不堪大任的天子并非没有,天子无能,便需重臣,权臣作辅,诸事平定后小舅将暂且留镇京师,为你甄选朝廷百官,直至一切安定,再为你出征玉璧关,扫除匈奴。直到基业安稳,小舅才卸甲告老,不定要十年。”
“但自闻你在枫关大败匈奴,又辗战西川,不费一兵一卒收服全境。”韩沧海笑道:“小舅就知道,只要从旁协助,为你打下京城,旁的事都不须再操心了。”
李庆成又道:“那如果我是个废物,小舅就不怕被人指指点点,说你挟天子以令群臣么?”
韩沧海随口道:“千秋功过,随人评说。”
二人互相注视良久,俱是会心一笑。
“方皇后那信上具体说的什么?”李庆成想了想,终于找到话题的突破口。
韩沧海不以为然道:“没细看,来使是交给何进的,转手便烧了。”
李庆成眯起眼,含糊道:“何进从前与方家有交情是么?你告诉我的。”
韩沧海瞥了李庆成一眼。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韩沧海如是说。
李庆成没办法了,正在寻思要不要将日前那名唤疾风的驯狼人让韩沧海看看,又怕证据不凿,韩沧海反而难以定夺。
李庆成舔了下嘴唇,万一何进想谋害韩沧海,会用什么方式呢?
韩沧海武功已臻化境,黑甲军又忠心耿耿,何进能使什么招数?李庆成思考间,韩沧海又蘸了口中津液,推开一页书,李庆成朦朦胧胧地察觉了什么。
正在此时,韩沧海头也不抬道:“说到用人,小舅有一事问你。”
李庆成脑中想事,未回过神来,随口道:“哦,今天谢谢小舅了。”
李庆成指的是他与方青余、张慕切磋时说的那话,韩沧海心系外甥,终究不放心,逐一试过两名侍卫武技,听到他与张慕说的那番话时,李庆成心内还是挺感动的。
孰料韩沧海蹙眉道:“你就快当天子了,庆成,人君岂可对臣子说一个‘谢’字?”
李庆成忙自心神一敛,笑道:“小舅说得对。”
多年前亲父李谋也曾经说过,如今韩沧海旧事重提,又道:“小舅知你心内感激张、方二人,毕竟一朝落魄,蒙臣不弃,一路护主乃是大忠,你成全自己的基业,也成全他们的一世忠名,我听你唤‘慕哥’‘青哥’,想必便是因此。”
“但臣子为君尽忠,乃是古往今来的天经地义,他二人是否会恃宠生骄,此不提。来日你登基称帝后,又该如何自处?何尝有常常对臣子说‘谢’的帝君?”
“况且你身系天下,为你做事,便是为百姓做事,尽忠于你便是尽忠于天下,也是尽忠于他们自己,男儿顶天立地,理应为苍生谋福祉,守护天子乃是报效国家,等同于报效天下,成全他们自己。何来谢字之言?!”
李庆成道:“是。”同时想到方青余还在门外听着,不知他尴尬不。
韩沧海又道:“你的基业,是自己挣下来的,本不必如此折节谦卑,退一万步说,就算是能臣送你,恭恭敬敬交到你手中,你也得假装是自己挣来的。否则事事表现得依赖慕哥,青哥,小舅,此例一开,难保来日又有数不清的能臣令你‘仰慕’,如此依恋两个侍卫,看在文武百官眼中,像什么样子?”
韩沧海说到此处,特地加重了语调,李庆成明白了,自己对方青余的依恋,韩沧海只是一瞥便察言观色,心中早知。
他在告诫自己,也在告诫门外的方青余不得恃宠而骄,也不得居功自傲。
“徒惹祸心,不智之至。”韩沧海淡淡道:“这就从小舅的身上,练习点当皇帝的样子罢。”
李庆成冷冷道:“韩爱卿教训得是,朕明白了。”
韩沧海赞许点头,李庆成蓦然又爆出一阵抽风般的大笑,笑得东倒西歪。
韩沧海苦笑摇头,又翻过一页书。
李庆成已把先前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忽又闻书房外有兵士回报。
“殿下,将军,何功曹在江州府上等候,说有要事求见。”
韩沧海道:“传何进过来。”
李庆成暗道不好,疾风还关在府上,万一听见何进声音一声吼,事情便难以善后,忙道:“小舅你去罢,我想去睡会儿,醒了过去寻你。”
韩沧海略一沉吟,便道:“快能整军出发了,你空了到府上来,小舅有一计策,说不定能轻易打下京城。”
李庆成点了点头,韩沧海便起身前去江州府议事。
李庆成在书房内坐了片刻,总觉得先前还有什么事没想明白。越想越乱,只得起身出去走走。
推开书房门,张慕在左,方青余在右,二人守在外头。
张慕已面壁完了,不知何时过来的。
李庆成瞥了二人一眼,盯着方青余,揶揄道:“听见了么?徒惹祸心,不智至极。”
张慕没吭声,方青余却笑道:“臣就是条呼来唤去的狗,绝不敢暗藏祸心,殿下英明,用不着的时候,给臣个痛快就行。”
李庆成摇头好笑,见海东青站在长廊下,若有所思地望着外面毒日头出神,遂道:“儿子,你也有心事?”
海东青咕咕地叫,跳开一步。
李庆成负手于背,跟在海东青身后一跳一跳,沉吟不语。
刚刚和韩沧海谈话时,仿佛是某个动作,令他想到了什么呢?无奈事情实在太多,短短半个时辰内说了太多事,导致他几乎没空遐想。
正跳到走廊尽头,要转身跳回来时,忽有名兵士进来。
“启禀殿下,何进大人命末将前来,将韩将军的军册带过江州府去,点兵有用。”
不说还好,一说时李庆成听到“何进”二字,便即心内一惊,想道那封沾手即死的毒信,又想到军册。
“在这等。”李庆成冷冷道,旋即一阵风般回了书房,用擦笔的宣纸包着手举起书,对着窗外日光端详。
看不出异状,不给又不行,陡令何进起疑。
李庆成哗啦啦翻开书页,找到其中粘连的两页,将那两页边角撕了块,又吹响鹰哨,海东青飞了进来。
李庆成握着海东青的爪子,在书封上刮了数下,选几页抓破些,抖干净,又把它的爪子按在砚台上,抓来抓去,把书弄得乱七八糟。
海东青莫名其妙,也不挣扎,便任由李庆成摆布。
李庆成把纸屑包上收好,带着书出去,说:“去回报何大人,方才没看住鹰,书房内被一阵折腾。破了些。”
那兵士道:“不妨,殿下稍安,末将这就去回报。”
兵士把书取走了,李庆成把纸包收着,犹如怀里揣了一团火,心里怦怦地跳,说不出的害怕。
“江州有你的手下么?”李庆成问:“慕哥?”
张慕沉默不答。
方青余道:“你怀疑何进在书上下毒?”
李庆成眯起眼道:“万一是慢性毒,这些年里小舅说不定已慢慢中毒了……希望我猜错了。”
张慕终于开口道:“让儿子带回汀城去,寻汤婆。”
“太远了。”李庆成摇头道。
此去西川近千里路,一来一回,纵是海东青也得三天,不定顷刻有变,如何是好?
正没主意时,门房忽来报:“启禀殿下,有一女子在门外等候,说是带来了方大人吩咐去配的药。”
喜欢鹰奴请大家收藏:(321553.xyz)鹰奴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