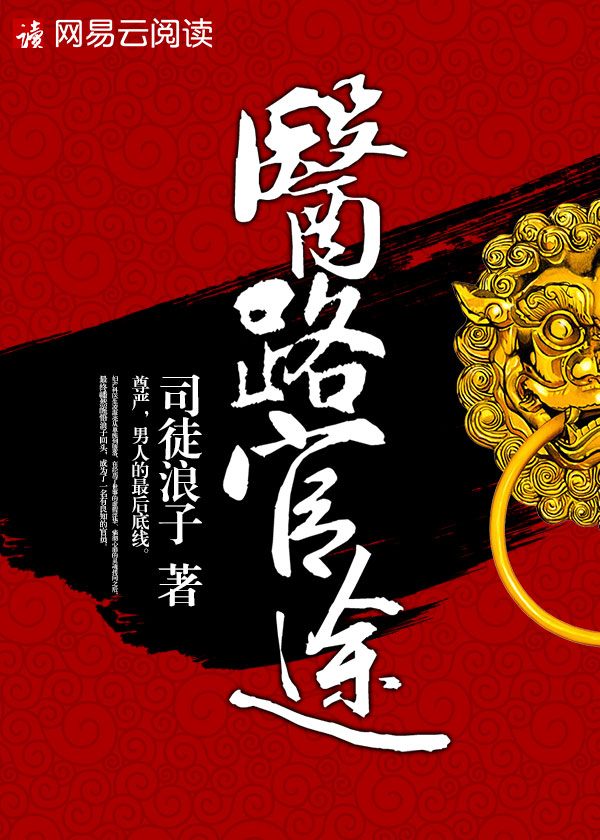到达黄杏儿家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幸好今天我们去换了皮云龙的那辆悍马,不然我们要进到这个地方肯定会非常的困难,因为从镇上到达黄杏儿家这段路程出奇的糟糕。
车子不能直接开到黄杏儿的家,我们将它远远地停靠在机耕道的路边。
机耕道与黄杏儿家相连的是一条窄窄的石板路,我走在最前面,小凌跟在我的后面,他手上拿着我给黄家买的礼物。一箱江南大曲。我知道农村人喜欢喝酒,烈性酒,这是我想了许久后才想到自认为最合适的礼物。
一栋土坯房,房前有一个小小的坝子,坝子前有几棵树,看上去还比较茂盛,在房子的一侧是一笼竹林。可惜房子太破旧了一些,要不然的话这里应该很美的。
我站在坝子里面看着面前的这栋土坯房。它确实太破旧了,我还闻到了一股农村猪圈里面特有的臭味。这种气味我很熟悉,因为我们三江的农村也是这样。这几年我时常下乡,有时候还住在农民的家里,这种气味虽然初次闻着的时候很难受,但是时间一长就会感受到一种乡村的气息。
“有人吗?”小凌在大声地问。
“来了!”我听到从前面房内传出了一个苍老的男声。“你们找谁?”一位瘦瘦的、大约六十岁的男人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是黄杏儿的家吗?”我问道。
他疑惑地看着我:“是啊。请问你是?”
“我是黄杏儿以前的同事,我来看看她。她在家吗?”我问道。
“在、在!”他急忙回答道。
“这是我给你带的一箱白酒。我来得急,也不知道带什么好。”我看着小凌手上的纸箱对他说。
“太客气了。”他的双手互相搓着,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屋内很昏暗。已经是晚上了,但是他家里还没有开灯。灶上的锅里面在冒着热气,灶孔处燃烧着的柴火让我慢慢地看清楚了屋内的一切。
我看到她了,黄杏儿。她穿着碎花布衣服,看上去整个人倒还很干净利索的样子。
“小黄!”我叫了她一声。
她木然地看着我,没有任何的反应。
“你还记得我是谁吗?”我问道。
她歪着头,似乎在紧张地回忆。
我在心里不住地叹息:看来她的病情仍然没有任何的好转。
“她现在好多了,她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呢。”黄杏儿的父亲说。
“为什么不送她去治疗?上次不是有人给了你们钱的吗?”我问道。
黄杏儿的父亲不说话。我见他的脸上很尴尬的样子。
我忽然想起了柳眉曾经对我说过的话来,我的心里有些生气了,问道:“为什么?您可以告诉我吗?我对您直接说了吧,那钱是我给的。我给你们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黄杏儿得到有效的治疗。如果你们觉得钱不够的话我还可以给一部分。”
我直直地看着他,希望他能够回答我。这时候小凌在旁边说了一句:“这是我们凌县长。”
就他的这句话,让黄杏儿父亲的脸上忽然出现了一种恐惧的神色。
本来我觉得小凌说这话正是时候的,但是现在看着黄杏儿父亲的脸色我不禁有些不忍。老百姓怕官,这是一种常情。这种常情就像遗传一样,一代一代地在往下传。在乡村,这种情况尤其明显。
“我……”黄杏儿的父亲欲言又止。
我忽然想起了这屋里少了一个人,问道:“黄杏儿的哥哥呢?”
“这个……县长,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黄杏儿。”他终于说话了,“我把你那钱给我家老大到镇上开食店去了。”
我勃然大怒:“黄杏儿是不是你的女儿?是治疗她的病重要还是你儿子开食店重要?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我看你儿子这个食店开得也不怎么样吧?不然你这家这么还是这样破旧?”
他低着头不敢接我的话,我不再说他了,因为我看见黄杏儿正惊恐地在看着我。
我心里不住叹息。
“把你们村长叫来吧。”我想了想说。
“县长,您别找我们村长。”他慌乱地说,“我想办法还你的钱就是。”
我顿时笑了:“我不是让村长来要你还我的钱,我是想把黄杏儿带走,我要带她到省城去治病。他来了也好作一个见证。”
“县长,您把你工作证给我看看就可以了。您带她去看病,那再好也不过了。”他高兴地说。
我心里很是气愤:给你钱让她看病,结果你却把钱给你儿子去开店。现在我带她走你倒高兴了,她究竟是不是你女儿啊?!
我从身上取出了我的钱包,从里面拿出身份证,再从我另外一个口袋里面取出工作证然后一起递给了他。
“你识字吧?”我问他道。
“认得一些的。”他连连点头。
“那你仔细看吧。”我说。
他在看着,随即将那两样东西交还给了我,说道:“县长,行,您带她走吧。”
我估计他不大认识字,因为他并没有叫出我的姓来。
黄杏儿继续在这里呆下去很可能会遇到危险。我心里想道。我带她走的心思更加地坚决了。“小凌,扶小黄到车上去吧。”我吩咐道。
小凌朝黄杏儿走了过去。但是令我想不到的是,黄杏儿却忽然惊声地大叫了起来:“不要!你不要过来!”
她的双眼充满着惊恐。小凌倒被吓坏了,他连连后退。
我知道这是因为黄杏儿曾经受到的那次惊吓所致。我朝小凌做了一个手势让他离开,我朝她靠了过去。
“小黄,你不认识我啦?我是凌医生啊?凌海亮。你还记得吗?你的凌大哥啊。”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充满柔情与温馨。我知道这很重要。
爱,用爱的声音也许可以将她从混沌中呼唤出来。精神错乱,说到底就是自己将自己隐藏了起来,除了药物,爱的表现以及爱的呼唤也一样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她在看我,神情充满着疑惑。我有些惊喜,轻声地叫她:“黄杏儿……”她仍然在看着我,忽然笑了笑。
我大喜,问道:“你记起我来了吗?”
让我失望的是,她在摇头。
“跟我走,好吗?”我柔声地问道。让我惊喜的是――她点了点头。
我心里充满着温情,过去轻轻地将她扶住。
“今后她治病的钱都由我出。你们不要再去医院接她回来了。”我离开的时候对黄杏儿的父亲说。
悍马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缓缓前行。黄杏儿依偎在我的怀里。她的身体是那么的娇小、可爱。我心中早已升起了一股怜爱之情。
小凌聚精会神地开车,从黄杏儿家里出来后他就没有再问我一句话。这就是优秀驾驶员的素质。
中途找了一个地方吃了晚饭,然后直接前往省精神病医院。
然而,精神病医院却没有急诊,我的想当然犯了错误。我们只好在山上找了一家小旅社住下了。
安顿好了黄杏儿,我走出了小旅社。黄杏儿自从上车后就一直温顺地在我怀里蜷缩着,吃完饭后仍然是这样。我像哄小孩一样地让她进入了睡眠。
我很疲倦,但是却没有一丝的睡眠。疲倦的仅仅是我的肉体。
“凌县长,外面风大。”站在苍茫的夜色中,我听到身后小凌在对我说。
“人生真是难以预料啊。”我感叹道。
“您是好人。”他说。
“我不是。”我摇头道,我知道他不是在给我说家乡的那个笑话,“是我让她承受了这么大的伤害。”
“一定不是在您的预料之中,是不是?”他问。
我摇头叹息,我自顾自地说:“如果有后悔药吃的话,我当初真不该把那件东西交给她。她虽然不是直接因为我而成为了这样,但是我罪不可恕,她现在的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凌县长,您就不要自责了。人这一辈子,谁说得清楚呢?我有一个战友,他为了救一个落水的女学生结果牺牲了。现在那个学生一直都在内疚。因为她当时是想要自杀。凌县长,您说,这样的事情谁能够说得清楚?当时很多人都在讨论我那战友死得值不值得呢。”小凌说。
“这两件事情不一样的。”我叹道。
“凌县长,我这人文化不高,但是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作为一个人,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位黄姑娘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您已经尽心了,尽力了,这就够了。”他说。
我不说话,我在想:我尽心了吗?我尽力了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你回去休息吧。我想独自一个人在这里站一会儿。”我对小凌说。身后即刻传来了他回转的脚步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