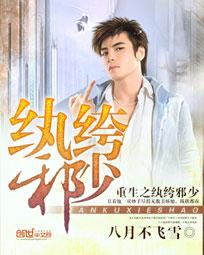北宋,徽宗朝,初夏。
万籁俱寂。
沉睡的郓城县笼罩在银色的月光下。
南街口,一个瘦小的身影拖着疲累的身躯,缓缓前行。
他穿着一件棕色的褂子,这件褂子的颜色本是蓝色的,但因为常年不沾水,他又对它始终如一,不离不弃,就算睡觉都要让它充当被子的角色,它便自然而然成了现在这种颜色。他脚上趿拉着一双露着八个脚趾的布鞋,第九个脚趾随着他每行一步,便调皮地往外露一露头,怕是再过几天,第九个脚趾也就能脱离那老布的束缚,也能够享受上清新的空气了;便是这双布鞋的鞋底,也十有三四早已告别了他的脚底板。
他的脸上蒙着一层厚厚的油腻,浑身散发出数年没洗过澡的异常气味,长长的头发从不需要发簪——他也没有发簪——便很自觉地三五百缕拧结在一起,远远瞧去,就好像大姑娘的花式辫子一般,颇为有趣。
这副尊容行走在南街宽阔的街道上,好在是深夜,街上没人,这条街便任由他来去。其实,即便是大白天,这条街也是任由他来去的。只要他一出现,人们无不远远地掩鼻退让,给他腾出一条宽宽敞敞足以畅行三辆马车的道路,他便在这道路中间晃荡而去,晃荡而来,虽没有人给他铜锣开道,亦没有人用大轿子抬着他,但爱说玩笑话的人总是会发出一些议论,说他行过这条街时的做派,简直让县太老爷都要嫉妒三分。
县太老爷唯一不嫉妒他的,怕只有他的容貌了。
三角眼,八字眉,尖嘴猴腮,似是涂满着黄油的那张脸,其真实颜色谁都没见过。但有人猜测,其本来颜色肯定不如那黄油色,不然他怎么就不舍得把那层油稍稍洗一洗呢?
他在南街上已经行走了一年有余,具体的时间是四百一十二天——这个数字,他并不清楚,是别人掐着指头一天一天背地里算出来的。别人之所以对他如此关心,是因为别人总是在乞求上天,乞求这位爷赶紧离开南街吧!
当然,并非每个人都不喜欢他。拐过南街,有一条死胡同,胡同尽头有一所破败的院子,院子里有一群人,他们还是非常乐意跟他来往的。这群人相互之间并非亲戚,也谈不上朋友,他们之所以聚在这所院子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这个爱好,也是南街的这位大爷唯一的爱好。
骰子。
南街大爷隔三差五总会去那里光顾一次,每次去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出征的将军,身上最少也带着十两银子,多的时候甚至带过三百二十九两去豪赌。但他每次出来的时候,总是一个铜板都带不回来,每一次的模样也总是像极了打了败仗的光杆将军。至于他这些银子的来源,没有人去追究,也没有人舍得去追究,但大家或多或少还是能猜测到一些的,因为那个院子里的人总是会在他光顾这里之前或之后得知一些消息,这些消息无非是谁家“又”失窃了,而窃贼“又”没抓到。
大家虽然总是喜欢将窃贼和南街大爷联想在一起,但又谁都没有证据,便谁都不在南街大爷面前提这件事,故而除了这些视其为财神爷的赌徒,整个郓城县居然没有谁知道南街大爷其实是经常都很富有的一位。
平常人能了解到这位大爷最深层次的东西,便只有他的姓名了。
他姓白,名胜,二十来岁,据说是郓城县安乐村人,至于他为什么不在安乐村当爷,反而跑来南街当爷,就不是南街百姓所能深究到的了。
当然,除了以上那些信息,南街百姓还知道他另外一条信息,这条信息便是他的住所。他就住在南街口的城隍庙中,庙里供着两尊神,一尊是城隍爷,一尊便是这位爷。自打这位爷入住城隍庙以后,大家便把供奉城隍爷的任务全权交托给他了。虽然他自知肩负着供奉城隍爷的任务,但他非但从来没把这位同居者放在眼里过,而且对城隍爷的财产也从来不客气,因为他曾经跟城隍爷说过:“南街大爷认你当个兄弟,你愿意否?”城隍爷没反对,于是他就以为城隍爷同意了,从那以后,城隍爷的财产便是他的财产,他的财产总是变成了赌徒们的囊中物。
自打人们知道他对待城隍爷的态度后,便谁都不同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城隍爷来往了,于是城隍庙便成了独属于白胜的天地,无论任何时候,除了南街大爷,谁都没有再踏入过庙门一步。
白胜晃晃悠悠回到城隍庙,便看见一条野狗卧在他的地盘门口呼呼大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事情。他不能容忍任何有生命的物体与他为邻,因为他总是免不了要在如此夜深的时分,做一些不能让人知觉的事情,比如*,比如开锁,比如挖地道。城隍爷的供桌下有一块能够掀起的石板,掀起这块石板,便有一条地道,这条地道四通八达,有通往员外马家的,有通往富户冯家的,还有通往衙门银库的,只要是有大把现银的地方,这条地道几乎无所不达。
这条地道是只能属于他一个人的秘密,他自然要多加小心,严加保密,禁止任何生物踏入他的地盘。于是那条野狗理所当然被他一脚踹飞,呜咽着给他腾开了门口,窜去了别处睡觉。
白胜推开庙门——他本来想给门上一把锁,但又考虑到城隍庙这种地方,敞着门比上着锁要安全许多,好在街坊都知道这块地盘已经属于了南街大爷,就连城隍爷都惹不起他,便谁都不来此地拜访了——如此稳当安全的一个所在,白胜却万万没有想到,今天居然会有人睡在他的草席子上。
而且睡着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
这两个人平躺而眠,全然没发现真正的庙主人已带着十分的不满走到身边。
但当白胜走到草席子前,看清楚这两个人的容貌时,十分的不满便消去了五分。因为睡在他卧铺上的,是两个女人。
睡在外边的一个约摸四十来岁,衣着朴素,瘦瘦的脸,身材略微走样,但也只是略微而已。岁月的无情虽带走了她的青春,却没有完全带走她的美貌,借着微弱的月光看去,她眼角虽已有了些许鱼尾纹,但那熟睡中徐娘半老的姿态,依然能够让许多中年男子产生兴趣,并甘愿为她付出些力气与本钱。
睡在里边的一个,十八九岁的样子,与半老的徐娘容貌略有些相像,但由于年轻的优势,比之显然要漂亮十倍都不止,想来应该是母女两个。她和她的母亲一样,穿着单薄朴素的衣裤,平躺在草席子上,坚挺的胸脯随着轻缓的呼吸高低起伏,好似春江的波浪,诱人禁不住无限遐想,想要在那上面揉上两把。
白胜不由得伸出手去,想要感受感受那波浪的形状,但眼见着就要触到了,却突然感觉有些异样。下意识停顿了一下,那只手就那么悬在少女的胸脯上方,两只眼微微一低,便瞧见了半老徐娘不知何时已大睁开眼睛,直愣愣瞪着他。
“你干什么?”半老徐娘冷声一喝,白胜慌忙抽回手来,顿觉脸有些发烧。
“滚出去!”半老徐娘极力压低着语调,发出了不容置疑的命令。
“干嘛?”
“滚出去!”
“喂!你搞清楚,这是我的地方!”
“滚!”
“凭什么?我在这儿住了一年了,你让我去哪儿?”
“你滚不滚?”
白胜当然不会出去。大半夜,两个莫名其妙的女人躺在他的席子上,他还没跟她们收住宿钱,其中一个倒让他出去,这是哪门子道理?
“你不滚是吧?”半老徐娘从席子上爬起来,怒视白胜。
白胜以眼神还以她肯定的回应。
她以实际行动报答了白胜的回应。
所谓实际行动,便是扬手一个巴掌狠狠甩在白胜右脸上,紧接着反手又一个巴掌甩在白胜左脸上,然后抬腿一脚,朝白胜裤裆间狠命一磕。
却见白胜抖了两抖,颤了两颤,突然就倒在了地上,浑身一阵抽搐,瞳孔放大,圆睁着眼睛盯着半老徐娘,神色中充满了无法忍受的痛苦。
“你跟老娘装什么蒜!”半老徐娘抬起小脚,在白胜脸上狠狠一踹,却见白胜嘴唇紧咬,牙关紧闭,嘴角间不停地涎出白沫,身体抽搐的幅度更加猛烈了。
见他突如其来的样子,半老徐娘免不得有些慌张,少女此时也已被吵醒,躲在她母亲身后,满面俱是惊慌之色。
但见白胜抽搐得越来越猛烈,脸上的神色越来越痛苦,想要张口喊救命,又感觉到舌根僵硬,已是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月夜,一颗星辰自天际坠落,划着凄美的弧线,坠入了天涯苍茫的山谷。
白胜中风,一命呜呼。
“娘,你打杀了人!”
“小贱皮,你胡说什么?——快、快走!”
罗贯中在白月生后脑上轻轻一拍。
白月生再次恢复了知觉的时候,便听到有两个匆忙的脚步声急促奔远。
睁眼一瞧,恰瞧见门外月色下,两个苗条的身影一晃而逝。
似乎是两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