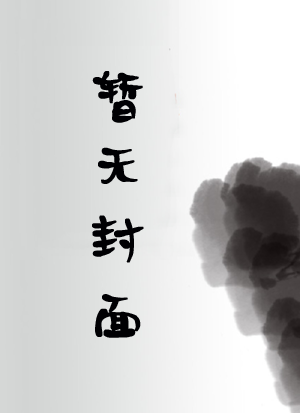好吧,今天是某人的生日,又是世纪大光棍节,暂定三章吧,多了我要疯的。。。。。。
生日快乐!节日快乐!
顺道求票啦!神马都是浮云,唯有票票是最爱啊。
柳桠子是一个镇名,位于南陇县境内的西南角,正式称呼一般叫柳桠镇。
这个名字非常奇怪,因为柳桠子在土话中是指柳树上分叉的树枝。可是,李炀在这里生活了将近十八年,却从未发现过哪怕一株柳树。当然更奇怪的名字也有,比如离这里不远的一个乡,名字叫“包包场”,而十余里外一条荒无人迹的深沟,名字居然叫“陀螺沟”。
这里,就是李炀的家乡。
和对大多数川南的小镇一样,柳桠镇说是一个镇,其实镇子上除了穿镇而过的公路外,就只有一条街道,整体呈丁字形状。论规模,估计连发达地区的村落都赶不上。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河将小镇拦腰截断,全靠一座巨石堆砌的拱桥连接河两岸。
河东是小镇最热闹的去出,不仅有唯一的街道,政府机关、银行、邮局和学校等等全部挤在那边。镇子上唯一一座超过五层的大楼就是镇政府,其余大部分均是两三层的楼房,裸露出红色的砖块来,偶尔也会有青瓦泥墙的低矮房屋夹杂其中。街道去年铺上了水泥,但灰尘依然相当严重,附近的房屋墙面、屋顶上全是厚厚的一层尘土。
随着这几年的改革开放,外出务工与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人赚了钱都喜欢回来修一幢小楼,才渐渐地有了今天的面貌。要是搁五年前,这里都还是大片大片的瓦房呢。
相较而言,河西就要冷清得多。整个河西地面上就只有一家企业,那就是早在去年就已经宣布破产的柳桠丝厂,据说是棉兰市内第一家破产的丝绸企业,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家。棉兰这个号称丝绸之府的千年古城,曾在西汉时期丝绸便因其精美而成为朝廷贡品,在经济市场化的大浪潮中,逐渐失去了她本来的色彩。
柳桠丝厂,这个曾经让无数人引以为豪的名字,这些年却渐渐处于被人遗忘的边缘。
其实柳桠丝厂在多年以前便已经日薄西山,很多有想法有路子的职工都办理了停薪留职,纷纷下海经商去了,剩下的职工也陆陆续续南下务工。因此这个曾经囊括了镇上一大半青壮年的大厂,倒闭时竟然没激起太大的波浪,悄然间,便走完了它近半个世纪的辉煌历程。
只不过厂子虽然倒闭了,但厂房宿舍仍在,据说镇政府曾想将这块土地整体出卖掉,却遭到了丝厂一些怀旧的老职工的坚决反对,只能作罢。或许,对于这些在丝厂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们来说,只要厂房还在,只要大门口柳桠丝厂这块牌子还在,丝厂就永远不会真正倒闭。
不过也多亏了他们,丝厂的宿舍大院才得以保存,李炀回到这里也不至于无处可去。这里是李炀出生并长大的地方,因此这里的一花一树,一草一木,他都再熟悉不过,即便是闭着眼睛也能找到家门。
宿舍大院门口的传达室,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睁开浑浊的双眼,打量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李炀来:“哎呀!是炀娃子回来了啊,可有段时间没见了。听说你到县城读书切了,你娃儿出息了啊!”老年人说土话口音重,喜欢将“去”说成“切”。
“张爷爷,你身体还是那么健旺啊,看起来比去年还要年轻了好多呢!”李炀小时候非常顽皮,常常搅得整个院子鸡飞狗跳,啥时候这么乖巧过。
老头子歪着眼睛看着他的背影嘀咕道:“看来进了县学就是不一样,这娃儿嘴啥时候变得这么甜了,小时候不喊我‘张老头’我就阿弥陀佛了。”
说是宿舍大院,里面其实就一排3层的居民楼,大都建于十几年前,因此显得有些破旧,连墙体都发黑了,上面爬满了爬山虎枯萎后的藤蔓。院子里的住户绝大部分都外出讨生活去了,因此院子里显得有些冷清,只有一些老年人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大部分人都很熟悉,间或也有些面孔很陌生。
李炀和他们打过招呼,径直上了楼。他和刘婧家是邻居,拜托了她奶奶帮忙照看房子,因此家里虽然将近半年都没人住,却一点霉味都没有。
听到响动,刘婧的奶奶走过来看到是他回来了,自然免不了一番惊喜。李炀拿了一袋从县城买回来的水果作为礼物,又解释说刘婧去省里她爸妈那去了,估计要到过年才会回来,让奶奶放心。
李炀的爷爷奶奶走得早,他自打生下来就没见过。小时候刘婧的爷爷奶奶非常喜欢他,经常拿些糖果给李炀吃,因此李炀跟他们并不生分,在他眼里,一直当他们是亲爷爷奶奶来着。去年爷爷去世,李炀哭得比谁都伤心。
李炀还记得她爷爷有糖尿病,可是又实在太喜欢吃糖,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剥一颗糖含在嘴里,躲在一边慢慢地吸吮,幸福地笑。那时候自己年级小不懂事,每次都悄悄地去偷他的糖吃,他也不生气,像捉迷藏一样将放糖果的罐子放在隐蔽的地方,可是每次都会被李炀给找出来。爷爷重男轻女的思想非常严重,他从来不给刘婧糖吃,如果知道刘婧偷拿糖吃,他还会大发雷霆。因此李炀经常偷出糖来,叫上刘婧,两个人躲在楼梯间,开心地分糖吃。
其实爷爷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人。他行医一辈子活人无数,那些年代农村里人穷,经常有人生了重病却买不起药,他就耐心地教他们去山上找草药替代,因此在这十里八乡口碑非常好,很多人都感念他的恩德。还记得他下葬的那天,很多人自发前来送行,这是现在很多医生想都不敢想的待遇。
令人痛惜的是,或许是能医不自医,亦或许是不知道忌口的缘故,他居然倒在了这个他医治好了无数个病例,常常说成是“疥癣之疾”的糖尿病上。
奶奶身体很好,耳聪目明,至今不用带老花镜,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很多年青人都追不上。爷爷死后,奶奶也曾病倒过一段时间,不过终究恢复了过来,只是比以前沉默了许多。李炀记得奶奶一直活到九十八岁才寿终正寝,如此长寿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里是非常少见的,院子里的叔伯婶娘们都说是爷爷当年积下的德报在了奶奶身上呢。
李炀有些惭愧自己竟然一个学期都没有回来看望她老人家,有几次刘婧回来,他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抽不出空。重生之后,早年的那些记忆毕竟淡薄了许多,不再像当年那样鲜活。
无论多么浓烈难以割舍的感情,在时间面前,都将会变得苍白无力。
不过刘婧的大伯一家就住在楼上,平时也会下来照看一二,倒也不用担心奶奶的饮食起居无人照料。院子里老人很多,她也不愁没有聊天的伴儿,并不像大多数空巢老人那样孤独寂寞。此时看见李炀回来,便乐呵呵地回去烧菜,让李炀一会过来吃午饭。
李炀将房间大致整理了一下,毕竟这么长时间没有住人,很多地方都需要打扫,又自己烧了热水洗了一个澡。前些年厂子还没倒闭的时候,哪里用得着在家里烧热水洗澡,煮茧车间里的热水源源不绝,甚至很远的人家都有人过来洗免费的热水澡。
奶奶炒了他喜欢吃的回锅肉,看得李炀直流口水。吃过午饭,李炀正准备下楼去电信局将家里停机的电话开通了,就听到楼下有人在叫他:“炀子!炀子!快下来!”
李炀下楼看见顶着一头乱糟糟长发的张君还在仰着头喊个没完,没好气地吼道:“吗的,说了别叫我炀子了,这名字真tmd难听。”
张君见着他,点了一颗烟含在嘴里吸了一口,才咧嘴一笑:“我听他们说你回来了,还以为是逗我玩的呢,跑来喊喊看是不是真的。”
李炀看着他坦率真诚的笑容,不由得有些感动。他和张君从穿叉叉裤开始就成了兄弟,在院子里一块打玻璃掏鸟窝,在学校里一块打架调戏小女生,是少有地在成家立业后还密切来往的好朋友之一。
初中毕业后,张君没考上南高,就在镇里的高中部就读。实际上,整个柳垭镇每年能考上南高的都不会超过三五人,这可比考大学的难度高多了。以张君这种三流水准的成绩,连考个专科都是一种奢望,自然不可能去南高。他在高中毕业之后就报名参了军,据说当了五六年的班长,眼见提干无望才认命般复员退伍。后来他跟着战友跑去上海包工程,居然没过几年就混的人模狗样,让当初一致认为他这辈子不可能有什么出息的邻居们跌了一地的眼球。
此刻张君身上还看不到那种经过军队锻炼捶打留下的铿锵男儿形象,顶着一头鸡窝似地头发,抄着手斜靠在一棵老槐树上,嘴里还叼着一颗烟,活脱脱一个不良少年。
李炀走过去朝他看了看,轻笑道:“这里是我的家,怎么可能不回来?你小子现在在大院里都敢抽烟了?张叔不打你了?”
“他?”张君撇了撇嘴,毫不在意地说:“要不是看在妈的面上,我才不怕他,打不了对打一场,看谁打得赢些。”
李炀张了张嘴,无声地笑了。
张叔是那种典型的严父类型,奉行“黄金棍下出好人”,小时候张君没少被打。记得最严重的一次,张君在学校里打掉了同学的两颗门牙,结果张叔一怒之下将他捆在一棵柏树上用皮带抽。张君也是一个脾气很倔的人,硬是不说一句求饶的话,要不是邻居们劝着,那次估计不被打死也会被打残。张叔以为打过这样一次,张君应该会老实一段时间了吧。却没想到这小子变本加厉,没过几天,又在学校里将一个女生的辫子“咔嚓”一声给剪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