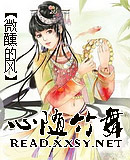第三百五十八章春筵(下)
这场风雪还没停,虽是初春将至,可建康仍旧风雪颇大,北风狂乱,卷起细雪呼呼往车里蹿。
往常建康的初春可没见过这幅鬼样子。
长亭手一放,冰雪就被隔开了。车里与外面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车厢内燃着银霜炭,暖烘烘的,而外面喧杂不堪,哭闹无助的声音交相重叠,听不清他们在细说些什么。
唯一能耳闻的,只有那些声音中相同的,无法忽视的凄凉。
“难民还是入了城。”玉娘抹了把眼睛,眼眶红彤彤的,“这世道到底什么时候算个头,外头的人吃不饱穿不暖,老子卖儿子,儿子吃老子。宫里头还发帖请筵,大鱼大肉…”
今日春筵是庾皇后一早便定下来的。
大腹便便的谢之容与年纪小小的陆长宁都被留在了陆家宅邸,胡同外有内城巡卫司把守,内有陆家死士三百,只为护府中三个女人周全。
长亭本也不欲带玉娘出来,可若她连玉娘也不带,以谢之容的聪明,多半会立刻猜到形势有变。
猜到而什么也不能做,这种感觉最让人痛恨。
玉娘仍在低声嘟囔,喋喋不休的样子让长亭不由自主笑起来,笑着笑着,长亭轻轻叹了一口气。
现今除却长亭、张黎还有始作俑者,整个建康里再没有人知道石阔已经战死邕州。
包括皇城中的石猛与庾氏。
石阔身亡,此事在陆长英与蒙拓预期之外,故而此刻两人皆在城外无法回城。
谁也不曾想过,岳番会反,石闵有这个胆量在这个时候冒天下之大不韪用这么敏感的方式去激怒他的父亲。在经历陆家一门的惨事后,石猛对骨肉相残看得非常重。争,可以。人生来就什么也没有,一粟一粒全靠你拼我夺,但是别越底线——而同胞兄弟之间不能见血,这就是石猛的底线。
要不是石闵疯了,要不是岳番疯了,要不,这两个人都疯了。
玉娘见长亭面色不善,伸手帮长亭挽了碎发,“你怎么了?”
长亭笑着摇头,“无事,前日给蒙拓写了一封家书,也不知他收到没有。”
家书里写着石阔身亡的消息。
蒙拓早一天知道,局势就少一天被动。
玉娘“啧”一声,神情暧昧。
长亭也笑起来,推了玉娘一把,漫不经心道,“过会儿,我就把你放在王朗家了啊,王太夫人也要去宫里,你自个儿去找王家姑娘耍。”
玉娘不在意地“嗯嗯啊啊”几声。
到王家胡同口,知王太夫人一早便进宫去了,是王家大姑娘来迎的,热情极了,挽着玉娘手一口一个“胡姐姐”,又同长亭意有所指地说,“蒙夫人也别不放心了,我虽是未来小姑子,可也不恶,还能吃了胡姐姐呀?王家虽不才,可好歹武将出身,会拳脚的护院也是有几个的。”
长亭再看王家门口亦是严阵以待的架势,便抿唇笑起来,照王家这样对局势的敏感程度,若是躲过这一劫后,他们家都发达不起来,那她陆长亭就把名字倒过来写。
长亭送完玉娘,孤身一人上战场。
车厢里暖和极了,白春扶长亭上车,低呼一声,“夫人,您指尖这样凉!”
这样凉?
长亭手扶在车框上,不以为然。只可惜当初寒冬腊月在冰河里泡着的时候,天寒地冻在雪地里跪着走路的时候,迎着北风躲在山洞的时候,她的指尖,她的心比现在还凉还冷,她比现在还要害怕!
只是当时没有人在旁边握住她手,知道她冷罢了。
爷们在城外还不知道是个什么情景,她决不能在内城拖后腿。
长亭摸摸白春的头,这姑娘什么也不知道,镜园里的人,长亭一个也没说,长亭手在车门框上停了一停,随后便低头上了马车。
去甘泉宫是畅通无阻的,下了马车换小撵,石家称帝也有些时日了,仍旧没有换掉宫内装饰和前朝宫人,许是宫里开筵的缘故,这一路看到的来来往往的宫人比之前几次加起来还多,小撵开的窗有些大,一路过来有许多老宫人对着小撵磕头叩首,颤颤巍巍地唤一声,“大姑娘长安”。
都是旧朝的老宫人,还是唤着长亭“大姑娘”。
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长亭抬头看天,阴沉沉的,风卷残云般叫人只好沉默着顺从地随着这天气无端落寞。
甘泉宫已聚集了些人,外头的天空灰呼呼的,里面却灯火通明,庾皇后就坐在正上方,穿着一身极艳丽的牡丹百花开绣金丝襦裙再套了件正红的褂子,身边坐着石宣和庾家五姑娘,庾五娘比之前长大了些,面容长开了,怀里抱了一只雪白雪白的小猫儿,正很温顺地躺在她的胳膊弯里,庾五娘和她姑母有五分的形似,三分的神似,是个看上去让人很舒服的姑娘。
庾皇后身边还围坐了几个石猛的妾室,位份都不高,最高的才封到才人,这是很给庾皇后这个发妻颜面的行为。
坐在左侧第一个的便是崔氏,右侧是王太夫人,挨个儿下去便是如今建康城中数得上名号的夫人太太们。
长亭算是来得晚的。长亭一露面,庾皇后便笑得慈和,招手让长亭过去,“阿娇快过来。”看了看长亭身后,又笑,“我就猜你嫂嫂不来,却也没想到玉娘那孩子也没来...你嫂嫂身子可还好?”
庾皇后神色未见半分异样,甘泉宫中花团锦簇,很富贵。
宫里还没有人知道石阔身亡的消息。
长亭心中暗忖,一边面上笑着同在座的颔首一边亲亲热热地坐到了庾皇后身边去,拉着庾五姑娘的手,“嫂嫂身子骨挺好的,大夫说明年三月就生,素日里羊乳燕窝也都吃着。”长亭仿若突然想起似的,朝崔氏俏声道谢,“说起燕窝,当真谢谢大嫂娘家送来的燕窝了,嫂嫂吃得很好。”
崔氏不着痕迹地打量长亭神色,见长亭神采奕奕,一身鹅黄绣双面兰花高腰襦裙再配了匹白绒绒的貂毛披肩,髻上选的也是指甲盖大小的黄澄澄的宝石来配,看着模样就是细心挑过的。
当一个女人还有心思挑服饰佩饰的时候,便证明还没有什么大事儿发生。
隔了半晌,崔氏方笑称,“一点小东西也当得起你一声谢!”
王太夫人也在旁笑言,“皇后的几位儿媳妇儿都是顶好的,一个婉和一个娇俏,等二皇子凯旋回了建康娶了亲,那可当真是团团圆圆了!”
王太夫人说着,庾五姑娘红了脸。
庾皇后哈哈笑起来,把庾五姑娘往身边搂了一搂,“小娘子家家的,庚帖才刚过,你可不许胡闹我们家姑娘!”
再有夫人在下头含笑附和,“瞧瞧咱们皇后,媳妇儿都还没过门呢!这就护上了!”
崔氏便笑道,“庾五姑娘既是儿媳,又是侄女,这论关系,怎么着皇后娘娘也得护严实了可不能叫咱们这群姐姐欺负了去!”
庾皇后笑得很自在,脆生嗔崔氏,“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叫你们跟这儿说!老大媳妇儿这是在暗里怨怪我偏心自家侄女儿呢!这点子小心眼,快给你们王妃上一壶杏仁豆腐来堵住她嘴!”
“罢了罢了!晚烟,记得来三盏!我一盏,五妹妹一盏,蒙夫人一盏!皇后娘娘就是再偏心五妹妹,我也不醋,大儿媳妇就是得忍得了苦,吃得了亏。”崔氏故作哀伤,揪着帕子抹了把眼角,庾皇后连声笑道,“该打!该打!”惹得堂内夫人太太们笑呵呵的一片。
晚烟含笑应声退下,长亭使了眼色,白春从隔间跟着晚烟向外缩。
满堂宴宴,端的是宾主尽欢的样子,堂内越热闹,长亭一颗心“咚咚咚”越是跳个不停。
毁灭前的狂欢。
长亭兀然想起来这六个字,长亭眼神一一扫过,无论是娇嗔卖乖的崔氏,还是自在欢悦的庾皇后,还是那些跟着石家打打杀杀几十年的将领的夫人太太们,这会儿都是沉默前的狂欢。
她们都是聪明人,都很敏锐,每个人都应当知道随后就是一场硬仗。
虎视眈眈的胡人,与胡人勾结在一起的符稽,一心称帝的石闵,还有她们不知道已经死了的石阔。
战争,一触即发。
这一点,她们不可能不知道。
至少...
长亭认真看向崔氏,崔氏正极其恭顺地捧着一盏杏仁豆腐侍奉庾皇后。婆母慈祥,儿媳孝顺,好一副母慈子孝图。可一旦拿锋利的匕首将这幅图划烂,露出来的便是充斥着血腥味的败絮。八年的陆家是这样,如今的石家也是这样。
外患尚在,内瓤已烂。
没有谁是真正靠得住的。
城外的难民还在,土地中庶民们干涸的鲜血还在,建康城从姓符改成了姓石,可这帝王座椅下面仍然是腐臭的,万里河山仍旧千疮百孔的。国仍然不泰,民依旧难安。
长亭紧紧攥住拳头,别过眼去,如果是石阔,她能够心安,如果是十年前的风华仍在的石猛,她也能够心安,可为什么偏偏是石闵!
为什么偏偏是石闵!
为什么偏偏又是用这样的方式!
“留芳台子已经搭好了,皇后娘娘与诸位夫人娘子可预备着启行了。”晚烟声音温婉如常,长亭抬头细看却见其手拢袖中指尖微微颤抖,长亭回头再看白春已经回来了。长亭侧身轻声问白春,“可已与她说好?”
白春敛眉低首,轻轻点头,有些担心道,“夫人不怕这事儿有假?万一是假的,咱们岂不是唯恐天下不乱?皇后必定觉得咱们居心叵测...”
白春给晚烟说的是,今日石闵要反。
白春并不知道石阔已亡,晚烟和皇后也不知道,她们都不需要知道,皇后和石猛一旦知道,反倒会因情感而坏事。
“假的就假的啊。”典狱司典狱司点
众人已起了身,三三两两地向留春台去,长亭搭着白春的手起身,侧耳轻声道,“假的岂不更好?若是假的,就当咱们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可若是真的,现在提前告诉皇后和君上,到时候也不至于落得个被动挨打的境地。”
白春有点看不懂了。
正巧王太夫人走过来,长亭便于之相邀一道出去,长亭止住话头,看了眼正被晚烟细心搀扶的庾皇后,心头一叹,如今形势严峻,蒙拓与陆长英是否知晓此事尚无定论,一旦石闵今日发难,她陆长亭除了张黎手下的巡备司,一点底牌都没有,如今能拉拢一个便算一个。之前她不会也不敢向宫里递话,一来怕风吹草动让崔氏警觉,二来...
毕竟石闵是石猛与庾氏的亲儿子啊!
石阔一死,石猛只有倚重这个骁勇善战的成年长子了!
这种情况下,谁又能精准地预测到石猛与庾氏的反应,万一他们认为石闵掌不住蒙拓,为保石家江山,反倒要为自己那驽钝的长子清障铺路怎么办?到时候腹背受敌,长亭不认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活着和蒙拓再见面。
王太夫人笑着攥了攥长亭的手,老人家很慈祥,“玉娘如今在我们家,你放心。”
长亭也笑,“我有什么不放心的,玉娘往后可是要住在太夫人家里头的,与您是一家人,王家我都不放心,我还真不知道哪儿能放心了。”
王太夫人笑着再拍拍长亭手背,“王家虽门楣不显,可托战乱的福,对要死人的事都是嗅得到味的。”
长亭抬头慢慢笑起来,再轻轻点头。
留春台搭好了,随时准备开唱,女眷点了几出戏,庾皇后又添了几折戏,要不是阖家团圆的戏码,要不是才子佳人的话本,长亭正坐于庾皇后右侧,崔氏落座其右侧,石宣小姑娘在后面叽叽喳喳的,庾皇后偏头睨其,石宣当即安安分分,只剩下两只眼睛骨碌碌地左右转。
长亭细看庾皇后神色,并未查见任何异常。
长亭默不作声地别过脸去,认真看台上正咿咿呀呀唱着的戏。
毕竟过会子,台下的戏怕是也要上演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