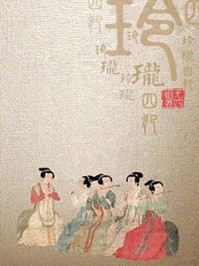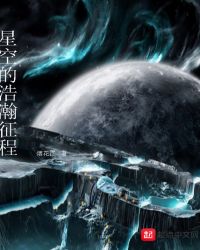第 64 章
云畔迟疑了下, 大概因为夜深了的缘故,脑子也有些不灵便, 她甚至认真思忖了一遍, 耿方直说过些什么话。
见她茫然,他叹了口气,“他说一辈子只有惠存一个女人, 再不纳妾了。”
“哦……”她嘴上曼应着, 忽然一怔,“你说什么?”
不敢相信么?也许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来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但在他自己看来却没有什么稀奇。
十七八岁青春萌动的年纪就对美色不感兴趣, 年纪渐长后定了亲, 愈发能够沉淀下内心。官家独子夭折后, 上京充斥着看不见的暗涌, 他有太多事要做, 更加没有闲心去物色女人。他是个怕麻烦的人,娶了一位处处可心的夫人,自己便花力气去维护这份感情, 不想因任何不愉快, 浪费了之前的努力。
他很现实, 做什么都要见到成效, 对待感情也一样, 不在没有价值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是他的宗旨,换言之, 能令他倾尽所有的, 必是唯一最好的那个人。诚然, 后嗣对于他来说很重要,万分重要, 但自己的夫人也能生,为什么偏要去和别的女人纠缠,耗费自己的精神?
他抬起手,轻轻触了下她的脸颊,“不要因那种不必要的事难过。”
他都看出来了,是因为自己这两日太过失态了么?
云畔嗫嚅了下,“可是祖母的意思,公爷听不出来么?”
“祖母不该管我房里的事。”他淡声道,“我要谁,自己心里有数,并不是随意塞两个女人在床上,就能成事的。”
“可是……可是……”她泫然说,“公爷需要孩子……”
“是嫡子。”他更正了一遍,“不是嫡子,生再多也没有用。况且过去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大哥和三哥相继成婚,相继有了孩子,我孑然一身,也并未落下乘。如今时局,韬光养晦方能明哲保身,我甚至觉得咱们暂且不要怀上,不去凑这个热闹,对我更好。所以你无需着急,更不要因此烦恼,长辈跟前尽可能地敷衍,敷衍不过去了自有我来应付……”他微微弓起身子,仔细看她掩在暗处的脸,“这两日你那么不高兴,我都瞧在眼里了,你以为能瞒过我?”
他说完这番话,她半晌没有言语,过了会儿委屈地伸手揽住他,闷在他胸前说:“我小家子气了,想了好多,不知道怎样才是对你最好的。”
“只想着对我好,没有想过怎样才能让自己欢喜么?”他抱住她,轻抚她的脊背,望着昏暗的帐中世界说,“有时候人就该自私些,不要总想着成全别人,你成全了别人,谁来成全你?我若是想要孩子,多少生不得,何必等到这时候。你拿耿方直的话来试探我,以为我听不出来,今夜我要是不和你开诚布公,你明日打算怎么对我?”
他真是什么都看透了,云畔忽然觉得在他跟前,自己是个藏不住秘密的人。至于会怎么对他……她嘟囔着:“我打算挑几个顺眼的女使,让你从中挑选。”
他嗤笑了声,低沉的嗓音,在这小小的一方空间里格外诱惑,“我要女使做什么?我只要你。”
这话勾起了她的酸楚,她呜咽了声,像得到垂怜的小兽,使劲在他怀里蹭了蹭。半晌才仰起脸来,抓紧他绢衣的衣襟楚楚说:“我暂且不用把你分给别人了,对不对?你不知道,我一想起要送你到别人屋子里过夜……”
他的唇角勾出好看的弧度,“便怎么样呢?”
云畔吸了吸鼻子,“便……心都碎了。”
他愈发要笑话她了,“我不去别人那里过夜,每夜都在你身边。”
嘴里简单地说着,心里却满含欢喜,他的小妻子眷恋着他,只有感情深浓,才会那样纠结,如果不喜欢,不爱,大可以随手让给他人。她不是那种想起什么便会口无遮拦说出来的人,且要在心里翻滚上很多遍,若是他不去戳破,她就佯装天下太平,时候一长,夫妻就离心离德了。所以就要他来警醒,对她足够关心,他并不觉得这样会令自己乏累,反倒乐在其中。毕竟若是应付妻子你都心不在焉,那么这场婚姻便真的没有任何意义了。
云畔到了这时候方觉心满意足,她轻轻嗯了声,“要是什么时候必要纳妾了,我希望公爷亲口告诉我,不要借着祖母和母亲之口让我知道。”
他说好,“若是哪天我不得不纳妾,一定亲口告诉你。但我一日不说,你一日就可泰然处之,不要整日疑心,不要听见别人有了身孕,生了孩子,就心神不宁如坐针毡。”他在她鼻尖刮了一下,“人一旦慌张,就不好看了,记住了么?”
是啊,整日提心吊胆,忧心丈夫纳妾而愁容满面,长此以往真会变得越来越丑。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思忖了半晌问他:“可是另两位公爷都纳妾了,你果真不想吗?”
他也作势忖了忖,“咱们成婚第二日进宫谢恩,太后的话你还记得么?夫人天资聪颖,知道她只想互相制衡,若是枕边换了个愚钝的,品不出里头深意,果真把我的一举一动都呈报禁中,那我还筹谋什么,哪一日大祸临头都未可知。”
这番话有理有据,并不仅仅出于夫妻间的浓情蜜意。云畔的心也踏实下来,知道他并不为难,是真的没有纳妾的打算。
感谢他,给了她足够的底气,一夜甜睡,第二日起来精神很好,送他上朝后便去茂园回禀今日的行程。
惠存也忙说要跟着一道去铺子瞧瞧,“我错过了开张的吉日,今天陪阿嫂过去。昨日一路上总听说晴窗记,女眷们如今是拿那儿当成宴客的场所了,到底上京没有专为女客开辟的铺子,阿嫂现在只是做手作,将来还可以开设酒楼,像班楼和梁宅园子那样。”
王妃看她眉飞色舞,放下荷叶盏问:“你昨日和耿郎子出游,两个人相处得怎么样?瞧出他的人品来了么?”
云畔也仔细观察惠存脸色,她还是淡淡的模样,只说:“是个体贴的人,说不上多好,也说不上不好,对上京哪家的甜食好吃倒是如数家珍。”
云畔听在耳里,心头也暗暗嘀咕,像那些有名的甜食知道几样倒是常事,若是对每一家都如数家珍,那就不大好了。向来女孩子都喜欢吃那些小玩意儿,他要是太过精熟,就说明前头有人让他费过不少心吧!
但眼下不能说,陪着长辈们吃罢了早点,和惠存一起从府里出来,登上马车只有彼此的时候才道:“那位耿郎子,你一定再好好瞧瞧,反正现在不急,离大婚还有三个月呢。”
惠存点了点头,“我省得,阿嫂就放心吧。”
既然如此,总不好阻挠人家的婚事,就像李臣简说的,尽到提点的责任,听不听全在她了。
后来进了铺子,就去接待那些莅临的女客,早前宰相夫人家宴上结识的贵女,像玉容、恰恰她们都来了,吵嚷着要学做乾坤核桃。云畔便手把手教她们,怎么打磨核桃壳,怎么调色,怎么和石膏。有些东西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女孩子们聚精会神雕琢了半晌,可能因为略略的一点出入,就前功尽弃了,立刻哀嚎声四起,云畔只得安慰她们,推翻了前头的重新再来。
几间雅室都有专人传授技艺,但总不及云畔亲自指点热闹,这一早上来回走动,忙碌得很,略晚些梅芬也来了,云畔道:“上回公爷带了螺钿和弁柄漆回来,我有个好主意,想做个螺钿杯,阿姐瞧成不成。”
说着便敛裙在长几前坐下,取来薄薄的贝母,碾成芝麻大小的碎片过筛,然后按着钿面颜色的变化分类,把不同色泽的螺钿挑出来。这是个极其消耗时间的手工活儿,几个人一齐上阵,花了半个时辰才逐一挑拣好。然后取来杯胎打磨上漆,螺钿需用粘性极强的生漆粘附,杯身刷上小小的一块,方寸之间一屑一星地贴上细钿,才贴了一指来宽,便已经让人觉得云霞潋滟,波光无边了。
旁观的贵女们乾坤核桃还没学会,立刻又坠入了螺钿的漩涡,大家纷纷嗟叹:“了不得,公爵夫人的巧思那么多,这样下来一年半载只怕都做不完。”
云畔笑道:“不过是消遣,得闲了便来光顾光顾,大家聚在一起才热闹呢。”
这里正笑谈,听见门上女使通传,说防御夫人来了。云畔和梅芬忙出去迎接,春生下了车,不等她们说话便自嘲起来,“大着肚子不在家歇着,见天地乱跑,你们可是要这么说我?”见她们都笑,自己也笑起来,啧了声道,“还不是闲不住么,昨日和梅娘子提的那件事,回去后就和家里说起了,家里父亲母亲都是极开明的人,听说是舒国公家千金,心里还犹疑,只怕咱们的门第配不上人家,冒然说合要招舒国公及夫人笑话。”
女人们都有这样的雅兴,说起做媒最是起劲,云畔怕春生累着,请她上里头坐定,一面又问梅芬:“阿姐回去后,和姨丈姨母提过吗?”
梅芬有些措手不及,她没想到春生这样放在心上,当时满以为是随口一提,谁知人家果然是当真的。这么一来倒不好意思了,只得搪塞着:“昨夜回去得晚,还没来得及回禀……”
春生是快人快语,摇头道:“我晓得,你哪里是没来得及,定是忘了吧!我同你说的那些可不是打趣,要不然今日也不会专程跑这一趟。反正鄙府上长辈求之不得,只要你点头,向公爷与夫人那里,咱们自然托了大媒正正经经提亲。”
梅芬推脱不得,难堪道:“姐姐盛情……”
“那就好!”春生一拍手,不等她把话说完就起身指了指街对面,“人我已经带来了,你瞧一眼,要是合眼缘,明日就去提亲。”
这话不光梅芬和云畔,连店里经过的女客也听见了。真是头回看见说亲说得这么着急的,倒勾出了众人的好奇心,于是大家簇拥着梅芬到门前,隔着长街望对面的人——那人穿青骊的襕袍,腰上挂着银制的蹀躞七事,因是武将,身量挺拔如劲松一样。深浓的鬓发,磊落的风骨,眉眼也长得匀停温雅,和赵重酝有六七分相像。见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人,好像狠吃了一惊,但还是拱起手,遥遥向这里作了一揖。
女客们都只是凑热闹,哄笑一阵后便又回去忙她们的了,春生搀着梅芬道:“你瞧,那就是我家小郎,人品样貌绝不输人半分,年纪轻轻便是正五品的官衔,将来前途不可限量,替你挣个诰封不在话下。”
所以这位武将被嫂子闹得没办法,只得巴巴儿跑来让人相看,可见是个好说话的人。
云畔轻轻拿肘顶了下梅芬,在她看来是个不错的郎子人选,就是不知道梅芬怎么想。
人在对面站着,到底不像话,云畔便吩咐身边的婆子上前传话,请观察使入店,并僻出一间雅室,好让他们说话。起先春生还相陪,后来便借故退出来,跟着云畔喝茶去了。
两个人莫名被拉到一处相见,对坐着都显得很尴尬,还是赵重言先开口,郑重道:“今日贸然来见小娘子,真是唐突了。原本应该登门先拜见公爷及夫人的,无奈阿嫂催得急……不过我早就听过小娘子大名,对小娘子很是敬仰……”
可见不是个会说话的人,什么大名,什么敬仰,完全是男人应酬使用的客套话,结果搬到姑娘面前,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
梅芬呢,因为前有何啸,一朝被蛇咬,令她在和陌生的男子独处时,胸口一阵阵发紧,手心里攥出汗来。
想来她脸上神色不大好吧,弄得对面的人也愈发紧张,两个人对望一眼,很快各自调开了视线,半晌听见赵重言结结巴巴道:“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和姑娘说话,今日……要不今日就……就算了,下回……”
他不老练,显得比梅芬还要紧张,这样反倒缓解了梅芬的局促。
她纳罕地看了他一眼,“观察以前没和姑娘打过交道吗?”
赵重言没头没脑地红了脸,低头说:“我在石堡城驻扎了六年,那里连……连耗子都是公的……”可能因为说话不利索,自己很着急,摆手道,“我不是结巴,就是有些……有些紧张……”
梅芬忽地便释然了,奇怪,看见他的反应,就像看见了另一个自己。早前自己也是这样,一紧张便结巴,她一直以为世上只有自己是这样,没想到今天遇见了一个应付不得姑娘的武将,有意思得厉害,不管将来婚事能不能成,总算是一种缘分吧!
她抿唇笑了笑,“观察是什么时候回上京的?”
他说:“我是上月才调回来的。”
“那么我先前曾与人两次定亲,两次退亲,观察知道么?”
这种事好像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为了免于将来骤然发现上当,现在说清了反倒更好。
对面的人似乎逐渐平静下来了,沉吟了下道:“定亲退亲并没有什么妨碍,小娘子的事我听阿嫂说起过,很佩服小娘子自救的手段。反倒是我,年纪不小了,现在说亲晚了些,要是再过两年,恐怕只能娶寡妇了……”
这话又把梅芬撅了个倒仰,简直忍不住想摇头,果真是军中呆惯了,还不及向序会说话。
可是莫名的,又觉得这样的人很纯良,人生铁画银钩,欠缺繁花妆点,虽然不知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但就目前看来,冲着这份腼腆,似乎也可以商谈商谈。
只是他大概因为被延康殿大学士家拒绝过,有点不大自信,犹豫了下道:“小娘子家对文武可有什么要求?我是个武将,不会文邹邹那一套。”
梅芬心想何啸还不够“文”么,心机深沉令人不敢细想,相较之下宁愿找个武将,没有那么多的心眼,说话直来直去倒也好,便道:“我父亲是因军功授爵的,当初领兵征战过黑水。”
赵重言哦了声,“对,我竟给忘了。”说着赧然看了对面的姑娘一眼,见她眉目温婉,心里极称意,只是不敢胡乱表明自己的态度,怕自己太过粗豪,冒犯了这位公爵府的贵女。
后来闲话两句,聊了聊军中岁月,又说目下虽调回了上京,怕不日又要受命去外地赴任。好容易鼓足了勇气,桌下的两手握成了拳,他说:“我冒昧问小娘子一句,不知能否容我向贵府下聘?”
梅芬讶然,没想到他问得这么直接,大抵是军中的人没有什么诗情画意,心里想办一件事,就坚定地朝着这个目标进发吧!
她垂下了眼,“观察才见了我一面,就决定下聘么?”
赵重言说:“能不能结交,三言两语就知道了。小娘子是个直率的人,我也不会拐弯抹角,若是小娘子不嫌我蠢笨,我明日就登门,拜见向公爷和公爵夫人。”
梅芬怔忡着,不知怎么弄得私定终身一样,可是看看这人,他的目光真诚且热烈,能融化坚冰。细思量一番,两家的门第是相配得过的,自己好像也需要一个伴侣,不说一辈子有多相爱,能相携走完人生就够了。
轻舒一口气,她微微笑了笑,“请观察先禀报过家中尊长再行定夺吧。”
这是委婉的答复,说明她已经答应了。
赵重言到这时才笑起来,爽朗的眉眼,看上去没有任何城府的样子。
右拳击左掌,他说好,“我这就回去禀报父母。”急急要出门,忽然想起来说了半天话,还没把自己的名讳告诉她,便回身道,“小娘子,我叫赵重言,小字万钧,天等十年四月初三生人……我这就回去禀报,请小娘子等着我的好信儿。”
他说完,快步走了出去,路过前厅,边走边向饮茶的两人拱手。
春生见他走得急,站起身问:“小郎,你上哪儿去?”
他已经走出铺子往街对面去了,扬声答了句“回家”,便翻身上马,朝长街那头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