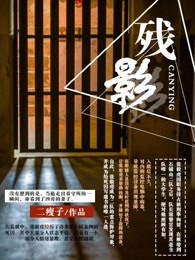从杀手大大家出来,我下楼,回家。
一路上,我特别平静。
说句真心的话,我安静起来,连我自己都害怕。
打开家门,我妈在门口换鞋。
她注意到我,问道,“什么时候出去的?”
我倚在门口,安静地看着她。
她也不是很在意我的回答,说着中午不回来吃了,今天要和编辑见面,就出去了。
目送她出门,我走回自己的房间。
从我家房门走到我的卧室需要七步,走到第六步的时候,我蹲了下来。
胃疼。
我蹲着,突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toki,真的会是你吗?
在我之前的陈述中,应该有人会发现一个悖论。
我说我在寻找一个人,可我又说他死了。
我说我没见过他,可我又说我可能见过。
整件事,需要重新放大一下时间轴。
今天在安以乐那里得知的事情,其实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
有人造成婴儿假死现象,骗过我的家人,也蒙混过在场的其他医护人员,然后悄无声息地将死婴掉包了。
没人再提起过这个孩子,我便一直作为家里的独生子成长着。
直到我七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翻到了我的宝宝日记,也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知道了他的存在。
起初的我,那个七岁的我,对士凉的存在是没有概念的,我那时甚至都不清楚双胞胎是什么意思。
只知道我有过一个兄弟,出生时就死了。
其实我没什么好难过的,那时我又没有见过他。但我不敢和父母提,因为我怕他们难过。
你看,这就是一种血缘逻辑。好吧,理论上,我还是有点难过的。
事情的转折源于我八岁那年经历的一次事件。
这件事后来还登了报纸,出于对当事人的保护,没人知道事件的主人公是我。
十年前,我们一家去埃及旅游。
尼罗河的赠礼,埃及。
我被父亲牵着,穿梭在石雕与神殿之间。
卢克索,这座坐落于尼罗河河岸的古城,其所孕育的古文明是那时的我所难以领略的。
身边的人们走走停停,有人静驻,一脸朝圣。
有人疾走,呼朋引伴。
也有人打转,忙着拍照。
我前面的一个阿姨停了下来,她举着一部看起来很重的单反,对着眼前的石雕按下了快门。
咔嚓。
不知道她手里的那部大家伙有没有好好记录下那个瞬间,至少我的大脑是记录了下来。
爆头,血花四溅。
人群开始骚乱起来,他们尖叫着,慌不择路。
我盯着那个倒地的阿姨,她的相机甩在地上,一路滑到我的脚边。
我想去摸那个相机,却被我爸爸迅速抱了起来。
之后我又是听到了几声枪响,视线里又炸开了几朵血花。
我感觉身体一晃,我父亲似乎是被谁撞倒了,我也跟着从他肩上滚了下来。
视野忽地变暗了,只能看到人们的腿,在我周围编织起了一个笼子,一个随时会倒塌的笼子。我吃力地爬起来,被人群冲出去好远。
我甚至没有力气喊出那声爸爸。
当我从这人网中脱落的时候,我发现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八岁的我,迷路了,在异国他乡。
事后过了很久,当我在网上检索那天的事件时,只用了四个平白的字解释了一切――恐怖袭击。
不过那时的我不懂,我最害怕的,是我可能找不到妈妈。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身边的神像被笼上了暗金色,天边泛着红,就和我在书上看到的一样。
路过一排一排的神像,最后我在一处停了下来。
那是一片废墟,有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坐在那里。
他靠着身后的柱子,迎面的夕阳照着他的脸。房檐的阴影投在他的身上,我以为那也是一尊雕像。
事实上,他确实如雕像一般安静。尽管我走到了他的身边,他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我可能是因为刚刚哭过,视线还是很模糊。当我走近,仰头望着坐在废墟上的他时,这才意识到,这个孩子,和我长着一样的脸。
他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色,在夕阳下泛着黝黑的光亮。和我不一样,他养着一条小辫子束在脑后,一条粗糙的麻布军裤,裤腿掖进一双小军靴中。而他上身却披着一件带点埃及民族特色的坎肩,脖子上系了一条藏蓝图纹的三角围巾。
“你好...”我说。
他头倚在身后的石柱上,面朝夕阳。听到我说话,他突然眯起眼睛。似乎我打扰了他的宁静。
见他没作出任何反应,我也只能悻悻地找个柱根坐了下来。我走了好久,很累。
太阳渐渐沉了,我想找妈妈的愿望更为迫切。
“那个...你叫什么呀?”
“......”
“我叫士冥。”
他可能是嫌我太烦了,终于有了一个不算是回答的回答。
“......我没有名字。”
“那叫你士凉怎么样?喜欢吗?”
他继续沉默着,我猜他是不想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因为不想再继续这段对话。
然而不是,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反问我,“为什么是士凉?”
“这是我弟弟的名字。”
“......”
我站了起来,“你和我长得很像!”
“像?”
“对!”
后来我才知道他压根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
他从废墟上跳下来,自顾自地走了。我无人可依,便屁颠屁颠地跟着他。
他要去岸那端的集市,我跟着他坐上了船。
我们荡在河中央,卢克索被尼罗河分割成两半,这一岸是生,那一岸是死。
河畔两岸的喧闹向我诉说着这长久的文明,而我那时是听不懂这呢喃的。
他坐在船头,手里是一把刻着镂雕的短刀。
“刚才就是那边,有人开枪杀了好多人...”我跟他讲。
他无视了我,平静地坐在那里。
“我迷路了...”我又说。
他看着河岸,手里娴熟地转着那把短刀。
下了船,我跟着他走上了集市。在集市的尽头,他找了个角落停下来。
他回头看我,从口袋里扯出一个面包丢给我。
我是震惊的,因为我一路跟着他,居然丝毫没有发现他偷了东西。
我当时有些蠢,我居然有些生气地说,“你偷东西是不对的!”
他丝毫没有生气,竟然扯动嘴角笑了一下。感觉在嘲讽我。
哦,我当时就觉得,这孩子这么小就学会嘲讽别人了,很讨厌。
他老三老四地叼着面包蹲在地上,嘟囔了一句,“货币交易是人类社会的发明,我不属于社会范畴,更别提什么文明。”
用现在的话讲,我当时的内心是卧槽的。
我忘了我当时说了一句什么,但一定是想表达卧槽的。
大概就是,卧槽,我没听懂。
他也没打算让我听懂,感觉只是中二病发作而已。
事实上,我们之间的交流少之又少。我找他搭话,一般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他无视我。第二种,像刚才这样说些卧槽听不懂的。第三种,他会突然整出两句外语。
个人感觉,他的语言系统还是非常混乱的。毕竟才八岁就游荡各国,装了太多外语导致他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说的是哪国语了。
比如我们吃完面包,又逛回集市上。集市边上有卖色彩斑斓的灯饰的,很有异域风趣,我便围着看。
他从我身边走过,并不打算等我。我便跑上去,拉住他。
我说,你看这边有块铜镜!
我紧紧地靠着他,试图把我们俩都挤进这块镜子中。他看到我们俩极为相似的脸,不易察觉地愣了下。
他说,他很久没机会照镜子了,有点忘记自己的样子了。
我当时万千感慨,感叹道你这是过了什么水深火热的日子。
他好像是给我解释了下,但是可惜他说的是不知道哪国语。
我假装听懂了的样子,听他踢里拖落地讲完一大串。
一路上,我跟着他。看着这个和我年纪相仿,面容相仿的少年,心里莫名升起一种矛盾的陌生与熟悉感。
熟悉是因为我们的相似,陌生是因为他似乎有着和我截然不同的童年。那种我无法想象的童年,而我们偏偏还那么相似。
我感觉他还是挺开朗的,有路人滑稽地跌到他也会扯扯嘴角。与我相处了几个小时,他也不再对我沉默。
他说,“你要回家是吗?”
“是的。”我甚至说,“你也可以和我一起回家。”
“为什么?”他平静地问,“就因为我们长得像?”
我说,“你还这么小,你的爸爸妈妈呢?”
他将短刀在指尖转了一朵刀花,很认真地思考了下,发现没有答案可以回答我。
按照我的回忆,他把我领到一个巷子,“有印象吗?你爸妈是不是住在这里?”
“大概...”我点点头。
我往巷子中走去。
他站在巷子口。
“你...”他叫住了我。
我停下来回头望他。
他说,“回去以后,告诉你爸妈快点离开这里吧,这几天不是很安全。”
我点点头,不舍地看着他。
突然,头顶一声巨响,有土屑落了下来。
感觉有人冲过来拽住了我的手腕,我的双腿也随着跑动起来。
他拉着我往巷子里跑去,身后不断坠落的碎石与瓦砾。
这条巷子是极窄的,两边是六七层高的旧楼房。
当时情况太紧急,他来不及拉着我转向往巷外跑,所以只能顺着往巷子里跑,随后他发现走投无路了。
如果不拉着我,我猜他完全可以冲上前,翻过前面那座矮墙脱险。
可是他没有,他抓着我,一个惯性把我甩到前面。
我只觉得视线一暗,随后鼻腔里充满了扬起的尘土。
我感觉我要窒息了,恐惧蔓延到胸口。
“你?!你怎么样了!喂!”我喊他,我知道他趴在我身上。
一股热流顺着我的脖子淌在地上,湿润了我整个侧脸。那不是我的血。
我奋力爬起,从碎石的缝隙中爬出来。
随后我愣住了。
我顾不得眼泪是否糊住了双眸,只记得那一片废墟之下,有着一个和我一样弱小的身躯。
同样的幼小,可他却护得我毫发无伤!
我把他从里面扯出来,两块大石在我们上方支起一个三角,这才保证我们俩没有被拍成肉饼。
但是仍然有几块大石块砸在了士凉的后背上,我把他拽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大口大口地呕血了。
我帮他按着腹部,试图缓解他的疼痛。
他吐得几乎缺氧,上半身软在我怀里,张着嘴,像一个永远倒不尽的水壶,任凭大口的血流出。
这个画面,一度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见血会失控。而这个场景也在我去教学楼怀旧那天上演了――王将在我怀里狂呕鲜血,由此勾起了我十年前本已沉寂的记忆。
看着怀里的士凉,我开始感到绝望,我一遍一遍地告诉他你别害怕,等爸爸妈妈来了会送你去医院。
他听不见我说话,他的眼神开始发直。
我觉得他可能是快要死了。
我用士凉这个名字一遍一遍的唤他,他也只是直直地望着天空,满口都是流不尽的血。
那天的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了。
当我再次回忆的时候,只记得医生在帮我包扎胳膊上的擦伤。我问他们,和我一起的那个孩子呢?
他们说没有我所说的那个孩子。
我拉着他们一遍一遍地用他们听不懂的中文说,还有一个孩子,和我长得一模一样,他被砸得重伤!
可他们都觉得我是被吓坏了。
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会做起那个梦。
夕阳西下,废墟之上,我说,“那个...你叫什么呀?”
“......”
“我叫士冥。”
“......我没有名字。”
“那叫你士凉怎么样?喜欢吗?”
有一种血缘逻辑告诉我,那个孩子就是士凉,他不是死胎。
我觉得他可能是死于了那场意外,但是我仍妄想有一日能再次得到他的消息。
可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对于士凉的事,我无计可施。
去年的时候,我拿着那张b超照片去了一家医院,打听到照片中确实是一对双胞胎。
我记得那天我哭了。而今天的我,不想哭。
我蹲在地上,把头埋在膝盖里。
toki,士凉。
真的会是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