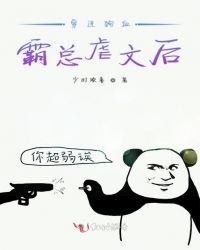一场透雨过后,卫河登时改变的模样。油油的绿色冲破铅灰色岸,如同天地
间一支巨笔抹就一般,挥酒道劲,直冲大海。
岸边巨型水车的多级车轮在河水推动下,吱吱呀呀的加快了速度。虽然很不
情愿,却奈何不了这奔腾的潮流。水车另一端连接着一级级齿轮和钢轴,带动两
岸工厂里的重型设备,将各种钢料打磨成型,淬火,再由泊在码头上的运输船拉
走。运到更远处的工厂里。装在火铳、巨炮和战舰上。
“加把劲,这批货今晚要做完,老板昨天刚接了个新单儿,大伙不愁没活干
……”工头的指挥声带着笑意,从岸边的工厂里穿出来,沿着河流飘向远方。
“那是,咱们厂,毕竟是老字号。”伙计们大声答应着,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频率。天津在二十年前还是个小鱼村。建城时间短,城里百姓多是从蓟州、永平、
梁城等地招募过来的工人和卖了土地转向新行业的工厂主,这些人性格爽朗,喜
好炫耀。哪个厂里边有活干,巴不得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加上工厂都守着在河边,
*河水的动力做活。哪家烟囱冒了烟,哪家厂房传出笑声,彼此都清清楚楚。那
笑声是最响亮的。肯定是生意最好的。能从开春笑到河水结冰的工厂。老板第二
年肯定会加盖厂房。招募人手。相反,一年中无声无息的工厂,也许第二年老板
就要曲尊到别人家做伙计,厂里的工人们就是另寻东家。
自从洪武十二年后,卫河两岸人家的生活就变了。这里不再是个无名小鱼村。
而是朝廷的战舰和火炮制造基地——天津。城里的工厂,有一半与军械制造业有
关联。特别是城北头的陈记。从北平搬迁过来时,头上就“顶着”圣旨,二十几
年下来。陈记早就成了天津第一天商号。陈记老板陈星,也成了天津众商家的领
军人物。跺一跺脚地面乱颤。整个天津城的工厂店铺都唯其马首是瞻。
傍晚,老陈星晃着圆圆的身躯,慢慢的蹭下马车。一个跟班伸手相搀,被他
一把推开了。人老了,难免脾气有些古怪。小跟班一吐舌头,屁颠屁颠跑到前边
去开大门,没等他跑到门边上。朱红色的府门吱呀一下打开,少东家陈青岩大步
走下台阶。搀扶住陈星的胳膊。
“爹,您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都督衙门里没有事情吗?”边向院子里走,
陈青岩边问。天津举义后,陈星被公众推举为大都督。眼下虽然战线已经远离天
津。但身为天津商团的首领和天津的最高军政长官。陈星的所承受的压力一点没
减少。做儿子的有心替父亲分担些。又实在帮不上忙,只好每天早早回来等在家
里。陪父亲说说话。也算尽到了孝心。
“今天没什么事,爵士会那帮家伙又在吵架。我听着烦,回家歇歇。”老陈
星疲惫的笑了笑,把胳膊搭在儿子的肩膀上。慢慢走进了院子。
这不是实话。从父亲的表情上,陈青岩就知道父亲心里有事,特别是近几天
来。在武伯伯的战舰*岸后,细心的青岩明显的发现父亲憔悴了下去,两鬓的白
发更多,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刻。
每当陈青岩看着老父疲惫的面孔,他的心里就发酸。当年北平火药局被炸,
母亲受惊吓过度,很快病故。父亲从此一个人支撑着整个家族,一步步走到现在。
家族事业越干越大。父亲身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姐姐出嫁后,他身边几
乎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自己所学。与父亲的观点又往往和不来。出了点子,
往往惹父亲不快。
大门在父子二人的身后吱呀一声关闭。陈青岩搀扶着父亲穿过爬满青藤的回
廊穿进书房,他看到陈星鬓角上的汗水,但现在北方的天气还没有热到主具出汗
的地步。况且陈星今天穿得也不多。
“爹,出什么事情了。”陈青岩将老父扶到椅子上坐好,接过仆人打来的洗
脸水,亲自润湿再拧干一块毛巾,放到陈星的手上。
“保皇党的人和立宪派的人在爵士会里吵起来了。”陈星抓起毛巾放在脸上。
话语显得有气无力。仆人听到父子之间说悄悄话。赶紧退了出去,顺手将房门小
心翼翼的掩好。
“那您跟着生什么气啊,他们不是天天吵架吗?这又不是第一次。吵完了。
还不是该干嘛干嘛,有了买卖交往,彼此还热乎的跟亲哥俩儿似的。”陈青岩笑
着安慰了老父一句。他内心里倾向立宪派,但知道父亲更倾向于保皇党的主张。
以陈家现在的地位。也的确应该保皇。这不仅仅是因为朱棣当了皇上,陈家就是
皇亲国戚这么简单。而是天津商团的产业决定了保皇对他们更有利。陈家是做火
药和军械起家,天津商团有一半以上和军火生产有关联。一个喜欢开疆拓土的皇
帝和一个决策迅速的朝廷比一个为军费多少吵上三个月的爵士会,哪个会购买更
多的火器,不用想,大伙也能知道。
“没那么简单。岩儿,去后院祠堂里,将香案上的那个黑盒子拿出来。”陈
星无力的摇摇头,低声吩咐。
“嗯。”陈青岩答应着。转身出门。一会儿,屋子里就又响起了年青人特有
的脚步声。一个黑漆金锁的盒子被摆到了陈星面前的桌案上。这个盒子的钥匙只
有陈星有。陈青岩从来没有打开过这个盒子。
盒子被陈星颤抖着开,里边是一叠宝钞。陈青岩吃惊的看着父亲将宝钞
取出来。一张张的摆在书案上,仿佛这些已经作废了的宝钞是什么稀世珍宝一般。
这是当年移民时官府给的宝钞。被武侯用银子买走了。后来陈家做烟花东山
再起。父亲又用银子将宝钞赎了回来。陈青岩听姐姐青黛说起过宝钞的故事,那
次移民,每一张宝钞都代表着一条人命。如果不是武安国及时用现银兑换了宝钞。
陈家老小可能就永远倒在北平的寒风里。
“爹,这些宝钞,你又想当年的事了。”陈青岩叹了口气,话语里充满了对
父亲的同情与理解。如今恩人武公和姐夫朱棣成了对立面。作为天津商团的领袖,
陈星的确很难做出抉择。
“是啊。当年如果没有你武伯伯,咱们一家就没命了。”陈星忧郁的说了一
句。随后补充道:“爹当年曾经立誓,此生武公差我风里火里,绝对不皱一下眉
头!”
原来如此,原来父亲为当年的誓言难过。做生意的人讲究信誉,说出的话轻
易不会反悔。陈青岩理解的点头,低声问道:“武伯伯这次来天津,跟您提要求
了吗?”
“没有,”陈星摇摇头,从儿子的话语中,听出了一丝狡猾的味道。武安国
没提要求,陈星自然可以按照自己想做的去做。这是一条很好的逃避理由。苦笑
了一声。陈星又摇了摇头。低声问道:“青岩。你知道爹为什么不帮武公吗?”
“为了姐姐和生意呗。那还用问?”陈青岩利落的答了一句,如今他也是商
团的重要人物,这点小问题,难不倒他。眼下对陈家最有利的事情,就是两不帮
忙,等到武安国与朱棣之间的明争暗斗见了分晓,再决定下一步动作。
“不全是如此啊。”陈星茫然的叹息道。沉重的呼吸将桌子上的宝钞吹落了
一地。“爹不帮武公。其实也是因为武公从来不提什么要求,他这个清高的样子,
怎能成大事。自古以来成大事的,那一个不是心黑手狠。他可以无欲无求。跟着
他的人怎能无欲无求。这么多年了,哪怕他要做皇帝,等高一呼,爹也不会皱一
下眉头去响应他。可他,哎!”
“姐夫和武伯伯毕竟有师徒之谊,况且武伯伯对姐夫还有救命之恩。所以即
使两人翻了脸,武伯伯也没性命之忧。”陈青岩一边收拾地上的宝钞,一边安慰
父亲。虽然内心倾向立宪派的主张,但武安国的确不是个好领袖。跟着他只会送
命。不会有好结果。想到这些,陈青岩也叹了口气,那些发黄的宝钞随着他的叹
息在地面上跳跃,暗红色的印记来回飘动。
“哎”,椅子上的叹息声让陈青岩听了心向下沉,仿佛是承受着什么重压般,
父亲的话音低而晦涩,“真是这样就好了,前几天燕子的部将从咱们买了一批”
乌金霜“,我今天查验回文,发现收货的不是燕王麾下那个军需官,而是个没听
说过的名字。”
“乌金霜”,陈青岩听到自家生产的这种独门炸药的名字,大吃一惊,手中
的宝钞顿了顿,一张线飘落满地。
半夜,大沙河南岩,一伙士兵打扮的人护卫着两架马车,行色匆匆的从南方
赶来。带队的长官是个急性子,在马背上连声的催促伙计加快脚步。掏出夜光手
钟,焦急的计算着时间。
道路两边的农田里没有人,青油油的小麦已经长到尺把高。很快就要灌浆。
受过战火洗礼的土地更肥沃。从农田里受惊冲出的鸟雀身上,就能看出丰收的影
子。今年春夏多雨,庄稼长势好,鸟雀也吃得肥墩墩的。听见人声,才飞起几步
来。就懒懒的扎进草丛。继续自己的美梦去了。
“你们几个,前方五里,警戒,如果有人赶夜路,立刻拿下。”带队的军官
用蒙古话恶狠狠的吩咐。几个朵颜武士答应一声,跨马远去,马蹄铁在桥面上打
出一连串火星。在这样宁静的夜里。马蹄声格外清晰。
“你们几个,赶快动手,凌晨之前一定将这里收拾干净,就像没有发生过什
么一样。”军官布置好警戒线后,对几个心腹工兵叮嘱。
“是,长官。”小工兵头目答应一声,组织人手从马车上卸下几个大箱子,
小心翼翼的抬上引桥,用绳子和器械吊着,慢慢的安放在拱桥的涵洞中。大沙河
石桥是一个多孔拱桥,引桥长而平坦。桥面高出河水两丈多。从圆滑的拱洞和整
齐的石梁上,可以看出此桥在设计和建造的时候着实花费了一番心血。当年为了
维修方便。建造者在桥侧面特意造出了石阶,现在这些石阶刚好给士兵们的工作
提供了便利。
一个时辰后,马车上的箱子都安放到位,工兵们拉出一团绿色长线,借着桥
面的藤萝掩护。将长线隐蔽的拉向岸边芦苇丛,为防止进水导致意外,每隔数米,
工兵就在泥滩上竖起一个小木架。将长线架起来。然后再用芦苇掩饰好。
干完活,又仔细的检查了两遍。工兵头目跑到军官面前,立正敬礼。“报告
长官,施工完毕。”
“没问题么,你确保万无一失。”早已等得不耐烦的军官低声询问。
“没问题,南北两侧的第三个拱洞都放了乌金霜,只要有一个爆炸。这座桥
都得完蛋,两根快速导火线已经拉到了指定位置,没人会发现。按长官吩咐,从
点火到爆炸不会超过两分钟。”工兵班长认真的回答。回头扫了一眼石桥,对自
己的杰作十分满意。这么多乌金霜,甭说这石桥,就是长城也能炸塌。他唯一不
明白的是,好好一座桥,为了一次演习,真炸了不可惜么?并且点导火索的人离
爆炸点那么近。根本不是个安全距离。
带队的军官仔细观察了一遍。看样子对工兵们的作业很满意,笑着拍拍工兵
班长的肩膀,表扬道:“有一手,带着你的弟兄们去洗洗脸吧,咱们明天还有别
的演习呢。”
“是,长官,”工兵班长憨厚的笑了笑,招呼几个部下走上了河滩,捧起河
水洒到了脸上。
猛然,他在河水的倒影里看到了一把马刀,借着月色劈了下来。
月色突然一暗,几个工兵同时倒在了河边的泥滩上。杀人的武士拖起工兵们
还带着体温的尸体。快步向远处一个泥坑走去。
鲜血在泥滩上画着一道道黑色的轨迹,被上涨的河水一浸。瞬间淡去了。刺
鼻的血腥味在空气中散开,慢慢消弭在冷冷的风中。
东方渐渐发白,石桥上又恢复了平静。昨夜的士兵不知道走到了哪里。河水
哗哗的从桥下淌过,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般,依旧向东流去。
距离石桥远远的几个土丘后,不时飞起几只野鸟,早起的庄户人家看到了,
纳闷的看看,无暇关注这些变化。埋头扎进了自家的田地里,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的,的,的”清脆的木鱼声在军帐中响起,大师姚广孝一手数着念珠,随
着木鱼声念颂佛经,满脸慈悲。
“大师,我们可以走了吗?”几个军营恭恭敬敬的走到姚广孝身后,低声询
问。
回过头,姚广孝的目光刀锋一般从帐篷里众人脸上扫过,口中佛经唱颂声止,
顺着这个语调,轻描淡写的说道:“当然可以,在洒家身边呆着干什么,早做些
准备,免得到时候有个风吹草动的,给弄得措手不及。”
众人的脸色瞬间变了变,都是经历过沙场的人。心里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
紧张过。姚广孝口中的“准备”二字,如蘸血写就,让人不忍再闻。是要准备,
如果陈亨能在半路上谋害了武安国。自卫军中间肯定有一大批人不肯善罢甘休。
下去准备,则是磨刀霍霍,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将亲武系将领的反抗风潮扼杀
在萌芽状态。
想到几天后,不知多少昔日的好友会倒在自己的屠刀下。有些人后悔不己。
但名字已经签在计划书上,如果此番刺杀不成功。众人的前途也从此毁掉,弄不
好甚至要丢掉性命。
几个将领彼此对望,眼神中都露出几分无奈。躬了躬身,倒退着走出了陈亨
的大帐。眼下虽然姚广孝没有什么官职,可大伙都明白,如果燕王被皇袍加身,
此人就是将来的赵普,半本佛经忽悠天下,所有人的升迁恐怕都得与这个三角眼
和尚点点头才能通过。
听到众人离开,姚广孝嘴角浮现了一丝笑意。他仿佛看到了燕王惊愕的表情。
也仿佛看到了享用不尽的富贵向自己招手。
“到时候,我就坚决不在朝中做官,而是以帝王之师的身份隐居在寺庙里。
这样既掌握了权力。又可以博得美名。我教也可以光大……”他虔诚的闭上眼睛,
脑海里出现了一尊如来,宝相庄严,仿佛在俯视着脚下弥弥众生。
“来人,擂鼓聚将。”讨逆军大营。老帅耿柄文猛然睁开双眼,大声命令。
雷鸣般的战鼓声在大营中响起,各路将领闻听鼓声,从各自的营帐中飞奔而
来。三鼓之后,帅帐中已经站满了武将。
耿柄文满意的点点头,讨逆军前一阶段虽然战败,但还没有垮。就凭刚才将
军们汇集的速度来看,这支军队还保持着老安东军的素质。看看众人已经到齐。
耿柄文挥挥手,几个参谋将一张巨大的地图铺开在帅帐中间的大圆桌上。
诸将领一同围绕到了圆桌边。圆桌会议本是震北军的传统,李景隆被调回京
城后,耿柄文在军队中也推行了震北军这一套做法。通过圆桌征集大家的意见,
同时也利用圆桌凝聚武将们的忠诚。
“我刚才接到线报。武安国不日即将抵达真定。为此,我决定。”一向从谏
如流的耿柄文今天出人预料,会议刚刚开始,没经讨论,即下达的作战部属。
“我军兵分两路,分头准备。一路以平安将军为主将,在武城准备,寻找机会重
插真定。另一路,我亲自带队。沿临清方向插往高邑,在真定府与平安将军汇合。
与北军决一死战。”
“元帅,这,北军现在士气正高?”将军何兴霸迷惑的问。他的问话代表了
很多讨逆军将领的疑虑。所有人抬起头,目光聚集在耿柄文脸上。
“一个坚持平等的人,和一个想篡位为帝的人,能搅在一起吗?”老将耿柄
文冷笑道。目光中充满对敌手的蔑视。“大伙立刻回去准备,这两天如果发现北
方有异常举动,我们马上出击。一战解决胜负。还大明百姓个清平世界!”
“张京,届时你部从武城出发,作为先锋,强攻董家庙,然后向东转,插到
冀州方向,那里是朱棣麾下张玉和郭璞麾下的林风火将军势的交叉点。他们一旦
发生内乱,彼此互相怀疑,不会组织起有效防御。占领冀州后,就地组织防守,
等待大部队汇合!”
“是。”被唤做张京的将领接过令箭,转身出帐,一会,帐外就响起了急促
的脚步声。
“耿忠,你带忠武师从丘县向鸡侧迂回,造成我军准备攻击广平的假相,不
要与敌过多接触。以调动守军,吸引注意力为目的。”耿柄文用笔在地图上画了
一道,指出了自己手下将领的行军路线和作战目的。
“明白。”小个子耿忠领命而去。
“何兴霸,你部执行穿插任务,待耿忠调动敌军后,闪击广平,将大名府的
军队分隔开,就地吃掉……”
“是!”
……
武将们按照耿柄文部属,接过令旗,陆续奔出帅帐。老将军耿柄文的笔在地
图上画出一条条红线。随着帅帐中的将领数量的减少,红线慢慢形成一个绳索。
向北方六省首脑居住的真定套去。
时隔多年,上天给了老将耿柄文又一次将敌军拖垮,并逐一击溃的机会。老
将军不敢独战其功。这个拖字战术出自黄子澄。虽然不喜欢黄子澄的为人。耿柄
文在内心深处不得不承认黄子澄这手拖延战术玩得高明,“北方六省不会团结一
心,朝廷的压力一去,他们必然为了彼此的利益互相残杀。”从这几天传回来的
情报分析,黄子澄当初也预见没有一点儿错误。没有长幼尊卑的秩序约束,人与
人之间的利益争斗足以让六省新政自己倒下。
马蹄敲碎夏日的宁静,田地里,农夫们茫然的看着军队一拨拨从眼前开过。
又要打仗了。有人低声叹息,这老天,难道就不能让人少流些血么?
千里之外,一队打着晋军旗号的队伍迅速向尉州*拢,那里是*近新政老巢
北平的地方,越过美屿所即可到达怀来境风。晋王麾下大将林心武跨在马背上,
不断催促士兵加快脚步。“走快点儿,走快点儿,误了晋王的大事,你们这辈子
就会永远休息!”
“报……”一声紧急报告声从队伍的后边响起,烟尘过处,几匹快马飞驰而
至,将一份火漆了的手谕交到了林心武的手里。马背上的信使边喘息边喊,“晋
王府将令,着将军一切按手谕上行事!”
“知道了,请王爷放心,”片刻后,林心武在马背上还礼,目送信使远去。
信封口的火漆已经被拆开,雪白的纸上,字数不多,却代表着晋王封地各派力量
的最终意见。
“燕王胜,则北上响应燕王。武公胜,则南下协助北方六省!”林心武笑着,
将密令撕碎了,吞进了肚子里。目光转向南方,到底与谁为敌,用不了几天,那
里会给他最终的答案。
夏日的阳光下,马背上的骑士们英姿飒爽,沿着水泥官道由北向南疾驰。在
骑兵队伍中间,护卫着一老一壮两个将领,老者高个光头,年龄看上去已经五十
开外,马背上的身影却和当年一样英武。壮年将领是老者的弟子,难得和师父一
聚,话语里带着兴奋。一路上指指点点,介绍沿途的风景和自己曾经的战绩。
近卫师长张正心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毛头小伙子,经历了这么多年历练和一场
又一场战争,他已经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统帅。骑兵们在他的指挥下,前后左右拉
开距离,彼此用哨子和花炮联络。由于地形所限制,武安国身边护卫人数虽然不
多,但远远看去却有千军万马的威势。
一个师的骑兵遥遥的跟武安国和张正心的卫队身后,随时准备接应,临来前
郭璞大人吩咐得好,一定要保护武大人平安到达真定,他是解决眼前危机的唯一
人选,有他在,北方六省各派系就不会分裂,不会在国家局势没安定下来前,刀
头先染上自己人的血。
马蹄声迅速*近了沙河大桥,河滩边芦苇丛里,数只受惊的野鸭子扑打着翅
膀飞上了半空。纷乱的影子吸引了骑兵们的视线。在岸边最不起眼的一棵枯树下,
发出了几声蟋蟀的叫声,吱吱,吱吱,轻微,细小,瞬间被湮没在马蹄声里。
两点火光在无人注意的情况下闪了闪,细细的丝丝声,就像风声一样轻微。
在卫队里绝对不可能有人听得见。
武安国与张正心纵马上桥,指点着天边浮云,微笑着,仿佛在讨论着一件有
趣的事。是北平新政之初的笑话,还是第一次北伐时的战绩?
两点火光穿越芦苇,迅速向烈性炸药乌金霜堆放处逼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