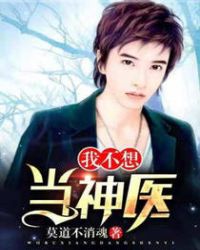处理s私文件时出错
宋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儒学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早思想上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当时因为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三教内容的靠拢兼容,所以自然形成了以崇奉黄老之道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其后周敦颐援道入儒,创立学。周敦颐晚年定居于庐山,筑书堂讲学于莲花峰下。莲花峰下出一溪,从书堂流过,他便以家乡溪一水命名,称此溪为溪,书堂为溪书堂。后世称他溪先生,称其学派为学。
“周敦颐虽然创立学,但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一般人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而没有人知道他在儒学思想上的高超成就。”赵明诚说道,“大宋有两个人非常了解周敦颐,并对其推崇备至。一个是南安通判程太中,他知道周敦颐在儒学上的造诣很深,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都送到他的门下学习。一个就是你的父亲李长浩。周敦颐的学就是在你父亲和程氏兄弟的极力推崇下,才广为天下儒士所知。”
周敦颐这个人李虎听老爹说过,之所以印象深刻来自于周敦颐写的一篇文章《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篇文章李虎自小就背得滚瓜烂熟,但没想到的是,它的作者竟然是大宋有名的大儒。
“你父亲在太学、国子监授学的时候,曾做了一件轰动天下的事,那就是把周敦颐、邵雍、二程(颢、颐)和张载并列为大宋五大鸿儒,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周敦颐霍然列于五大鸿儒之首。”
赵明诚说到这里的时候,想起了昔年往事,眼里露出一丝哀伤之色。
“这五位大儒在儒学上不但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各自开创学派。”
“二程在学术思想上承继了周敦颐的学,其后出入佛老,返求于儒家之六经,并传圣人之学,创天理论,自此有了二程(颢、颐)的洛学。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派称洛学。二程在政治上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也反对作为王安石新法理论基础的新学。在学术思想上,二程的洛学与王安石的新学更是直接对峙。”
“邵雍创立象数学。邵雍的思想结合了佛、易、儒三家,倾心于《周易》研究,并以易学为中心,构建了象数学。象数学侧重于宇宙发生论,且有方术倾向,故而不居主流地位。邵雍在政治上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有着相同的见解,对王安石新法多有讥评。”
“张载创关学。张载出生长安,后居陕西凤翔府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故称其学派为关学。张载对新法的态度不同于政治上连结旧党的二程,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保留立场。张载一方面主张改革,另一方面则主张循序渐变,不同意新法的‘顿革’。王安石变法之初,曾希望得到张载的支持,但张载在肯定其变法方向的同时,反对其变法的方法,于是二人相处默然,语多不合。”
洛学、关学在大宋归属道学,在这之外,尚有两大学派,那就是王安石的新学,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蜀学。
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故称其学派为“蜀学”。
提到新学,自然就要提到变法,提到变法就要提到党争。赵明诚一说到党争,心里就极度难受。几十年的党争,两派互相厮杀,最后搞出来一个元佑党人案,总算暂时停止了两派的纷争。
“在大宋,元丰党人又叫新党,新党是变革派,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学,而新学在元丰党人主持变革之际,更是成为官学,并延续至今。”
“元佑党人是守旧派,又叫旧党,而旧党在党争中逐渐分成了三派,就是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和苏氏父子的蜀学。元学术其实就是指这三种学术。司马光是陕州人,;故其学说叫朔学,朔学以史学为重点,洛学以道学为重点,而蜀学兼采佛老,偏重于文学。在这三种学术中,尤以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
赵明诚不厌其烦,把大宋儒家学派逐一说明。
李虎对儒家学说不感兴趣,他从赵明诚的话里得出一个结论,新党用新学做为锐意改革的理论基础,而旧党用洛学、朔学、蜀学做为因循守旧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国策,不管是变法还是不变法,都需要用一种学术思想做后盾。
未来的根基在西北,西北的士人主要是洛学、关学子,而这三种学术理论除了正统关学支持温和变法外,洛学和朔学都是反对变法,如此说来,如果自己要推行变法,那么可供选择的学术理论只有新学和关学。
“叔父,你认为,未来大宋变革的学术理论应该是何种学派?”李虎等到赵明诚把各家学派的理论大致说完之后,马上问道。
“当然是新学。”赵明诚不假思索地说道,“大宋要坚持变革,当然要以新学为学术理论基础。”
李虎沉默不语。
这种深层次的东西,他需要时间消化和理解。
“大宋当然要变革,这是毋庸置疑的事。”赵明诚正色说道,“大宋原有制度造成的弊端严重危及到国祚安危,如果不变革,哪有出路?蔡京主持的变革虽然导致新政蜕变,但这并不代表新政是错误的,变法是错误的。”赵明诚指着李虎说道,“你不是一直坚持要变法吗?既然要变法,当然就要坚持‘新学’,否则新政用什么学术理论做支撑?”
李虎惊讶地望着赵明诚,而李清照也从赵明诚这番话里听出了其它东西,她也十分吃惊。
“元佑党人案不能翻,元佑党人不能解禁,是吗?”李虎问道。
“是的。”赵明诚的口气非常坚决,“元佑党人案是错误的,这个案子迟早要翻过来,但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李虎追问道。
“变革成功之日。”赵明诚严肃地说道,“变革没有成功,大宋没有富强,这个案子就不能翻,元佑党人更不能解禁。”
李虎晕掉了,这个结果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学派之争、学术之争,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国策之争,就是变革之争。”赵明诚的语调有些高,情绪有些激动,“你用元佑党人,用元佑学术,那么只能因循守旧,没有可能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退一步说,你可以用元佑党人,但你要坚持改革,则必须用元丰党人,如此新旧两党共同执政,那么党争势必爆发,两党人士为此互相倾轧,大打出手,变革如何继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几十年的党争给大宋造成了巨大危害,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李虎低头沉思。
李清照忍不住了,她生气地质问道:“太上皇和蔡京发动了元佑党人案,把元佑党人赶出了朝堂,党争是没有了,变革是大刀阔斧了,但结果呢?结果大宋富强了吗?新政成功了吗?”
“太上皇和蔡京的做法没有错误,把元佑党人赶出朝堂,把守旧派驱逐汴京,定国是,全力推行新政,没有任何错误。”赵明诚指着李虎说道,“将来他若想变革成功,也要走这一条路,而且只有走这条路才有希望。”
李清照气得杏目圆睁,差点要和赵明诚翻脸了。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是新党,而赵挺之是元佑党人案的发动者之一,赵明诚支持变革,支持驱赶旧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夫妻两人在一起生活十几年了,赵明诚隐藏得很好,从来没有暴露自己真正的心思,但今天赵明诚终于吐了真言。
“你一直在骗我?”李清照气极了,面红耳赤,腾地站了起来,“你竟然骗了我十几年。”
“你不要只想着你李家的事,你要顾全大宋的利益,要为大宋千千万万的百姓想一想。”赵明诚正色说道,“对于大宋来说,若想长治久安,只有变革一条路,对于千千万万的大宋百姓来说,只有变革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而要变革,只能用强权为后盾,只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否则变革必定失败。”
“朝堂之上,怎么可能只有一个声音说话?”李清照厉声说道,“旧党人士有朔学、蜀学和洛学之分,新党不也是派系林立吗?”
“正因为如此,正因为要吸收党争的教训,吸收新政蜕变的教训,在未来的变革中,我们才要确保变革的两个原动力和过去完全不一样。”赵明诚激动地说道,“在未来的变革中,我们不但要保证发动变革的皇帝始终如一坚持变革,而且要确保实施变革的大臣们不再陷入党争之祸,所以,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我们统统都不要了,他们都已经成为历史了。”
李清照骇然变色。李虎吃惊地望着赵明诚,忽然明白了赵明诚的变革思路,那是一种全新的变革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