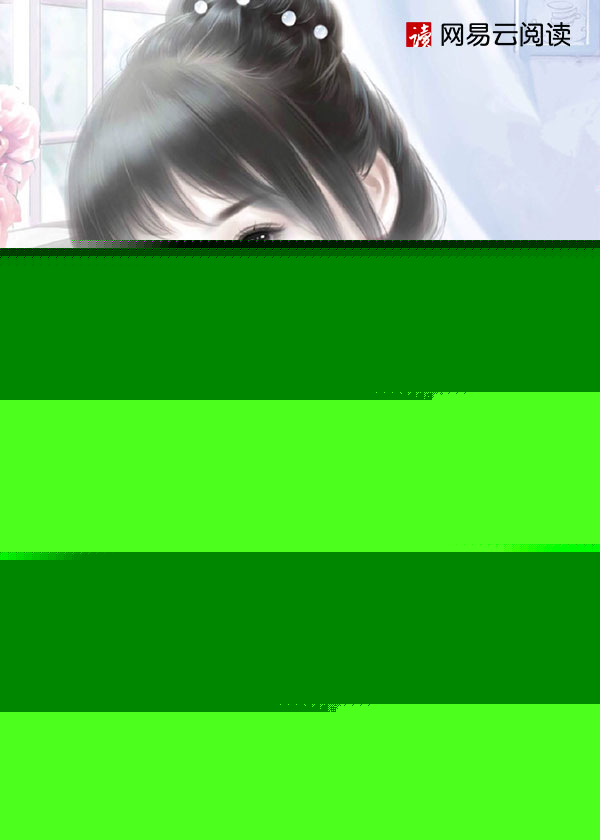殷妙双手搭在护栏上,望向窗外,眼里是淡淡的怀念。
“时间过得真快啊,算起来我出国那一年咱们就没再见过面,快八年了吧?”
段一鸣听到这里,不动声色地瞄了她一眼,什么都没说。
“你这次是回来了?”
“没有,刚从喀麦隆轮换回来,还不知道调去哪呢,可能欧洲,可能南美,也可能还在非洲。”
从决心投身于外交事业的那一天起,段一鸣就做好放弃部分个人利益的准备,且从未感到后悔。
“那你家里……怎么样?”
段一鸣面带惆怅地叹息:“都说成家立业,我正好反过来了,这把年纪还没成家呢。不过这样也好,人家好好的姑娘,跟着我东奔西走,满世界乱转吃苦,也不是个事,过两年再看看吧。”
他闭口不谈曾经追求过殷妙的那段往事,只像老朋友一样叙旧,免得两人尴尬。
隔着长长久久的岁月,时间早已磨平一切,也教会了成年人学会放下。
如今的段一鸣,身上沉淀了饱经历练的沧桑气质,和当初那个肆意妄为的少年相去甚远。
谈起这个略显遗憾的话题,两人一时陷入沉默。
身后的侧门突然被拉开,路德维希从楼梯间上来,出现在他们面前。
看到殷妙靠着窗户在和人说话,他脚下顿了顿,还是迎了上去。
将一袋三明治塞到她手里,他低声叮嘱:“早餐,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没吃饭吧?”
包装袋还是温热的,他今天琐事缠身,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备下的。
殷妙接过后,轻轻道了声谢谢。
路德维希不放心地又说了一遍:“记得吃,我先下去了,有事找我。”
临走前,他客气地对着段一鸣点了点头。
路德维希之前绕着会场找了一圈,现在却好像真的只是来送个早餐。
他说完这几句话就转身离开,没有任何其他表示。
段一鸣却眯起眼睛,定定望向他离去的背影,过了好一会儿,他表情释然地笑了笑。
“你们还在一起呢?”
“什么?”殷妙讶然地抬头。
段一鸣向楼梯间的方向扬了扬下巴:“他不是你男朋友吗?”
“……不是,你误会了。”
段一鸣右手拇指和食指轻微揉搓,是个想抽烟的姿势。
“你不用不好意思,我早就想开了。”
“他是叫路德维希吧?长得那么招眼,我的记忆力还没退化,应该错不了。”
“殷妙,两个人能走到今天不容易,别轻易就说放弃。”
“……你在说什么?”殷妙怔怔地问。
段一鸣转头看了她一眼,声音里满是怅然和唏嘘。
“还记得我那时候说过,德国和法国不就相当于跨省吗,我一定会去找你。”
“……我确实去找你了。”
“你知道的,我德语说得相当一般,到海德堡以后求爷爷告奶奶地打听了一圈,好不容易才找到学生宿舍……可惜啊,去的日子太不凑巧,正好撞上你和你男朋友吵架。”
“我当时心里还盼着,吵架好啊,我巴不得你俩赶紧分手呢,我好趁虚而入,从天而降给你个惊喜,然后夺得芳心归,结果你头也不回地跑进宿舍,我连喊你的机会都没有。”
“你那男朋友也挺奇怪啊,我看样子是他惹你生气的,可你跑了也不追,就在后面偷偷跟着你,跟木桩子似的在楼下一个人站着,也不道歉也不走人,完全不知道他想干吗。”
“我本来等着看他笑话呢,结果哥们竟然在底下站了整整一晚上,到早上五六点才走……”
“后来我就想,完
了完了,没机会了。”
“这人这么拗还这么疯,你就算和他分手,恐怕也不会喜欢上我了。”
段一鸣说到这里,忽然停了好久。
其实他没说的是,那天晚上路德维希的确守了一晚上,可他同样也熬了一晚上。
真正让他放弃的并不是路德维希的执拗,而是殷妙最后看向对方的眼神。
――她从来没用这样的眼神看过他。
于是他在那个夜晚清楚又悲哀地明白,自己的爱情没戏了。
路德维希至少还有站在下面守护她的资格。
他才是什么都没有。
殷妙听着段一鸣的话,脑袋里一片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