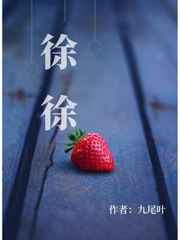这是个非常生僻的单词,但很巧的,宁织知道它的含义。两年前,在他还写公众号文章的时候,他就有一位叫作 sarcophagi 的忠实读者。或许用忠实读者来概括不太准确,因为 sarcophagi 从不评论,但是每篇都会打赏,好像没什么话想对宁织说,但又想让他注意到自己一样。
公众号停更以后,这位珍贵的读者失去了踪迹,两年后的今天,又如此突兀地出现。宁织看着那行字母,突然产生了一种故友重逢的唏嘘感,虽然他们素未谋面、并不相识。
他抱着窥探的心思摸进对方主页,结果发现 sarcophagi 非常不活跃,只偶尔发些城市的风景照片,有雪天的屋顶、雾气中的霓虹招牌、夜幕下的山峰轮廓。正在翻动态,江忏的消息进来了,宁织连忙点了个关注,然后退出微博。
江忏发的是个微信名片,就是之前联系过的精神科医生。宁织感激地道谢,江忏回了句不客气,口吻很是云淡风轻。
宁织继续吃饭,放弃了寡淡的茄子,对着鱼香肉丝挑挑拣拣,手机屏幕微微一暗,他碰了一下防止锁屏,可是亮起来的界面里并没有弹出新消息。
宁织斜眼看了一会,拿起手机打字:“你在干什么?”
江忏说:“吃饭。”
“外卖?”
“嗯。”
“我也是。” 宁织拍了一张快餐的照片发过去。
可能是因为刚才遇到了 sarcophagi,宁织心情不错,乐颠颠地说着废话。
江忏很快也发来一张午饭照片,宁织放大一看,顿时不平衡了。同是外卖,江忏的菜色就那么精致,杯盘碗碟摆了好多,跟皇帝用膳似的。
“吃得真好,” 他酸溜溜地说,“也不怕长胖。”
江忏觉得冤枉,午饭是助理订的,又不是他要故意讲排场。他把理由一讲,宁织更愤慨了:“还有助理可用,万恶的资本家!”
江忏无奈:“你不是也有?”
他指的是祝薇云派给宁织的两个实习生,前几天闲聊时,宁织随口提过。
“那是集团董事长的千金大小姐和未来女婿好吧,我才不敢使唤呢!”
“好可怜。” 江忏不自觉地对着手机微笑,“我请你吃。”
宁织配合地发了个 “嗷呜” 的表情包过去,表示“在吃了”,然后又打字:“谢谢老板”。
发送完毕后,他将手机倒扣在桌面上,猛喝了一口饮料。
耳朵还是很烫,冰红茶并没有起到降温作用。宁织有点害臊地琢磨,都说谈恋爱让人降智,怎么跟炮友聊个天也有类似的症状?这不正常。
雨足足下了一整天。
下午四点多,同事们心不在焉起来,交头接耳说闲话的声音多了,还有人走到窗前查看雨势,没带伞的抱怨着待会怎么回家,有家室的想提前溜去接孩子。陶珊趴在办公桌上,虚弱地哀叹:“饿了……”
热茶和糕点就是这个时候送到的。送餐员是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不像是职业外卖员,穿着白衬衫和灰色马甲,彬彬有礼地询问 “策展一组的同事坐在哪里”,找到位置后,一件件把奶茶、果茶、咖啡和甜点取了出来。
“哇,谁给我们点的,” 大家都很雀跃,陶珊探头朝祝薇云的办公室看,“祝姐吗?她今天没在公司呀。”
送餐员笑道:“是一位宁织先生。”
“我……” 宁织懵懵的,还没搞清楚状况,大家的惊呼和感谢就蜂拥而来,他不知该怎么办,只好傻笑着糊弄过去。
热热闹闹地,热饮和零食分完了,宁织叼着奶咖的吸管躲到茶水间,给江忏发消息:“你订的下午茶?”
“嗯。” 江忏回得很快,估计也在摸鱼:“你中午不是没吃饱吗?”
宁织的呼吸微微停滞,既焦躁又喜悦,这种复杂的心情就像意外捡到了一件稀世珍宝,处理起来很棘手,但拥有的感觉那么美好。
他斟酌良久,回了两个字:“谢谢。”
整日的阴雨过后,鹭江市终于放晴了。
周五的天气虽然称不上艳阳高照,但也和煦温柔,青南艺术中心的海棠树掉了些花朵,长出些绿叶。宁织一鼓作气写完了项目计划书,请祝薇云看过之后便发给了简青黎。随后又联系了江忏介绍的胡医生,确定了对方来家里诊治的时间。下班回家,他特意绕了段路,在小街买了一个烤红薯。外婆还在的时候说过,他母亲喜欢吃这个,现在郑秋代生病了又不肯去医院,宁织便想尽办法让她高兴。
推开门,客厅里一片昏黄,水晶吊灯没开,只有一圈窄窄的灯带亮着,郑秋代靠在沙发上,陷入了难得的、短暂的睡眠。宁织尽量放轻手脚,小心翼翼地给她盖毯子,但郑秋代还是立刻醒了,揉着干涩的眼睛坐起来,问他吃过饭没有。
母子俩把烤红薯分了,郑秋代吃得很慢,把红薯掰成一缕一缕的,吃糖一样抿在嘴里,看宁织的眼神里有浅浅的笑意。
自从因为去不去医院发生争执,他们之间的气氛始终有些僵硬,幸运的是,一个烤红薯就足以化解。
看到郑秋代比前几天多喝了一勺粥,宁织信心大涨,绷了好几天的神经也随之松弛。晚上,他洗了个热水澡,和江忏拌了几句嘴,充满期待地入睡了——梦里他母亲容光焕发地拉着小提琴,他父亲在画布前打量未完成的作品,江忏站在他正前方,仰着头对他笑,而他呢,坐在过山车上,轰隆隆地俯冲下去,像一支离弦的箭。
宁织做着小孩子才会做的那种征战游乐场的美梦,完全不知道他一睁眼,会看到什么新闻。
第15章 突发事故
周六,天蓝得像油彩,视野里不见一朵云。宁织神清气爽地睁开眼,把还差三分钟才响的闹钟关了,一跃而起。
洗了澡,他围着浴巾刮胡子、喷须后水,不时伸手去擦镜面上被他呵出的白雾。镜子里的青年有漆黑的发丝、深棕色的眼瞳和翘翘的鼻尖,皮肤很润,仿佛戳一下就能滴出水来。
宁织仰着脖子,余光往下暼,他的身体不算健壮,但也没到营养不良的地步,薄薄一层肌肉均匀地分布在骨骼上,瘦得很好看。宁织对自己的身材还算满意,平时很少去健身房,但偶尔也会幻想那种八块腹肌、宽肩窄腰的完美体型。不知道江忏是怎么锻炼的,宁织忽然想,见了面得问问他,到底吃了多少蛋白粉。
院子里,郑秋代正在扫地,听见宁织的脚步声,诧异地回过头:“今天不是放假吗?”
宁织讪讪地:“嗯,但我要跟朋友出去玩,所以起早一点。妈你吃什么?我去买。”
“都行,” 郑秋代挥舞着扫把,犹豫了一会,又问:“是上次来家里那个……”
可能是因为年龄,也可能是因为抑郁症,她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宁织接口道:“江忏。”
郑秋代低低地 “哦” 了一声,没有再说什么。宁织感到些许尴尬,抿住嘴,大步流星地出了小区。提着豆浆和小笼包回家时,郑秋代已经扫完了院子,正盯着墙上的挂钟出神。
宁织招呼母亲吃饭,郑秋代来到餐桌旁,小心翼翼地问今天去哪里玩。宁织回答游乐场,郑秋代呆了呆,似乎很不解:“怎么会想到去那里,不是小孩子才喜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