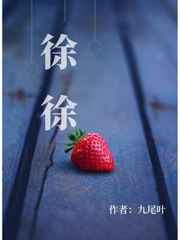当天晚上他们歇在汐园,宁织留了个心眼,发现郑秋代进的不是主卧,而是斜对面的客房,微微松了口气。郑秋代不知他心怀鬼胎,说了晚安之后就要关门,宁织突然冲过来,手一撑挤开了门缝,笑道:“妈,咱们聊聊吧。”
郑秋代愣了一下,退后让他进来,宁织拘谨地坐在单人沙发上,郑秋代则贴着床边坐下了。两人面面相觑地望了片刻,郑秋代疑惑地问:“怎么了?”
她的声音很温柔,宁织实在做不到开门见山,尴尬地搓着裤腿,说:“妈,我看你最近气色好多了。”
“有吗?”郑秋代摸了摸自己的脸,“我自己倒没觉得。”
“汐园……风景挺美的哈。”
郑秋代“嗯”了一声,见宁织欲言又止,便多说了几句:“也就你江叔叔有闲心,天天和园丁打理那些花草,后山的野湖也漂亮,前几天我们还去那钓鱼呢。”
宁织忙道:“你和江叔叔很聊得来啊。”
郑秋代并不否认,谈起江启平,她的语气中充满赞许和钦佩:“你江叔叔懂古典乐,也懂油画,人又幽默,很有意思。以后你接触多了就知道了。”
幽默?宁织怀疑自己听错了,在心中翻了一个大大的白眼。他尽量委婉地问:“那你觉得他怎么样?”
“什么我觉得他怎么样?”郑秋代感到莫名其妙,看宁织表情严肃,忍不住笑了,“刚不是说了吗――”
笑着笑着,她意识到了什么,惊讶地张开嘴,定定地看向宁织。确认过眼神,发现真是自己理解的那个意思后,她又笑了,不过这次无奈居多。
宁织撇清道:“你别误会,我不是阻拦你们。”
“你想哪去了,我们只是朋友。”说完这句话,郑秋代沉默下来,窗外寂静的夜色似乎感染了这间卧室,宁织大气也不敢出。
片刻后,郑秋代再次开口:“我们就是互相做个伴,说实话,你爸走了之后我心里很难受,但一直没告诉你,你江叔叔呢,这么多年也过够了一个人的日子,我们凑在一块,就是希望老年不孤单。都五十多奔六十的人了,没想那么多。”
宁织吸了吸鼻子,一股酸意窜到头顶,他说:“妈,我真不是那个意思,如果你们相爱,我会祝福你们的。”
“唉,你这孩子,”郑秋代柔柔地叹息了一声,和蔼而沧桑的眼神落在他年轻的脸庞上,“宁织,人的感情是很丰富、很复杂的,目前来看,我和江先生不会结婚,不过,谢谢你的祝福。”
同一时刻,关着两扇红木门的私密书房内,另一场谈话也在进行中。
江忏有个项目请教江启平,请教完了也不走,赖在太师椅上,不断摩挲着光滑的扶手。
他们父子俩的关系比那边的母子俩生疏多了,这么多年,互不干涉私生活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相处原则。
江忏在脑海中预演和推敲自己的说辞,嘴唇紧抿着,倒是江启平察觉了他的反常,问道:“公司那边怎么样?”
江忏回过神,如实汇报了最近发生的事情:“江瑞成向法院起诉了,要求撤销股东会的增资决议。”
江启平哼了一声,说:“法院判决没个一年半载的下不来,我们的增资程序又完全遵守公司章程,他赢不了的。倒是你,下个月的董事竞选演讲准备得怎么样了?”
江忏谨慎地说:“还好。”他知道江启平去意已决,等帮助他在集团董事会站稳脚跟,就会彻底放手。江忏责任重大,这段时间偶尔会失眠,幸好有宁织陪着,再辛苦也不觉得疲惫。
想到这,他忍不住以一种新的眼光打量起对面的男人来,不须定神细看,江启平衰老的痕迹已经明显。虽然身体依旧硬朗,眼神依旧坚毅,但完全不复年轻时的意气风发,尤其不如妻子在世时。
江忏心神一晃,下意识问:“你想我妈吗?”
江启平扬了扬眉毛,笑了:“当然。每天都想。”
从窗外吹来一缕湿润的风,驱散了书房的闷热,江忏嗅到了雨水的味道,不久,淅淅沥沥的声音果真响了起来。
父子俩沉默地听雨,过了一会,江启平说:“你的眼睛和曼曼长得很像,那时她刚走,我看到你就想起她,所以把你放在姑姑家――”
江忏制止了他的道歉:“我明白。”
江启平转过头,惊诧、感慨,江忏也看着他,两人对视几秒,不约而同地笑了,就此释怀。
这天晚上他们聊了很久,凌晨两点才散。江忏回到卧室时,宁织已经睡着了,一盏台灯幽幽地亮着,将他的脸照得雪白。江忏掀开被子,小心翼翼地躺在他身边,宁织翻了个身,撞到他的肩膀,迷迷糊糊地叫他的名字。
“是我。”江忏在他嘴唇上亲了一下,关掉台灯,说:“睡吧。”
.
雨过之后风和日丽,一夜滋润,山林里竟然冒出些大大小小的蘑菇。汐园的刘管家是云南人,小时候在山里长大,对菌子很熟悉,带着江忏和宁织去后山捡了半筐。
他边捡边上课,介绍每种蘑菇的特点,哪种有毒哪种无毒,哪种鲜美可口哪种寡淡无味,滔滔不绝。宁织亦步亦趋地跟着,睁着清澈的眼睛,听得十分专注,像模像样地将几朵蘑菇摊在手里比较,不时点头回应老师的教诲。趁刘管家不注意,还凑到江忏耳边教训:“你怎么不好好听?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用上这些知识。”
江忏失笑,揶揄道:“荒野求生的时候吗?”
宁织瞪他一眼,小跑着追老师去了。
采来的新鲜蘑菇,当天中午就由厨师处理了,或炒或煮或煎,弄了一桌蘑菇宴。
江启平把管家、园丁、厨师都喊来吃饭,大家热热闹闹地坐了一大桌,欢声笑语在别墅里回荡不绝。
宁织侧过头,小声问江忏:“你跟叔叔谈了吗?”
“谈了,他说就是跟郑老师做个伴。”
“我妈也这么说。”
宁织抬起头,刘管家正在讲年轻的时候当兵的故事,以及在边境的各种见闻,江启平和郑秋代听得投入,嘴角轻轻勾着,眼里不见阴霾。
真好,他在心里说。
午餐过后,江忏和宁织要回市里,两位长辈一直送到马路边上,往汽车后备箱里塞了不少水果和茶叶,郑秋代还修剪了两束鲜花让宁织带回去。
没有什么依依不舍的场景,双方简单地告了个别,江启平叮嘱江忏开车小心,郑秋代则说,下周再过来。
开出去几百米,后视镜里仍能看到江启平和郑秋代的身影,宁织有些难过,将右手伸出车窗,使劲挥了挥。
下山之后,江忏看了宁织好几眼,见他始终怏怏的,问道:“怎么了?”
宁织摇了摇头,几秒后,打起精神说:“江忏,如果以后我比你先离开这个世界,你一定不要太难过。”
他后面本来还有话的,但被江忏打断了:“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