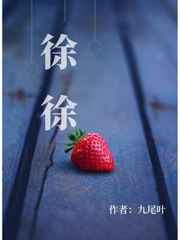小院外传出汽车引擎声,郑秋代抬起头,脸上有了轻微的喜色,快步走出别墅。
宁织从一辆黑色奔驰中出来,手里提着饭盒和纸袋,叫了声 “妈”。
郑秋代点头,看着驾驶位上年轻英俊的男人:“这是……”
“我朋友。” 宁织的表情有些不自在,后悔刚才没有拗过江忏,让他把车开进了小区,开到了家门口。
“阿姨您好,” 江忏下了车,自我介绍,“我叫江忏。”
“哎,你好。” 郑秋代苍白消瘦,但首席小提琴手的气质还在,微笑时犹如玉兰花开,静而美:“谢谢你送宁织,吃了晚饭再走吧。”
江忏礼节性地推辞,见郑秋代坚持,才接受了好意,一脸歉疚地说:“不好意思阿姨,没准备什么像样的见面礼,这个,希望您不嫌弃。” 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看尺寸是个胸针,送到郑秋代手上。
“你――” 旁边的宁织眼睛都直了,这还叫没准备礼物?他怎么觉得江忏准备得过于充分了呢?
“哎,太客气了,” 郑秋代也吃了一惊,打开盒子一看,果真是个钻石胸针,设计得简约大方,与她那些优雅的礼服相当搭配。
只是近两年来,郑秋代已彻底丧失了装扮自己的兴趣,摇头说着 “这不合适”,就要还给江忏。
“您收下吧,” 江忏轻柔地推她的小臂,讶异于她的瘦削无力,“我和宁织……”
故弄玄虚的停顿让宁织感到一阵轻微的紧张,手指上勾着的饭盒前后晃动起来。
江忏卖了个不讨人厌的关子,笑着说:“我们是好朋友,您别见外。”
第12章 同病相怜
“宁织还是第一次带朋友来家里呢。” 郑秋代对江忏说。
或许因为来了客人,她把一楼的灯全部打开了,别墅里亮堂堂的,压抑的感觉散去不少。
“是吗。” 江忏笑了。
宁织回避他的眼神,没来得及看清他脸上是戏谑还是同情,心想这是我的错吗?小时候天天被爷爷抱在怀里教甲骨文,上了幼儿园小学,跟同学们一点共同话题都没有,难得交上了朋友,才不愿把他们带回家,让古板无趣的长辈们毁了友谊。
一阵忙乱后,郑秋代从厨房端出一盘扎着牙签的苹果:“真是对不起,家里没有什么水果了。”
“阿姨您不用客气。” 江忏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发觉郑秋代的生活十分朴素,朴素得有些清贫。
但不应该是这样的。
无论是宁冉章留下的遗产,还是郑秋代自己的收入,都足够她过上优渥的生活,不至于拉开冰箱,只剩下两个苹果、三个鸡蛋。
“小江在哪里工作?” 郑秋代和气地问。
江忏回答:“一个小公司。”
坐在对面的宁织发出 “噗” 的一声,金鱼吐泡泡似的,对江忏的虚伪施以谴责。
郑秋代又问:“是什么职位?也是策展人吗?”
“没有,” 江忏抿了口茶,“算是职业经理人吧。”
宁织又撇嘴,眼睛却是笑着的,弯成柳叶。他往后靠,磕到了什么坚硬的东西,一摸,是他母亲的小提琴盒,上次他回家的时候就在这里。
以前郑秋代是每日必练琴的,从什么时候开始荒废了?
他想问,却不知如何开口,童年时不亲近的母子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他做不了那种体己的、撒娇的孩子,也不懂委婉关心的方式。
郑秋代与江忏仍在闲聊,节奏掌控得很好,像一首舒缓的老歌,不知怎么说到了江忏的教育经历,宁织惊讶地发现,江忏也是在茂市读的大学,而且与他同一级。
“你是哪个学校?” 他有些兴奋地插嘴,“是在东文区的大学城吗?”
东文区有好几所高校,如果江忏在那里上学的话,他们很有可能在街上遇到过。虽然这种相遇没有什么意义,但已经是宁织竭尽全力抠出来的缘分了。
江忏摇头:“我在 A 大,西河区。”
“啊。” 宁织一愣,又觉得理所当然,A 大是顶尖学府,江忏谈吐不俗,想必成绩也很优秀,不读 A 大才奇怪。
而他之所以热切地希望江忏在东文区读书,希望他们曾经擦肩而过,也许只是因为潜意识里,他还想为他们初见那天的事情做个解释。想证明他不是随便就答应了江忏,他们之间有很深的渊源,酒吧的相遇只是露在地面上的一片叶子,底下还连着无数的根须。这样的念头太幼稚了,宁织暗中唾弃自己。
郑秋代说:“一个城东一个城西,确实挺远的。”
江忏打趣道:“可不是,我大学室友的女朋友就在东文区,隔着一个城市,也相当于异地恋了。”
郑秋代轻声笑,眼角堆起几缕皱纹,突然,她想起了什么,皱纹凝固不动了,严肃地刻在脸上:“还没问,你和宁织,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挺简单的问题,但没有得到快速的回答。也许是因为心虚,宁织总觉得那几秒内,客厅里安静得突兀。
“其实……”
“看展!” 宁织高声打断江忏,做作地维持着欢欣的语调,“前几年 S 市有个安迪 . 沃霍尔的作品展,我们偶然遇到了,发现都是鹭江人,就认识了。”
他说谎技术不错,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编得有鼻子有眼。江忏微笑着点头,替他打掩护,补上没说完的话:“其实,我爸收藏宁老师的画。”
宁织愣住,耳朵尖发烫,有些抬不起头来,使劲扎了块苹果,放进嘴里猛烈咀嚼。
听到丈夫的名字,郑秋代微微失神,交叉在胸前的手指握紧了:“是吗?鹭江市有位老板收藏了他好几幅作品,也姓江,叫――”
“江启平,” 江忏顿了顿,“就是我爸。”
“那还真是有缘。” 郑秋代肺部的气息似乎不足,缓了一会才说:“我以前见过江先生几面,他很懂画的。”
“妈,” 宁织捏着牙签,迟疑地问:“你是不是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