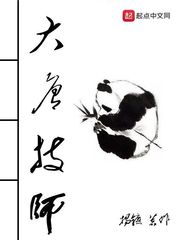大唐技师 !
房玄龄故意把声音放大,以便祠堂里的卢氏听到。眼角的余光瞥见卢氏动了,他才加快脚步,带着管家匆匆离开。
卢氏来到门口,瞧着房玄龄步履匆匆,抬手叫过院子里正在打扫的下人,问道:“刚刚公爷说什么?谁来了?”
国公府上下,谁不知道是卢氏当家。下人不敢不答,道:“管家来报,说是逐鹿侯来访。公爷说不能怠慢了,要大开中门迎接。”
“什么?!”卢氏登时勃然大怒,道:“什么人都值当他大开中门去迎?真是越来越不尊品了!来呀,取我的诰命服来!我倒要看看,这个李牧是个什么怪物!天上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日我便要为范阳卢氏报了大辱!”
房遗爱听到这话,也顾不得还在罚跪了,起身跑过来拦着,道:“娘,使不得啊!这个李牧不是一般人物,您这样会吃亏的!”
“让你起来了么?”卢氏扬起手里的戒尺,房遗爱只好跪下,但还是说道:“娘,在府里,爹让着您,我们敬着您,您怎么着都行。但是在外头,可不是什么都能随着您的心啊,李牧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能斗倒叔公,必然是有本事的,您……”
“休要说这些废话,你是想说你娘是个女流之辈,不顶用吗?真真是一点礼数都没有!他李牧再厉害,能比得过皇帝?你给我跪在祖宗面前悔过,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管!”
卢氏曾因李世民要赏赐侍妾给房玄龄的事情,与李世民发生过正面冲突。李世民拿来醋当毒酒让她喝,她仰头便喝了下去,李世民吓得也不敢再管。卢氏以为是自己赢过了皇帝,其实这是妇人之见,李世民身为皇帝,怎么会惧怕一个妇人。他是看出房玄龄对卢氏的情意,不忍逼死自己重臣的妻子留下恶名而已。
卢氏目光短浅,以此为凭,炫耀自己的厉害,李世民也有过几分耳闻,但他也没说什么,权当是看在房玄龄的面子了。
卢氏在丫鬟的伺候下,换好了诰命服饰,提着一股气,气势汹汹便来到了前院大堂。走到门口,正要推门而入,听到里头的谈话声,卢氏微微蹙眉,在门口站住了,没有进去。
“……房相,寒暄也寒暄过了,为了节省时间,我就开诚布公了。这次我来叨扰,除了拜年之外呢,还有一件事要跟房相说起。近日,房相想必也听说了,最近粮价上涨的事情。房相身为宰辅,自然是明白,民以食为天,粮价关乎社稷。若是天灾人祸,也就罢了,去岁没有大灾,粮价却徒然上涨,这件事的背后,必有人捣鬼!”
房玄龄点头,道:“此事确实不正常。”
“陛下震怒啊!”李牧站了起来,怒气冲冲:“房相,你说怎么会有人枉顾法度至此呢?牧虽年幼,但这基本的道理,也还是明白的,百姓不可欺,黎民不可辱啊!”
房玄龄瞅着李牧,心中暗道,什么叫人才,这就是人才啊!若不是提前知道,这是演给妻子看的一场戏,房玄龄都要以为李牧说的是真心话了。
李牧已经入戏了,哪知道他在想什么,继续按着心里的剧本,道:“陛下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自然是竭尽全力为陛下分忧。派出锦衣卫,调查了此事。事情并不难查,半天的时间,脉络已经清楚了。此事背后捣鬼者,乃是以范阳卢氏和荥阳郑氏为首的山东士族。他们不甘心陛下对他们的惩罚,妄图操控粮价,威胁陛下,威胁朝廷。如此胆大包天,与造反何异?”
卢氏躲在门外,听到“造反”两个字,心登时提到了嗓子眼!
山东士族对李世民的不满人尽皆知,但要说达到了造反的程度,却也是没有的。原因么,很简单,不敢。
当年山东士族,为了自己的私利,支持地方豪强试图拥兵自立。一时间诞生了多少的豪杰,最后怎么样?还不是尽数被消灭了?而且消灭他们的还不是战无不胜的天策上将李世民,只是不以武力见长,手中也没有多少良将的李建成。
换成李世民亲自去,以李世民当时的作战风格,山东士族现在能否存在都是两说。
所以时至今日,山东士族对李世民的反对,永远都控制在嘴上,而不会真个行动。因为他们心里头清楚,没有一个如当年李世民一般众人归心的人带领,山东士族再强大,也不过就是一盘散沙而已。
李世民也是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一直也没把山东士族真正当回事儿,只是觉得烦人罢了。
但如果李世民真的认为山东士族会造反,那事情可就大了。李世民是皇帝,初唐又是将星济济的年代,刚又大胜了突厥,士气正旺。可谓是雄兵百万,猛将千员。反观山东士族,有粮无兵,几百个守护庄子的乡勇,在大唐铁骑面前有当得上什么用处。他们就像一群面对饿狼的肥羊,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事关范阳本家,卢氏如何能不紧张。有心推门进去,却又担心她进去了,李牧会碍于她在旁边而不继续说,只好继续等在门口,等着听李牧接下来说什么。
“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汇报给了陛下。陛下听了之后,非常的生气。当即便要下令,把涉事的粮贩共计三十余人,全都抓起来斩首,以儆效尤!”
房玄龄在旁看的是叹为观止。作为大唐的宰相,若是真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要一次性斩首三十余人,他不可能不知道的。这件事肯定是没有的,但绝就绝在这儿了,李牧能把没有的事情,说得跟真的一样,真是太绝了!
忽然,房玄龄看到李牧递过来的眼神,急忙收起看戏的神态,叹了口气,道:“这些粮贩虽然有罪,但一次斩杀这么多人,也实在是有点……陛下曾立志做一个明君,此举对陛下的声名怕是有损啊!”
“是呀,是呀!”李牧跺脚道:“我也是这样想,房相与我,所见略同啊!”
房玄龄差点没憋过气去,饱读诗书如他,怎么会没读过《三国志》,英雄所见略同,语出《三国志・蜀书・庞统传》,天下智谋之士所见略同耳。这是一句英雄惜英雄的话,话是没什么毛病,但被李牧说出来,总有一种把俩人拉到了同一水平的感觉。
房玄龄听得是十分的不舒服,但此时有求于李牧,也不能说什么,只能赔笑含混过去。
“……我当时就跟陛下说了。陛下,您糊涂啊!为了荥阳郑氏,范阳卢氏这一群牛马,毁了自己的一世英名,何苦来哉呢?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那都是一些什么玩意,那就是乡野村夫,泼皮无赖,尤其是那个什么狗屁大儒,圣人的经书都读到了狗肚子里!都是些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辈,陛下您跟这些人,犯得着较真么?这就如同对牛弹琴,恁地丢了身份!”
这一顿好骂,不但门外的卢氏听不下去,就连房玄龄也有点听不下去了。范阳卢氏,荥阳郑氏,那是五姓七望之一,千年的门阀。早在三朝之前,人家就有响当当的名号。祖上随便提起一个来,都是当代的名士。
怎么到了李牧的嘴里,就成了牛马、村夫、无赖了呢?
房玄龄担心夫人爆炸,赶紧往回找补,道:“话也不能这么说,既称大儒,必定是有本事的,不可妄言,不可妄言啊。”
“妄言?”李牧冷笑一声,道:“圣人教他们忠君,他们忠么?圣人教他们爱民,他们爱么?他们若是爱民,也不会哄抬粮价,让百姓买不起米了!我骂他们怎么了,我骂他们,他们还得谢我,要不是我拦着,此时他们已经人头落地了!”
房玄龄可算是见识李牧这张利嘴了,担心引出更多的话来,只好附和:“对,你说得对,他们得谢谢你。”
“我乃君子也,岂能跟他们混为一谈,他们的谢,我可不受。”李牧一脸傲娇,道:“经过我的劝说,陛下答应不斩他们。限时三日,让他们把粮价降回去,并承担一切损失。同时每个人罚五百贯,用来救济孤儿流民。”
说道这里,李牧深吸了一口气,赞叹道:“陛下之胸襟如四海,真是我等学习的楷模啊!房相,你我身为人臣,能在这样的陛下领导之下,真是……真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房玄龄已经懒得说什么了,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但是!”李牧忽然来了个大喘气,吓得房玄龄心里一哆嗦,暗道你就不能一口气说完么,这一惊一乍的,谁受得了啊!
“陛下爱民如子,对这些不懂事的商贩,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罚过酒算了。但是朝堂中的蛀虫,却不能这么轻易算了。身为朝中大臣,却心不在朝堂,而在于私利,这样的人,必须得找出来,除掉!”
李牧余光扫了眼门口,继续道:“陛下的意思是诛杀吃里扒外的奸臣,杀鸡儆猴,让某一些人,涨涨记性!这也是我今日来找房相的目的,这件事情,与房相多少有点关系。”
房玄龄听到李牧这样说,真有些糊涂弄不清楚真假了,心里头不禁加了小心,道:“与我,能有什么干系啊?”
“卢照龄此人,与房相有亲吧?”
房玄龄有点蒙住,喃喃道:“老夫不记得有亲呐……”
这时,卢氏实在是忍不住,走进了大堂,道:“公爷,您糊涂了,有亲。虽来往不多,但卢照龄与我同是范阳卢氏出身,算起来是我的堂弟。”
房玄龄其实是装出来的,朝中的官员,他哪个不知道。见卢氏忍不住出来了,他偷偷对李牧使了个眼色,介绍道:“李牧啊,这位是我的夫人。夫人呐,这位便是如今大唐第一俊才,逐鹿侯李牧。看看,是不是一表人才?”
卢氏恨李牧入骨,听到这话,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但由于担忧范阳卢氏的安危,只得挤出一丝笑容,道:“逐鹿侯能被陛下委以重任,如何能不是人才?老妪我听说逐鹿侯来了,特意换了诰命衣裳来见,不敢有丝毫怠慢。”
李牧拱手见礼,笑盈盈道:“小子见过诰命夫人,夫人这身衣裳可真是漂亮,是几品诰命来着?”
“夫封从一品国公,自是从一品诰命。”
“哦!”李牧恍然大悟,道:“原来是沾了房相的光,我道怎么比我夫人的衣裳漂亮呢,原来如此。我不比房相,只是区区从三品军侯而已,所以我的夫人啊,也只是从三品的诰命,说起来,也是对不住我的夫人啊。”
卢氏的脸色登时难看了起来,她岂能听不出,李牧话语中的嘲讽之意?他是在说,卢氏的一切荣耀,都来自于房玄龄,没了房玄龄,她什么也不是,就算是从一品的诰命,也没有什么好炫耀的。
房玄龄在旁边胆战心惊地看着,生怕夫人原地爆炸撒泼。但让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卢氏的脸色从难看到更难看,再然后竟然渐渐平复了下来。
“方才在门口,听到逐鹿侯谈及范阳卢氏,范阳卢氏是我的娘家,因此颇有几分担忧,还望侯爷不吝赐教,陛下对我这堂弟,是如何处置法?”
“杀!”
李牧笑眯眯地说出这个字,更让卢氏胆寒。她从李牧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满不在乎,仿佛杀一个人对他来说,如同杀鸡一样简单。
卢氏不甘心道:“只杀他一个?”
“陛下仁慈,自然是只诛首恶了。”李牧笑道:“谁让他是民部侍郎呢?居其位而不谋其政,能管而不管,坐视粮价上涨,这样尸位素餐之人,死有余辜不是么?难道您觉着,他不当死么?”
没等卢氏说话,李牧又道:“他要是不当死啊,那死的人可就多喽。我相信卢侍郎是个轻生重义之人,若他知道死了他一个,可保数十人,想必他也是愿意甘心赴死的吧?”
“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