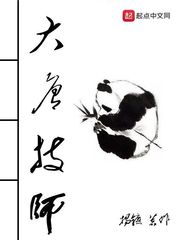大唐技师 !
长孙无忌闻听此言,顿时笑了,道:“伯施过滤了,李牧不是这等卑劣的人,他做事虽然孟浪了些,但却有一定之规。你看魏公得罪他多少次?他也没报复过魏公,足可见此子是一个心怀坦荡之人,不会罗织罪名,陷害忠良的。”
虞世南还要说话,被长孙无忌打断,道:“再说你与他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何要找你麻烦呢?若论书法,我若记得没错,欧阳询没有承认他这个徒弟,只说他是自悟的,也算不得师承,不要杞人忧天了。”
虞世南叹息道:“只怕他会把我视为山东士族。”
长孙无忌笑道:“伯施啊,你太过于忧心了。山东士族也好,河朔英豪也罢,重要的不是出身,而是态度。心向陛下,心向朝廷,什么出身都没有关系,但若心里头想的是其他——出身何地,都不能幸免。
虞世南脸色变了变,不自然地笑道:“国舅所言极是,我深受皇恩,自然是心向朝廷,心向陛下。”
“那就无碍了,没有必要忧虑。”
正说着话,忽然帐外一阵骚动。长孙无忌和虞世南来到门口,侧耳偷听,是一个校尉。他刚刚从审讯的树林回来,与袍泽闲谈,声音没有刻意压低,夜色静谧,几乎附近的人都能听见。
“……审出来一个了,嘿,猜猜此人是谁?竟是太原王氏嫡长房子弟,侍中王珪的亲侄子!”
“……呀,那侍中大人得保他吧?”
“保?”校尉嗤笑道:“陛下遇刺,行刺者竟是侍中的子侄?他能脱得了干系?你们忘了,侍中曾是隐太子麾下,任太子中舍人,乃是绝对的心腹!保不齐就是他卧薪尝胆,伺机刺杀陛下,想为隐太子报仇呢!”
长孙无忌和虞世南听得清楚,俩人的脸色都有些变了。事情若牵扯到玄武门那件事,就不是随便能够了解的了。龙有逆鳞,触之必死。若此事坐实,王珪必死,太原王氏也要脱一层皮。
就在校尉要继续分析的时候,程咬金从远处走过来:“瞎说什么呢?这也是尔等可议论的么?想活命闭上嘴巴,再说没用的,老子割了你们的舌头去!”
校尉被呵斥,不敢再说,声音渐无。
程咬金走了过来,长孙无忌忙拉着虞世南后退,二人还未来得及说一句话,就听隔壁军帐穿过来程咬金的声音。
“唉……事情犯了,你的侄子已经招供,我也不好多说什么。王侍中,跟我走一趟吧。”
王珪呆傻了,魏征帮忙说话道:“程咬金!你莫要污人清白,老夫绝不相信此事是叔玠授意!我要见陛下,我要见陛下!”
程咬金冷笑道:“魏公,别跟我在这儿大喊大叫的。你跟我说不着,我就是个跑腿的人。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审讯,是锦衣卫与厂卫一起审的,一边是李牧的人,一边儿是高公公的人,你要是觉得不公平,找他俩说去。不过,我是觉着没有什么必要了。王家那小子,我都曾见过,一年前来长安,在弘文馆读书,满脸的横肉,底细太清楚了,想抵赖都不成。”
王珪才反应过来,喃喃道:“你说的是王志?是他?”
“好像叫这个名字吧,我也没记住。”程咬金做了个请的手势,道:“侍中想必心里有数了,那就跟我走吧?实话跟你说,你想去不想去,你也得去,何必逼我动粗呢?”
“不行!”魏征拦在王珪前面,他俩曾同为李建成心腹,多年的交情,虽偶有嫌隙,但终是比其他人要关系近一些,重要的是,魏征是真的不信此事会是王珪所为,他认识王珪二十年,不信王珪有这样的胆子!
程咬金不给魏征说话的机会,伸出熊掌一样的大手,一下就把魏征抡出去两米,冷哼道:“魏征,你自身难保,还有心思管别人?活口还有五个,天亮之前,一个个都得招了,若是有一个跟你有牵连,下一个抓的就是你!敢行刺陛下,好大的狗胆!陛下龙颜大怒,这回谁也救不了,五马分尸都是轻的!”
魏征从地上爬起来,瞪眼睛喊道:“我要见陛下!”
“陛下伤重,正在休息,没功夫见你们这些乱臣贼子!”
程咬金丢下一句话,拽着王珪的胳膊,把他拖出了军帐。他是李世民的嫡系,秦王府的猛将,而王珪与魏征一直都是太子府的人,两边势同水火多年,早就互相看不顺眼,梁子一直都有。只不过在李世民登基之后,为了平衡朝堂势力,刻意压下了。如今出了这种事情,不落井下石就已经算好的了,哪还有客气的道理?
王珪面如死灰,来的路上他就有所预感,只是不愿意相信,心里还有一丝侥幸,期盼着不会是自己的那个傻侄儿。没想到天意弄人,越不想发生的事情,偏偏就发生了。
王珪心道一句吾命休矣,身上一丝力气都没了,被两个士卒拖着走,靴面都磨破了。
其他军帐中的人看到王珪的惨状,纷纷紧张了起来,虞世南更是吓得面如土色,他是真的不敢保证,那里头有没有他的子侄。关键是这玩意也看不见,话语权都在人家的手里,明明不是,楞说是也没辙呀!
士卒拖着王珪走在前面,程咬金走在后头,路过长孙无忌的军帐时候,程咬金忽然站住了。
“国舅安歇了么?”
长孙无忌示意虞世南不要说话,回应道:“还未安歇,知节有事?”
“李牧小子托我请国舅过去,有事相商。”
长孙无忌犹豫了一下,没有动弹,道:“待罪之身,不便相见。请代为转达,还是审完了刺客,解除了嫌疑后再见吧。”
“李牧小子说,若国舅也是刺客同党,大唐就算是完了。他愿意相信国舅,还是请国舅见一面。”停顿了一下,程咬金又道:“他还说了,国舅若是不去,恐怕会后悔。”
长孙无忌还在犹豫,虞世南小声鼓动道:“国舅还是见一见吧,那小子——逐鹿侯能如此信任国舅,是好事啊。若能见到陛下,请国舅帮忙美言,我真的是无辜之人啊!”
长孙无忌微微颔首,起身来到帐外。程咬金往帐内瞧了眼,道:“帐中还有其他人?”
“没有。”
程咬金也没有细究,让亲卫牵过一匹马来,道:“请。”
长孙无忌道谢后上了马,跟随前头徒步而行的王珪,一道去见李牧。
……
树林内。
在三狗手里过了两遍的王志,被两名狱卒搭起来,按着跪在李牧面前。
李牧瞧了眼,见他也没多少外伤,但整个人却像是脱水了似的,连眼睛都睁不开了,不由心里非常好奇三狗是怎么整的,着实是有点道行。
“杀了我吧……”
“不不不,不杀人。”李牧附身看向王志,微笑道:“实不相瞒,我与牡丹夫人……我俩呢,是好友。你叫王志是吧?算起来是她的堂兄?既然是有亲,那就好办,我这人最重视亲情,你把背后主使之人告诉我,我就放了你,如何?”
王志抬起头看向李牧,忽然冷笑了一声,道:“你当我是三岁稚童么?会相信你的鬼话?没人指使我,就是我想杀你!我还不妨告诉你,我想杀你,除了这次的事情,还有……”
没声了,李牧等了半天,皱眉喊道:“三狗,三狗!咋没声了,死了?”
三狗颠颠跑过来,把手指伸到此人鼻下试了试呼吸,回头示意了一下自己的小弟,小弟拎过来一桶水,直接从王志的脑袋顶上浇了下去。
这水都是凿开河面打上来的冰水,混合着冰碴子,冷得令人发指。这一桶下去,王志登时清醒了,怒视李牧,破口骂道:“李牧,你有种就杀了我,否则等我脱困,我必把你与王鸥的丑事公开,让天下人都知道,你二人是何等的男盗女——”
“啪!”
李牧甩手就是一巴掌,扇飞了王志的两颗牙,打得他满脸是血。
王志一歪头,很快又梗着脖子扭回来,看着李牧,吐了嘴里的血,道:“被我戳穿了,挂不住脸了吧?李牧!敢做不敢当?你这个乡野村夫,目无礼法,竟勾搭寡妇!你还要不要脸!太原王氏,绝对不允许此等丑闻发生,我要杀了你!我还要杀了她!你们都得死!全都得死!!”
“唉……”李牧长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还真是厌烦,本来真的想留你一命了,可惜啊,你这张嘴,是真的臭。”
三狗揣摩李牧的心意,眼睛一亮,从怀里抽出一把匕首,看向李牧,李牧刚要点头,忽然余光瞥见王珪被带了过来,摇了摇头,对三狗使了个眼色。
三狗从怀里拿出一份供词,拽过王志的手,用匕首在他手掌划了一道,鲜血流出来,用他另一只手,沾着鲜血,在供词上按了手印,随后拿东西堵住了他的嘴。
这时王珪来到跟前,看到跪在地上的王志,借着火把的光亮仔细辨认了一番,确认是他,脸色更加灰暗了。
王珪瘫坐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王志奋力挣扎,想要把嘴里的东西吐出来,告诉王珪一些事情,但他被两个狱卒按着,一动也动不了。
李牧挥了挥手,有人搬来一把椅子,三狗把王珪扶起来,让他坐在椅子上。
李牧揉了揉脸,叹息道:“侍中……算了,大家都这么熟了,我称呼你一声老王,不会生气吧?”
王珪苦笑一声,道:“事已至此,侯爷何必挖苦。”
“这么说,你便是承认了,你是行刺的幕后主使之人了?”
王珪虽然万念俱灰,但心里头却比什么时候都明白,此时若他若承认了,对太原王氏来说,就是灭族之祸。他深吸了口气,坐直了身体,看向李牧,一字一句道:“侯爷,我说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是我必须得说。此事,我一点也不知情!”
李牧笑了,指了下王志,道:“那这个人,你也不认识了?”
王珪看向王志,叹了口气,道:“此人,名叫王志,确是太原王氏子弟。”
“那我就不明白了。”李牧摊了摊手,道:“你说此事你不知情,却又承认此人是太原王氏子弟,什么意思?他吃饱了没事儿干,一拍脑袋,就想行刺陛下?你们太原王氏的子弟,都是这么潇洒自如么?”
王珪无话可说,低头道:“侯爷,事已至此,我实在是不知如何辩解。无论如何,此子是太原王氏的人,王珪管教无方,愧对陛下,愧对天下,愿以死谢罪,只求侯爷不要株连,太原王氏必世世代代感激侯爷大恩大德!”
说着,王珪便要跪下。李牧赶紧示意三狗拉住他,王珪这老家伙都七十多了,他可不想折寿。
李牧看着王珪泪流满面的样子,心里也是十分难受。都是为了自己的家族,其实细想想,也无可厚非。
李牧叹气连连,道:“老王啊,你说,我分明已经暗示过你了。就一点钱财,你们几家商量商量,给我一个面子,也给陛下一个面子,对不对?这次你们帮了忙,我还能亏待你们么?若有机会了,内务府多给你们两个订单,也就把亏空补了,大家都欢喜,多好?你说你干的这叫啥事儿?还搞起了刺杀来?”
“刺杀也就刺杀了,你们好好调查调查,派几个机灵的选手,是吧?你说你们派的这几个人,好像都没脑子一样,刺杀的时候就不调查调查,把陛下也稍待上了,你说这事儿弄得,多尴尬呀!”
王珪百口莫辩,急得脸红脖子粗:“侯爷,冤枉啊!我没有想过刺杀你,我更没有想过刺杀陛下!我对你的事情,一贯都是支持的。不信你去打听,当日我是极力主张大家凑钱度过危机,根本就没作他想,听到行刺这件事的时候,我和魏公正与侯君集商量价码,若我有其他的心思,怎会如此大费周折?”
李牧拧着眉头,幽幽道:“那可不一定,也许是故意为之,想解脱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