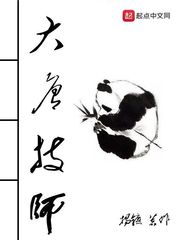大唐技师 !
从屋里出来,李牧来到柴房,阴影处站着一个影子。
李牧生火煎药,影子站在他身后,说道:“夫人在慈恩寺见过袁天罡。”
“是袁天罡约见夫人?”
“尚不知晓。”
“查!”
“嗯!”影子应了一声,消失不见。
倒不是李牧在怀疑白巧巧,只是事出反常,太过奇怪了些。白巧巧是李牧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人,容不得半点差池。李牧一直把白巧巧保护得很好,不想让她沾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现在竟然有人打她的主意,这是李牧绝对不能允许的。
刚刚那个影子,便是李牧让独孤九挑选出来的那一批特殊的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犯下了大罪,无法行走在阳光下的人,所以哪怕在李牧面前,他们也不以真面目示人,这是李牧定下的规矩,为的就是让他们能够放心地效力。等他们完成了承诺的事情,锦衣卫也会给予承诺的他们的东西,或是保他们的妻儿一世富贵,或是给他们一大笔钱让他们远走高飞,又或是动用锦衣卫的力量,帮他们复仇。
就像是一场交易,非常的公平。
这个负责保护白巧巧的人,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功夫,独孤九亲自试过,百招之内,二人不分胜负。得过一百五十招,才会败在独孤九的快剑之下。
这样的手段,已可纵横江湖。有他在,李牧对白巧巧的安全,还是非常放心的。但有话在先,他只负责白巧巧的安全,其他的事情,他不会出手,也就是说,即便白巧巧做了害李牧的事情,他也不会阻止,因为他的这张订单里头,没有那一项。
李牧不担心白巧巧会做伤害他的事情,他只是担心,白巧巧会被袁天罡利用。
药煎好了。
李牧端着要回到房间,金晨和张天爱也都回来了。三个女人正在叽叽喳喳地聊着什么,见李牧端着药回来,二女忙问是谁得了病,得知是安胎药,俩人才放了心。张天爱便要接过药碗来喂给她喝,白巧巧哪里敢让她喂,毛毛躁躁的,喂十口还不得撒八口去,还是金晨接过碗来,轻轻柔柔地喂给了白巧巧。
李牧也插不上手,便来到门口,坐在了门槛上。张天爱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李牧歪过头去,她却坐到了另一边儿:“多大的孩子,还坐门槛儿,也不怕让人笑话?”
李牧笑了笑,拉过张天爱的手,轻轻地握在了手里。
女子属阴,多体寒,手掌也是凉的,但张天爱从小习武,她的手一直都很温暖,而且很有力量。这一点和李牧的其他女人都不一样,白巧巧的手,软而绵,到了张天爱这儿,他有时候甚至会担心被张天爱把骨头给握碎了。
“夫君,你看什么呢?”
“在看天上的星星啊。”
张天爱靠在李牧的肩膀上,看了一会儿,没看出什么来,觉得没意思,起身回屋聊天去了。李牧却仍看着天上,像是在等着什么似的。忽然,黑色的天空,闪过一点儿迷蒙的光影,暗卫的热气球从上空掠过,李牧的目光随着这团影子远去,目光深邃,不知在想些什么。
……
次日清早,李牧受侯君集的邀请,去了一趟东城的兵工厂,午间,正打算吃侯君集一顿,宫里来人,宣他入宫。
“陛下,臣来了,还没吃饭,有没有现成的搞点,搞一点来吃啊。”李牧进了殿,也不拿自己当外人,旁若无人地嚷嚷着,嚷嚷完了,才发现殿内有人,还都是熟人。有昨天刚见过的玄奘法师和小和尚一休,还有有过一面之缘的小和尚的师父,会医术的那个惠日和尚,还有一个长着一撮小胡子,看起来就像是个小偷的猥琐中年人,看他的模样,也不难猜测,他应当是倭国遣唐使的正使,犬上三田耜。李牧依稀记得见过他一面,但记忆有些模糊了。
除了这几个人之外,魏征也在。李泰和李承乾兄弟两个,也束手立在一边,高公公和几个小太监在旁边伺候着,人还真不少。
“给他拿点桂花糕来。”李世民对高公公示意了一下,高公公忙叫小太监去取糕点,顺带给李牧搬了个锦墩。这一屋子的人,除了李世民之外都站着,李牧坐下了,显得尤为乍眼。但是却没一个人觉得不妥,李牧的不妥之处太多了,这等小事,已然没人在意了。
小太监端来一盘桂花糕,站在李牧身旁伺候,双手托着盘子纹丝不动,李牧伸手拿了两块放进嘴里狼吞虎咽,他已经饿得不行了,哪里顾得上什么礼数了,一边吃一边含混不清道:“陛下召臣过来,可是有什么急事么?”
“事情倒是有几件,你快吃两口,吃完细说。”
“没事,臣吃东西也用不着耳朵,陛下说就是了。”
李世民瞪了他一眼,道:“先说和尚事,这位玄奘法师,你可认得?”
“认得认得,昨天刚见过。”李牧吃噎着了,也不等李世民赐茶,自己拿着桌上的御盏便喝,李世民只当做没看见,继续说道;“玄奘法师,不仅佛法精深,更是难得的通晓番邦文字的大才,朕与他谈论,诸多见解,颇有茅塞顿开之感。与凡俗之流不可比拟,当敬重之。”
“嗯嗯、”李牧含混地应了声,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李世民正要申斥,玄奘忙道:“陛下,洛阳侯对佛法的见解,贫僧不能及,请陛下万勿责备,贫僧羞杀也。”
李世民一愣,道:“法师这是——”
“贫僧方才提及之事,正是受到了洛阳侯的点拨。”
“点拨?”李世民顿觉奇怪,他早就知道玄奘的名声,说是佛教百年不出的人才也不为过,这样的大才,李牧如何点拨他?按下心中疑惑,李世民清了下嗓子,说出了正事儿:“玄奘法师说,这世上有大乘佛法与小乘佛法,大唐僧人之所以堕落至此,是因为他们只学了小乘佛法,而没有学到大乘佛法,他愿意去那烂陀寺求取真经,来向朕求通关度牒,此事你觉得可行么?”
李牧明白李世民的意思,前几天,李牧刚在慈恩寺搞了一回事,玄奘此时又说起取经,多少有点像是跟李牧掰手腕的意思,而李世民这边呢,帝王之术在于平衡,给一棒子之后,通常都要给个甜枣吃,他有意答应,却要顾及李牧的面子,所以问他的意见。
“那烂陀寺?”李牧心道,不应该是大雷音寺么,怎么成了那烂陀寺?这个寺可没听过,他看向玄奘,玄奘忙躬身施礼,道:“贫僧昨日回到证道院,与诸位大师谈及此事,均一致认为,若这世上存在大乘佛法,必在那烂陀寺。所以贫僧要去那烂陀寺,求取真经。”
“为何一定是那烂陀寺?”
玄奘见李牧不知道,便解释道:“那烂陀寺乃是佛教圣地,此地原是庵摩罗园,后有五百商人捐钱买下献佛,佛在此说法三个月,教化世人。后摩揭陀国王铄迦罗阿迭多在此兴建佛寺,子佛陀鞠多王在寺南扩建,呾他揭多鞠多王在东面建寺,幼日王在东北建寺,金刚王在此西建寺,中印度王在此北建寺,帝日王此东建大寺——”
“停停停、”李牧听得头都大了,印度人的名字怎么没个正常的,他懒得听了,看向玄奘,问道:“法师可听过‘大雷音寺’么?”
玄奘一愣,道:“倒是不曾听过,大雷音寺,难道大乘佛法在大雷音寺?”
李牧心道,西游记里头就是这么写的,说出来也不算是骗你,李牧清了下嗓子,道:“好像记得有这么个名字,却不知在哪里,法师可以打听打听。”说完,他看向李世民,道:“陛下,既然法师有普度众生的心,朝廷也应当支持才是。只是臣有一个捎带脚的小请求,还望法师能够答应。”
李世民看向玄奘,玄奘忙道:“施主请讲。”
“请问法师,此行是怎么个走法,是往南还是往西,走水路还是走陆路。”
玄奘答道:“佛法自西而东传,想要寻到那烂陀寺,打听出大雷音寺的所在,必是自东而西,贫僧往西边走。”
“好!”李牧听到玄奘这样说,心里有了计较,道:“实不相瞒,我的老家,便是在西边,小时候常常见到从西边来的胡人和波斯人,听说过沙漠更西的故事,心向往之,却一直未能成行。既然法师西行,必然是要路过这些地方,还请法师将沿途一路的风土人情,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下来,待法师回转之时,借我看看,我便也如同亲眼所见了,不知法师能否满足我这个小小的愿望。”
“啊,贫僧还当是什么事。”玄奘出了口气,道了声佛号:“这点小事,贫僧自无不允之理。施主请放心,贫僧每到一地,必细细记录当地所见,务求仔细,让施主知晓。”
“如此,便谢过法师了。我会准备一份心意,供法师路上花用。”
玄奘忙道:“贫僧此番西行,乃是一颗拜佛求经的诚心,必得是真心苦行,方可取得真经。若是一路悠哉享乐过去,便是不遵三宝,不敬佛祖,菩萨也说了,这样是取不到真经的。”
李牧也不强求,道:“也好,那我就仿照梦中的样式,做袈裟与锡杖赠给法师,法师若再拒绝,便是真的半点情分也不讲了。”
话说到这地步,玄奘还能说什么,只好答应下来。
李世民对和尚的了解,要比李牧多多了。他见玄奘不肯要李牧给的路费,便知道他是打算一路化缘过去。化缘总得有个家伙事儿,便又许了一个钵盂给他。御赐的钵盂,玄奘怎敢拒绝,也一并收了下来。
打发了玄奘,接下来便是遣唐使的事情了。倭国的正使犬上三田耜已经被礼部晾了半年,头发都白了一半儿,昨日得到口谕,说是今日召见,顿有一种太阳打西边出来的感觉。兴奋得整宿没有睡着觉,到现在眼睛都是布满血丝的。
李世民昨天也琢磨了很久,如何能够得到倭国的大银矿。白银这东西,没法糊弄,倭国虽然不知晓他们有那么大的银矿,但若知晓了,肯定也不会轻易地献出来,毕竟谁不知道白银是‘钱’呢、他们一定有所图,李世民召见遣唐使,便是想知道他们要什么,看看能不能商量出来一个对大唐相对有利的交易。
至于打,李世民冷静下来之后,倒是没想过了。他虽然对海路了解不多,但也知道倭国位于东海,在李世民的意识中,离岸的岛屿,都不值一提,一块飞地而已,大费周章地去打,得不偿失。
“你国国王派尔等过来,所为何事啊?”
李世民的态度颇为傲慢,实则也不能算是傲慢,这就像是一头猛虎在与一只哈巴狗在对话,即便猛虎已经拿出最和蔼的姿态了,在哈巴狗的眼里,还是吓人可怖的。
“舒明天皇使臣犬上三田耜参拜天可汗大唐大皇帝陛下,请收下我国国书。”
“天皇?”李世民的眼皮耷拉了下来,李承乾、李泰、魏征等人的脸色都不好看了。小小番邦蛮夷之地的国王,也敢自称‘天皇’,都说这倭国人狂妄而自大,如今看来果真是如此。
李牧察言观色,瞧见李世民不悦,登时暴怒,他抓起小太监拿着的糕点盘子,扣到了犬上三田耜的脑门上,骂道:“小小倭国使节,也敢在我大唐皇帝陛下面前放肆?天皇?你们也配,不怕折寿么?”
犬上三田耜吓得赶紧跪在地上,不敢把头抬起来,求饶道:“说错了,说错话了,是倭国国王,不是天皇,不是天皇!”
“你明明说了,还不认?看来是个巧言令色,油嘴滑舌之人,好呀,耍嘴耍到皇宫里了,本侯岂能容你?来人,把他的舌头割了!”
“侯爷开恩,下国岂敢有对大唐皇帝陛下不敬的意思。只是一个称呼罢了,大唐皇帝陛下如何称呼,下国就如何接受,这样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