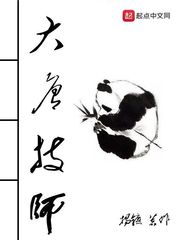大唐技师 !
窦仁哭了,叫道:“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说吧,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求求你不要让我再闻这、这狗屎的味道了!我要死了!”李牧见他实在也是可怜,便伸手去解绳子,恰在此时,窦仁竟然玩命的挣扎,绳子将揭开还未解开的时候,他这么一挣扎——
“啊……”
李牧一阵恶心,哇地一下也吐了。
……
窦仁洗了三遍澡之后,终于肯出来跟李牧相见了。他在袖子里放了一把匕首,琢磨着等会儿,待李牧不备的时候,拔出匕首杀了他。刚刚从梁上掉下来,搞得他满头的狗屎,这番耻辱,他此生都不会忘记,非得杀了李牧,才能一解心头之恨。
迈步进了书房,窦仁心中更气。只见李牧坐在桌案之后,一本正经地在读春秋。仿佛此间的主人,不是他窦仁,而是他李牧一样。早就听闻这小子狂妄,没想到竟然是这般的狂妄,就算是皇帝陛下驾临,碍于辈分,也断然不会对他做出这么无理的事情来,他怎么敢——
难道、窦仁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可能性,难道是自己的行径,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碍于亲情,不好出面,所以把李牧打发来敲打自己?
窦仁很明显是想多了,他这号人物,在李世民的脑袋里出没出现过都两说,李世民怎么会派李牧过来专门对付他。但痴人就算这样,就算此时有人点醒他,他也不会明白,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是个种子一样,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窦仁在门口徘徊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咬了咬牙,把匕首从袖子里拿出来,左右瞅了瞅,丢到了一旁。再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依旧堆满了笑容:“逐鹿侯这是在看春秋?我也喜欢看,就放在桌案之上,方便随手翻阅,春秋左传,微言大义,大义——”
李牧抬头看了眼他,把春秋丢到一边儿,露出了里面的小画册。空气瞬间尴尬了起来,窦仁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他心中暗想,这东西自己藏得很仔细的啊,怎么就被他给看见了呢?而且他是怎么知道,自己惯于把这些小册子包裹在春秋之中看呢?难道他在我的府中,备有眼线?
早就有耳闻,说是皇帝陛下,有一个监察天下的组织,称之为‘不良人’,莫非这不良人,早已经渗透在了我的府邸之中?
想到这些,窦仁觉得自己的脖颈有点儿凉意了,窦仁深吸了口气,抬手擦拭了一下额头的冷汗。
李牧只看到窦仁的脸色不断的变化,哪儿能猜到他心里想什么。他多少有点为刚才的事儿抱歉,正犹豫要不要表示一下歉意,突然,窦仁扑通跪了下来!
“这是做什么?”李牧有点懵,但他没有说话,静观其变。
窦仁哭道:“侯爷,我知罪。我嚣张跋扈,我顽劣不堪,我穷奢极欲——可是,可是我真的没做啥太大的坏事儿啊。那些女子,她们都是我买来的,有卖身契为证,逼良为娼的事儿我可没做过啊,即便是我过分了些,我琢磨着也用不着尚方宝剑——”
“原来他误会了。”
李牧没想利用这事儿,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陛下没说过你什么,我今天来找你,纯粹是因为我看你不顺眼,我心情不好,我就想找你撒气——”
窦仁哪里肯信:“侯爷,你不用掩饰了,陛下到底是怎么发落我,你直说了吧。”
李牧斜楞眼睛看着他:“咋,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有点瞧不起我啊?非得陛下处置你我才敢来,我自己就想揍你不行?”
“侯爷,我都猜出来了,你何必再掩饰呢?”窦仁急道:“你说这样的假话有必要吗?就想揍我?你怎么那么大的胆子?我可是皇帝的亲娘舅,太上皇封的寿阳侯,论爵位我可不比你低,论亲戚我更是远超过你,你凭啥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来我家欺负我啊?”
“说得好!”李牧站起来指着窦仁道:“想不明白是吧?想不明白就对了,我也想不明白陛下为啥欺负我,我看起来好欺负么?今天我欺负你,就像陛下欺负我是一样的,没有原因,我想欺负你就欺负你,我就来你家揍你怎么地了?我还告诉你,我的爵位已经被罢黜了,我现在也不是什么侯爷,我就是一个洛阳令——”
“啊?”窦仁蒙了,他观察着李牧的脸色,见他不像是在撒谎,突然就有了一种转身去把匕首捡回来的冲动,他愤然站起来,指着李牧骂道:“你就是一个洛阳令?哈,疯了不成,小小洛阳令,你敢在本侯的头上拉屎?信不信我把你剁了,我也一点儿事儿都没有,来人啊!”
甲胄摩擦的声音响起来,窦仁身后出现了一群人。
“给我把他抓起来!”
没人理会,窦仁回头,看到了苏定方的脸。他的表情僵了一下,想起来现在的处境了,是李牧带人劈了他的府门进来的,现在这府邸,已经被他控制了。
嘴唇颤抖了一下,窦仁强忍怒意,道:“你年纪轻轻,怎么做这种疯癫的事儿啊,这样,你现在退出去,我、我大不了不声张,咱们只当今日的事儿没发生,你看如何?”
“不如何,也不咋样!”李牧勾了勾手,苏定方走过来,递给他一把匕首。窦仁见了,脊背发凉,这匕首正是他扔掉的那个,没想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落在了人家的眼睛里。
李牧把匕首拔出来,银芒闪闪,他招了下手,几个校尉把窦仁掳过来,把他的手按在了桌案上。
李牧抓起匕首猛地一插!
窦仁吓得嗷嗷叫,连声道:“活祖宗,我错了,你到底想干什么!”
“服了么?”
“服服服,别伤害我!”
李牧把匕首丢到一边儿,换上一张笑脸儿,道:“也没啥旁的事儿,就是想让你替我写几封帖子。借你的府邸摆个席面,小弟初来乍到,还是得认识认识这洛阳地面的地头蛇,你说呢?侯爷。”
“是……”窦仁被李牧这两次三番的吓唬,已经有点破了胆,脸色煞白,半点儿也不敢再顶嘴了。
……
长安。
李牧走了之后,朝堂之上果然平静了许多。这种平静和李牧离开的时候那种平静不同,李牧离开的时候,虽然朝堂上也很平静,但各方势力在做事情的时候,总得想着,一旦李牧回来了,他会不会翻旧账,面对李牧的手段,应当如何应对。有时候想一想,应对起来太过于麻烦,多半也就放弃了。
但是现在,李牧去了洛阳,他很可能再也回不到朝堂上,行事自可无所顾忌了。李世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心里多少有些不舒服。他恍然发现,自己压制不住的这些门阀啊,勋贵啊,对李牧的忌惮,竟然比对他这个皇帝的忌惮还要多些。
李世民忽然想起了尚方宝剑,尚方宝剑给了李牧,李牧去了洛阳,李牧对自己来说,无异于就是一柄悬在这些勋贵头上的尚方宝剑,有他在的时候,即便不用,这些人也会忌惮。
自己是皇帝,他们当然会怕。但皇帝毕竟是皇帝,皇帝不可能亲自下场肉搏厮杀,很多事情,反而畏首畏尾了。
“禀陛下,吐蕃王子请求和亲一事,还请陛下定夺。”礼部尚书虞世南站了出来,举起笏板恭声说道。
李世民看着他,心中有些厌恶。这几次的风波,虞世南都平稳的度过了,仍然留在礼部尚书的职位上,但是这老小子,并没有感恩戴德,反而是因为王珪、长孙无忌的相继落马,开始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了,这吐蕃王子请求和亲的事儿,李世民已经明确拒绝过一次了,但他还提出来,隐隐地有想看笑话的感觉,让李世民颇为不喜。
“公主们都不满十岁,爱卿的意思是,让朕嫁个幼女给吐蕃王子?”
虞世南并不起身,道:“陛下,臣有两个办法,请陛下斟酌之。一,可先应下吐蕃的和亲,但告知对方公主年纪尚幼,故大婚可在及笄之后成行。二,可在皇姑之中择选适龄女子。”
“不可!”说话的人不是李世民,而是魏征,魏征怒视虞世南,道:“两个办法都不可行,前者,大唐与吐蕃是战是和,如今还未有定论,前些日子,吐蕃也有参与围堵,这件事还没跟他们算清,此时应允和亲之事,会让人觉得大唐软弱可欺。而从皇姑中择选,更加不妥。皇姑与陛下乃是同辈,吐蕃王子若是娶了皇姑,岂不是与陛下同辈?泱泱大唐与吐蕃成为了同辈,叫天下人嗤笑么?陛下为天可汗,吐蕃王子岂不是成了‘地可汗’,虞世南,你是老糊涂了?”
“魏公,你这样说话多有不妥吧,我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是否采用得陛下来说,这是我的职责所在,即便是不妥,礼部的事情,也轮不到你御史台指手画脚!”虞世南不客气地回顶过去,魏征皱起眉头,便要与之理论。李世民看着斗鸡般的二人,心中又开启怀念起了李牧,若李牧在,这种事儿,还有虞世南这等人说话的份儿么?
魏征虽然言辞犀利,但他的辩论,达不到李牧那种爽快的感觉,若李牧来怼虞世南,保准他连话都说不出来。这点信心,李世民还是有的。
“不要吵了!”李世民打断了二人,对虞世南道:“魏爱卿的话,与朕不谋而合。吐蕃对大唐不恭,事情还没有了断,此时答应和亲,显得大唐软弱可欺。断不可行,皇姑的驸马,朕做不得主,得太上皇点头才行,此事就此作罢,不用再议了。”
“陛下!”虞世南又站出来,道:“陛下三思啊!此事不仅仅关系到两国邦交,还有陛下加冕天可汗的事情。陛下,天可汗者,天下共主也,若四夷不服,日后史书之上,怕是不好看。后世史官品评时,难免会觉得陛下这‘天可汗’有伪造之嫌疑。答应和亲,不仅能够让两国重获和平,还能促成吐蕃拥戴大唐,拥戴陛下,如此一举两得的事情,陛下三思啊!”
“这……”李世民听到这话,有些犹豫了。
吐蕃与大唐是战是和,李世民确实不怎么放在心上,因为在他的计划中,吐蕃是早晚要打的。但眼下加冕天可汗在即,吐蕃的支持,对他来说非常重要。所谓天可汗,不是随便说说的事儿。而是真正要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才行,小国自不必说,它们就算不认可,也没有关系。但是几个大的,例如吐蕃,吐谷浑,突厥,薛延陀,高句丽等,若是不承认,这天可汗难免就失了很多成色。
“陛下,断然不可答应!”魏征站出来与之针锋相对,道:“国与国之间的较量,当以实力为准。若用公主来换取吐蕃的拥戴,其他国家看了,就一定会效仿,今日吐蕃王子,明日高句丽王子,后日薛延陀大可汗,陛下哪有那么多公主用来许诺?此例一开,后患无穷,陛下绝对不能够答应啊!”
“陛下三思!”
“陛下绝不能答应!”
礼部和御史台的人齐呼,李世民的脑袋瞬间大了三圈儿。他看向高公公,差点脱口而出去把李牧给朕找回来。忽然,他看到高公公在挤眉弄眼,眉头蹙了起来,心中奇怪,难道李牧回来了?否则挤眉弄眼是作甚?
高公公没办法了,只好凑到李世民耳边,小声耳语道:“陛下,刚刚收到消息,出事儿了。”
“什么事?”李世民凝眉道:“李牧那小子惹事儿了?”
“嗯!”高公公小声道:“他把寿阳侯绑了,占了他的府邸。”
“谁?”李世民愣了一下,没想起有寿阳侯这么个人,呆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寿阳侯是他的亲娘舅,一下子站了起来,怒道:“你说他绑了谁?他绑了朕的舅舅?”
百官忽然听到李世民这么一嗓子,都有些茫然,什么绑,谁绑到皇室的头上了?
不过,怎么听起来有点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