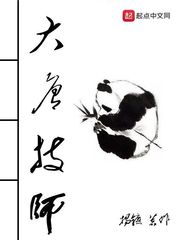大唐技师 !
李牧都这样说了,长孙无忌还怎么好意思让他花钱。李牧‘争’不过,只好把这个‘付账权’让给了长孙无忌。
正好也快到晌午了,一行人便乘坐马车,直奔天上人间。从逐鹿侯府出来,长孙无忌的脸就有点黑了。李牧是真撂得下去脸啊,说是阖府欢庆,还真就是阖府出动。也不知他从哪儿雇的车,把门房和丫鬟都带着,浩浩荡荡地开向了天上人间。
到了天上人间,长孙无忌的脸色更难看了。因为他发现,李牧请的人也太多了。王珪、王普、独孤修德、高士廉、尉迟环、李应、崔永仁等人都在,基本上大唐矿业和大唐盐业的股东全都来了。还有昨日去‘探病’的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都请过来了。
这得多少钱?
天上人间的宴席,最便宜的也得十贯钱一桌,还不包含酒水。放眼望去,乌泱泱全是人,少说也得八桌以上。连吃带喝,还不得个三四百贯?
合着不用你花钱,你就这么坑人是吧!
长孙无忌强忍着没有发作,打算先去给李渊请个安。先不说到了李渊的地方,作为晚辈应该请安。他得让李渊知道,这顿饭是谁花的钱,不然这几百贯可死的太冤了。
长孙无忌正要上楼,突然轮椅拦在了他面前。长孙无忌看到李牧,饶是他的养气功夫再好,被摆了一道,心里也难免不舒服,但还是带着笑容,道:“我正要去给太上皇请安,怎么,有事么?”
“不不不,不是我有事。而是我看国舅爷脸色似乎不太好,是否是因为小子请的人太多了?这倒是小子的疏忽了,小子本来是打算自己请客,庆贺收徒大喜。国舅爷也知道小子的行事风格,视金钱如粪土嘛。多花点,少花点,我根本不放在心上。却没有想到国舅爷非得抢着要结账,小子争不过,又没法把去请客的人叫回来,于是就出现了这尴尬的一幕。若不然这样好了,咱们这一桌,算是国舅爷请,其余的人,我来请。国舅爷以为如何?”
真够损的!
长孙无忌心里暗骂,这小子一肚子坏水。你不情愿收我儿子为徒,就处处拿话挤兑。我若是按你所言,岂不是被你拿住了话柄?罢了罢了,几百贯钱而已,虽然肉疼,但也不是花不起!
长孙无忌挤出一个笑容,道:“我虽然没有达到你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但也不差这一顿饭钱。高朋满座,乃是幸事。既然说好了由我来花钱,你就不要再争了。”
“唉、”李牧叹了口气,道:“没想到,除了我之外,长安城中还有如此慷慨之人。”他回头看了眼旁边的小陈公公,道:“陈经理,看到没有,听到没有,国舅爷吩咐了,这顿饭他请客。国舅爷显然是不差钱的人,什么好酒好菜,全都给我上来。尤其是平日里没人点,不敢点的那些贵菜,有一道算一道,通通上来。不求好吃,但求最贵。国舅爷请客,排场要足。我记得咱这天上人间不是还排演了歌舞么,也安排上,今日本侯收徒大喜,一定要做到宾至如归!”
小陈公公自然是认得长孙无忌的,也听得出话音儿,李牧这是在坑他。若搁在从前在宫里的时候,小陈公公或许会犹豫一下,但如今他是天上人间的经理了。天上人间的生意一直不怎么好,可逮到一次‘大活儿’,岂能放过?坑谁都是坑,反正有李牧在前面顶缸,他怕什么?
当下应承下来,回后厨安排准备去了。
长孙无忌再能忍,也差不多到了极限了。深呼吸了一口气,绕过李牧的轮椅,径自上了楼。
李牧看着他的背影,心里冷笑一声。经历了这次的事件,李牧算是想明白了,什么仁义道德,都他妈是狗屁。大家都是互相利用罢了。他组织公司,让长孙无忌等人入股躺着挣钱,等到了他出事的时候,一个个都在观望,每一个帮忙说句话的,不可恼?不可怒?
李世民说的那番话,李牧细细咀嚼之后,也觉得是在放屁。他以他自己做例子,意思说,我做皇帝都要受委屈,你李牧多什么,受点委屈不正常么?
听起来是那么回事,但是细想经不住推敲!
你是皇帝受委屈正常,那是因为这天下是你的。你经营自己的事业,受委屈当然正常。这天下可不是我的,凭什么老子替你受委屈?不就是因为你是皇帝,掌握生杀大权,说话就硬气,可以狡辩么?
明着肯定是要不着公平了,但是暗着可以啊。李牧自有办法,这里吃的亏,别处找补,总能找个心理平衡,要他一个山谷也是这个目的。对李世民如此,对长孙无忌就更是一样了。我不想收你儿子为徒,你逼着我收,那我就得挤兑挤兑你,恶心恶心你,让你破点财。你不乐意呀?好啊,别让你儿子当我徒弟不就行了?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谁要是觉得可以白吃,那他就是个白痴!
李牧忽然觉得自己的戾气有点重了,看来得整点燕窝补一补。李牧打了个响指,李重义弯腰抓着轮椅的椅背,毫不费力地把轮椅拎了起来,把李牧‘搬’上了二层,推着他去了白巧巧等人所在的包间。
……
高公公得了李牧的三条‘大黄鱼’,自然要把事情办到位。他派出了自己的‘儿孙’,去各御史家中通传消息。自己则回到了宫中,向李世民汇报。
李世民看了高公公模仿的李牧的表情,哑然失笑。高公公也是一个妙人,他虽然跟李牧半点也没有相似之处,但是模仿起来却有鼻子有眼,让人看了可以联想出本尊的样子来。
“这小子估计是气疯了,没办法呀,这就是天意,谁能想到卢智林的父亲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去世呢?而且消息还来得这么巧,晚一天都能让他得偿所愿了……”说着,李世民好奇问道:“那卢智林反应如何?”
高公公叹了口气,如实说道:“那卢智林一点也没有悲伤的样子,反而眉目之间颇有喜色。依老奴看来,这个人……不似孝子。”
不似孝子这个评价,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比说他贪赃枉法更加严重。果然,李世民听了之后,眉头皱了起来,道:“真该先免了他的官职,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御史呢?可恶至极!”
高公公道:“陛下,老奴按照陛下的吩咐,问过逐鹿侯之后,又去卢智林府上,告诉他必须允许他丁忧。您猜怎么着,卢智林竟然已经收拾好了东西,都已经装好了车,得了允许之后,跟老奴一起出的门,估摸着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城外了。”
“可恨也!”李世民摆了摆手,道:“不提他了,这次李牧出事,父皇也派人过问了几次,朕一直没有回复。如今事情也算有了眉目,父皇那边,朕还是得去看看。高干,去备车,咱们去天上人间。”
“诺。”
高公公备好车,李世民也换了便服,主仆二人没带随从,出宫门,转个弯就到了天上人间。
下了马车,李世民颇为惊讶。他知道,天上人间的生意不怎么好。平日赶上饭时,也不过几桌客人。但今天一看,满口的马车都停满了,显然是客人不少。难不成几日没来,生意好转起来了?
二人踱步进来,服务员本就是宫里的宫女,自然认得李世民。但是因有言在先,在这天上人间,李渊最大,李世民虽然是皇帝,但是在这里,也不用大礼参拜他。
看到李世民,服务员微微福了一礼,道了声‘欢迎光临’,便让开了路。
李世民经常来此,也不觉得怠慢,叫住一个服务员问道:“今日怎么如此多客人?”
“回禀陛下,今日是逐鹿侯收徒大喜,所以请了不少客人欢聚一堂。”
“收徒?”李世民看向高公公,高公公也一脸茫然,道:“陛下,臣离开之时,没听说此事啊。”
李世民又问:“收的是谁啊?”
服务员答道:“是赵国公世子。”
“胡闹!”李世民紧皱眉头道:“赵国公世子与李牧乃是平辈,还比李牧年长,这怎么拜师?”
服务员一直就在这大厅,刚好听到了刚才‘拜师仪式’上的对话。为了显示隆重,也为了让到场的宾客做个见证。刚刚在一楼大厅,重复了一遍在逐鹿侯府发生的事情。生于吾前,生于吾后那一套也又说了一遍,把长孙无忌着实折腾得不轻。
服务员便把她听到的,对李世民学了一遍。李世民听说长孙无忌也在,还是他亲自带长孙冲去拜师,顿时有些哭笑不得。他所了解的长孙无忌,不像是干的出这样出格事情来的人啊,到底是怎么回事,长孙无忌竟然会让自己长子拜李牧为师?
李世民摆了摆手,服务员退了下去。他则沿着楼梯上楼,打算找到长孙无忌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李世民听到了李牧的声音。
只见李牧坐在轮椅上,依在二楼的栏杆旁,左手一个酒壶,右手一个酒杯,醉眼稀松地看着一楼大厅的众人,打了个酒嗝儿,道:“诸位!诸位!”
把众人的视线吸引了过来,李牧笑了一下,道:“诸位听我一言!”
“今日,乃是我李牧收徒大喜。长孙冲!如今是我的徒弟啦!师父师父,做老师的,就如同父亲一样,徒儿徒儿做徒儿的,就如同儿子一样。长孙冲,如今就和我的儿子一样。”
众人听到这话,想笑又不敢。他们不知道李牧是醉了说得胡话,还是故意的调侃。看李牧的表情非常严肃,又不像是在胡说,让人有些捉摸不透了。
李牧又打了个酒嗝儿,继续说道:“实话实说,我李牧,有什么本事啊!我有什么可教的啊!是吧,我何德何能做别人的老师呢?”
李世民微微颔首,还行,算这小子有自知之明。
“我也不过就是……天才了一点,别人会的,我琢磨一下就会了。别人不会的,我琢磨一下也会了。别人做不出来诗,我随口就做了,除了这些之外,样貌也算是英俊,再也没有什么了。哦,还能赚一点点小钱,也就这些了,我实在是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的优点了!”
“……”
李世民狠狠地瞪了李牧一眼,心里暗道,亏得朕刚刚还欣慰了一下,你这小子,当真是目中无人。
虽然这是在场所有人的心声,但却没人敢说。因为其实李牧说得也是实话,听起来狂妄,但是做到的狂妄,就不能算是狂妄了。
李牧长叹了一声,道:“长孙冲这个徒儿,说实在的,我是不满意的。我会的东西,我教他,他能学会么?比方说,我会打铁,看到我兄弟背着的巨斧了没?这就是我打的!长孙冲学得会吗?他……学不会!”
“作诗?他更是白费。”
“但是国舅爷的面子,我不能不给,所以我收了他这个徒儿。”李牧挥挥手,向对面的长孙冲喊道:“徒儿,你不要生气!你要记住,你是最没用的!为师不会对你抱有什么期望的,你跟我学,学会多少算多少,学不会就拉倒,千万别有压力!”
“你!”长孙冲实在是要忍不住了,正要发怒,被长孙无忌拽住了。长孙无忌摇了摇头,对李世民的方向使了个眼色,长孙冲看到了,强压怒火,老实了下来。
李牧又笑了一下,倒了杯酒,洒了一半,他自己喝了一半。
“其实不瞒诸位,我的心情,最近不是很好。原因嘛,诸位也都知道,我也就不明说了。刚刚说到诗,今日高朋满座,我非常开心,文思如尿崩,实在是……啊,说错,文思如泉涌,差不多!呵呵……”李牧傻笑了一下,道:“给大家做个诗,博君一笑。”
众人听到李牧要作诗,都聚精会神了起来。李牧的诗乃是一绝,从来没有不好的,他这次又要做什么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