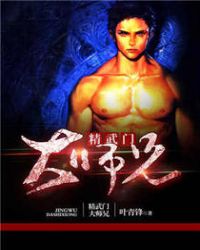她笔下生风:“万物皆处磁场之中。”
“……
“是否,万物皆有迹可循,又或者说冥冥之中自有一种难言的注定?
“比如亿万光年外,天体循循着运作;比如微观世界中,波函数不倦坍缩。
“……”
“比如夏虫追赶春意,冬雪覆盖秋霜;比如江上浮出水月,山林吹渡晚风。……
“比如女孩追着兔子掉进另一个世界,或者夜莺为少年衔来艳丽的红玫瑰。……
“是否,也可比如,我们的相遇?”
“……
“此处,我愿借用卡尔萨根的一句话:‘在广袤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里,能与你共享同一颗行星和同一段时光,是我的荣幸。’”
写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丁林风盖上笔帽,托着脸望向窗外。
――像是突然领悟了一般,她突然在想,倘若世事都要去追求所谓意义,那样会不会太无趣了点儿?
隔着玻璃窗,外面叮叮咚咚,簌簌落落;恍若有风在窃窃私语。
只是,明明都是盛夏时分,窗外绿意却远没有她印象中的那般明朗,甚至连阳光都有些许暗淡。四周分明充斥着虫鸣与躁响,空调的呼呼声与邻座笔尖戳着纸面的刺耳声音,以及某位同学时不时敲动的桌角,风推着门吱吱呀呀;丁林风却觉得周遭静悄悄的,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不经意间,不告而别了。
把鲜活的各色声音,也一并带走了。
第47章 电子表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丁林风发现本该充当闹钟的睡眠灯已经被拔了插头,想来是半梦半醒之间的暴躁行径所致。
窗帘拉得很严实,冷气也打得很足,一切都符合她睡前的一贯作风;除了没有踢被子。
像是做了一场冗长的梦,梦里有一场黑白又无声的老旧电影,树的影子在某个池塘张牙舞爪。
却又意外地睡得很香,反而有一种睡饱了的魇足感。
手机不在床边,以至于她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大致的时间,却恰好听见了桌上电子钟“滴滴”的一声。
她不禁想到,高中的时候自己老是丢手表,前前后后丢了得有四块,久而久之就不爱戴了;当然也有夏天嫌热、冬天又嫌手表老是卷进厚厚的衣袖翻不出来的原因。
于是她和叶想打商量,开启了共享手表计划,并给他带了小段时间的早饭――虽然他一般只让她捎个白煮蛋。
大考或月考的时候会去指定的考场,试场前面都挂着电子表,并无那些有关时间掌控的顾虑,所以只向叶想拜托了在班里小测的时候,把表摘下来,放在他俩桌子中间。
他的电子表会在整点的时候“滴滴”叫一声,声音不算大,但丁林风每次都能捕捉到。
其实,本来教室的前后都置办了石英钟,但是有一次做值日的同学不小心把前面那个碰下来摔坏了。一开始班级公共物品的置换更新归生活委员管,后来不知怎么的就被叶想揽了过去。
丁林风偶尔也会催他:“什么时候把教室前面那块表挂上去啊,这样我就可以自力更生,你也不用每次考试都摘表了。”
他总说下次采购会带上,但居然拖拖拉拉一直没实现。
这真的是叶想行动力最差的一次。
和床侧墙面上的光斑大眼瞪小眼,又稀里糊涂想了一大堆,丁林风踩着拖鞋去洗漱,对着镜子刷牙的时候,又想着是不是还应该再洗洗头。
老实说,她想过无数重逢的场景与时间,比如同学会,又比如他真的获得什么成就了,她在报纸上读有关他的新闻。总而言之,她真的无数遍想象过这样的场景:某一个地点,某一个时刻。
无所谓光与影,无所谓季节或晨昏,无所谓阴晴雨,甚至还可能会飘点小雪。
就算是重逢时两个人的状态,她也猜想过太多太多。面对面,也可能背对背;她甚至看到了彼此眼中毫不遮掩的惊异。
或许有人会哭,或者会笑;也很可能面无表情。
她应该会问很多问题,比如为什么说好一起报同一个大学却在成绩出来后独自去了北方,但又不知道该站在什么立场,毕竟那个大学似乎真的更适合他;当然,她也可能会避开这个问题而问些别的,事无巨细,喋喋不休;又或者是忍不住地自顾自说些近来的事情,比如拿到本校的保研名额了,最近也有在打算实习……
又或许,她什么也不会说,他也一样;他们只是冷漠地对视。
又或许……他们连对视都各自心虚,只是擦肩而过,然后真的就再也不见了。
其实这三年里她最常梦到的就是最后那种场景,她害怕这样,却也在潜意识里觉得这种是可能性最大的。
当然,可能性更大的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永远见不着面。
想到这里丁林风鼻子有些酸,她觉得自己一定没办法接受这种结局。
她望去门边,心里却涌出很多胆怯。
释然是假的,心无埋怨也是假的。只是……
想见到他是真的,怕见到他,也是真的。
--
已经接近下午一点,丁林风实在是饿到不行。
本来准备早上起来干掉半个西瓜,但这句话的客体已经在昨晚壮烈牺牲了――尸体正安安静静地躺在垃圾桶里。
打着哈欠,她后知后觉地摸了摸鼻子。
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不仅吃不到西瓜,还多了一个扔垃圾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