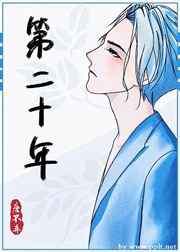郝春龇牙咧嘴。“你不是吧陈景明?你丫这是在抱怨我?”
“我为什么不能抱怨?”当着病房内这么多不相干的杂人,陈景明目光凶狠地瞪着病床上盘腿而坐的郝春,攥着拳,气鼓鼓地道:“你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怎么办?”
这句话透着说不出的亲密。听起来,就像是假如有天他死了,这家伙也会跟着一道殉情。
郝春再次咂摸了下嘴,啧啧连声。“当年撞残钱强的到底是谁,其实么,老子也不算真的想知道。”
这话说的。
钱强脸色一瞬间难看到极点,赫赫地干笑了两声。“郝春,你当年怎么不问问他?”
顿了顿,又像是生怕别人听不懂,钱强竟然又解释了句。“你既然这么相信他,他说不是,你就能相信。那为什么当年老子与你说了后,你不去当面问他?”
郝春眼神再次垂了下去,略带点烦躁地咂嘴,那只朝陈景明伸出的手兀自搁在空气中。“给我包烟。”
“我有。”钱强摸摸索索似乎想要伸手从口袋掏烟,但他如今被陈景明的俩保镖一左一右架着,外套也被脱了。于是只能恼怒地低声咒骂了句,狰狞着面目答应郝春道:“昨天在民政局你要老子去买烟。那包烟现在没了,在外套口袋里。”
郝春无可无不可地挑眉,又或许压根没听见。他的手是朝陈景明伸的。
“烟。”
他又催促了句。
陈景明深呼吸一口气,这回倒不敢真与他犟着――他不给,有的是人给。毕竟钱强就在旁边杵着。
“阿斌,”陈景明皱眉望向那俩保镖。“我记得你抽烟?”
阿斌利落地改成单手架住钱强,从口袋里掏出包烟隔空抛给陈景明。
是包薄荷烟,陈景明记得郝春不爱这种,嫌女气。又或许因为郝春烟龄早,那会儿读书没钱,抽的都是冀北城本地的一个牌子。
陈景明捏着那包烟犹豫了不过三秒,那个该死的钱强又开口笑了。
“他抽北城。”钱强说。
北城,就是冀北城本地卷烟厂的牌子,十块钱一包,焦油含量挺高的。
陈景明脸色又沉了沉,亲自走到病床前把那包烟递给郝春,郑重地塞到他手里。然后就像示威一样,俯身低声道:“有烟感器,我让他们关下。”
当着钱强的面,陈景明总是要表现一下强势的,于是他转身就对阿斌吩咐道:“阿斌你去弄吧!”
阿高顿时有点局促不安。
“嗯,阿高你也先暂时回避下,就在门口就行。”陈景明语声沉静,逐项地吩咐。“另外他这病不是不能吃喝,让他们弄份餐食过来。”
“是!”
阿斌阿高都应了,小心翼翼地出去。
门关的很轻。
病房内只剩下钱强、陈景明与郝春。郝春盘腿坐在床上,又朝陈景明伸手。“没火。”
陈景明语噎。他又不抽烟,哪能随时身上带着火机。
钱强再次刺耳地笑了。他甩动刚恢复自由的左胳膊,嘎嘎笑道:“老子身上有。”
陈景明抿了抿薄唇,有点真生气了。
病床上的郝春瞄了眼陈景明神色,似乎觉得有点可笑,但他却没当真笑出来,丹凤眼尾垂着,淡定地道:“我找他要火,关你什么事儿?”
郝春第二次当着陈景明的面怼完钱强,然后抬头望着陈景明皱眉。“你丫的这么多年都没能学会抽烟?你不是吧?”
陈景明薄唇翘了翘。“不习惯。”
顿了顿,陈景明又特地补充了句煽情的。“你总是病,又总是这样不爱惜自己身体,若是连我也病了,那以后……谁来照顾你?”
“……行吧,”郝春无可无不可,皱眉笑了声。“那你先给老子捞个打火机来。”
搁从前,陈景明对他的命令那绝对是言听计从。但今天陈景明不行。
“他还在这,我不放心。”陈景明瞥了眼钱强。
钱强脸色憋的更加不好看,但居然也强忍着没发作,刺啦一声拖出椅子,跷着二郎腿坐在上头冷笑道:“两位快都别假惺惺了!这事儿当年不是你们心头的刺儿吗?怎么,突然间就都害怕听见真相了?”
郝春与陈景明同时皱了皱眉。
郝春避而不答。“火机。”
陈景明立刻跟上他的节奏,薄唇再次微翘。“好!”
他如今就站在郝春身边,于是他顺势又俯身,几乎是刻意凑到郝春耳边低低地笑道:“那,你与我一起出去拿火机?”
郝春嗤笑,懒洋洋顺着陈景明搀扶的力气起身,其实他这病也不是真残,要说残,也就脑子废了。但陈景明乐意宠着他。
宠就宠吧,反正也宠不了多久。
陈景明这样伺候他、惯着他的日子,也许还剩下一天,也许,需要用秒表倒计时了。
35
十九年前,陈景明从来没主动提出带郝春走出那间景山私立医院的病房。
十九年后,陈景明不仅带着郝春离开病房,甚至提出要去长廊外的花丛间看看。说是盛夏落过雨后,那里的芭蕉叶青翠欲滴,有一蓬蓬蝴蝶花。
郝春诧异地瞪圆了一双丹凤眼,眼底多了丝亮光。“可以吗?我以为你会……”
我以为,你会一直把我关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