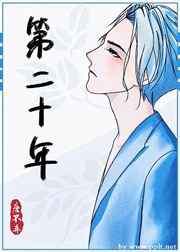郝春叼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烟灰细长地挂在距他唇边不远的地方。光线幽幽暗暗,就像那些个躲藏在暗处的回忆。“嗯。”
陈景明以为这就是终结了,顿了顿,刚想试探性地再多问几句,没想到这次郝春又说了下去。
“初三那年,爷爷单独来景山看过我几回。一开始说老子配不上你,老子不服。第二次,他拿了钱。”郝春讥讽地勾起半边唇角,长长的烟灰抖动着掉落在地。
“陈景明你知道他拿了多少钱么?”郝春夸张地比划了个方框。“那是一张支票,随时可以提现,数字随便填,他妈就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样!”
郝春赫赫地笑。
陈景明笑不出来,他只能攥着拳又再次哑着嗓子道歉。“对不起!”
对这句对不起,郝春充耳不闻。他继续在说着那段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记得的记忆。“第三次,爷爷什么都没带,既没拍桌子骂我,也没拿个空空的支票来。老子被打了镇静剂,醒来的时候,他就慈眉善目地坐在床头,正在给我削苹果。”
郝春唇边那支烟已经燃烧完了,掉在地上,烟蒂一丁点微渺的火星还在不死心地明灭。
“唉陈景明你是不知道啊,咱爷爷慈善起来的时候……”郝春长长叹了口气,口里喊着“陈景明”,眼神却压根不瞟正蹲坐在他身边的三十五岁的陈景明。
陈景明分不清他到底喊的是十六岁的陈景明,或十五岁的,抑或是如今三十五岁的他。
“咱爷爷吧,确实也是个挺会哄人的老头子。”郝春继续嗤笑,一双丹凤眼尾下垂,带着莫名讥诮。“那次他和我说,陈景明你打小儿就是个爱钻牛角尖的,认定了一个人,那必然是不会放手的。他说你绝对不会主动离开我,我活着,你必然要坚持和我在一起一辈子。我死了,死了也不得行,你会跟着我殉情。”
幽光中陈景明眼神动了动。
“所以只有让我疯了。”郝春赫赫地干笑了两声,蹲坐在一堆烟蒂中央,昂起头。“爷爷说,疯了,就是不死不活,这样你就不能再缠着我了。因为等我被诊断为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后,你就再也不能跟我结婚。”
“……阿春,”陈景明嗓子抖的就像含了一支燃着火的烟。
“所以陈景明,老子他妈是为你疯的!那么多的药片喂下去,你说这世上有多少人能撑得住?”
三十五岁的郝春似乎已经完全不介意身边是否有人唤他,他昂着头,目光落在阴沉沉要雨不雨的黑暗深处,嗓子喑哑。“陈景明,你不能懂。我也不希望你懂……曾经希望过,现在,不了。”
郝春突然抬起手,指向那片暗夜沉沉的天幕。“在老子心里,你陈景明一直都是那颗最明亮的北极星。可是北极星啊……它住在天上,它不在凡尘。”
☆、28
阿斌阿高畏畏缩缩地站在黑暗里,都不敢上前打扰陈景明和郝春。但是他们俩个头实在高壮,陈景明一回头就看见了他们。
陈景明伸出去拥抱郝春的胳膊停在半空,长眉微皱。
“阿春,”陈景明开口才发现自己嗓子哑的太厉害,也不比疯了的郝春好多少。他顿了顿才尽可能平缓了语气,轻柔地哄郝春。“你我的事情,回头再说好不好?我先带你去吃饭。”
郝春充耳不闻,甚至还有点烦躁地用脚尖碾碎了几根烟头。
两个人如今都是蹲在地上,形象都差不多狼狈。被催促声惹恼了的郝春斜眼,自下而上扫了眼陈景明。――哦,还是有区别的,这家伙至少没穿病号服。
郝春嘴角微歪,碎发凌乱地遮住额头伤痕,上衣扣子也散开两粒,脖子以下都是淤青。但是他笑起来的时候,通常就没人能注意到这一切,只能看见他鼻梁下那两瓣唇。
人瘦了,也过得苍老,只有这两瓣饱满的唇依然诱人如初。
陈景明目光锁在那两瓣在夜色中微微有些暗的唇,喉结滚了滚。“阿春,走吧!”
他站起来,揉了揉久蹲有些酸麻的膝盖,俯身,伸手来拉郝春。
和过去很多年那样。
郝春斜乜那只手。陈景明的手指总是好看的,骨节玉润,指甲处微红。
所以就是陈景明了。也只能是陈景明。
郝春眼神动了动,慢慢地把手搭在那只“陈景明的手”上,借力起身,然后晃了个踉跄。
陈景明连忙半抱住他,说话声贴着他耳朵。
“要不要我背你?”
郝春艰难地借着廊下幽光打量这半张近在咫尺的脸。高鼻梁,看不见薄唇,大概是说话时“陈景明的薄唇”落在了他颈后。倒是有一对儿料峭长眉。
郝春忍不住抬起另一只手,按在那对儿料峭长眉,仔细地描摹,从眉峰初聚、眉尾斜飞,一直到左眉下藏着的那粒芥米大的黑痣。
“呵呵,”郝春轻声自嘲地笑了笑,歪过头,认认真真地说了句。“你这家伙,长得挺像陈景明的。”
陈景明心里咯噔一声,强行控制不让郝春察觉到他的震动,极慢地扶他站正,然后与他脸对脸相对。
半秒后,陈景明哑着嗓子道:“我就是陈景明。”
郝春又笑了声。歪着头,咂摸了下嘴。“你不是。”
异常肯定。
陈景明薄唇不受控制地抖了抖,嗓子更沙哑。“阿春……”
“别喊我这个名儿!”郝春粗暴地打断他,拳头扬了扬,恼怒道:“老子这名儿,只有陈景明能喊。”
陈景明试图抱住他,然后不出所料地,被推开了。
“滚!离老子远点!”
郝春脊背微弓,如临大敌,瘦到颧骨高突的脸上只剩下一对儿异常明亮的丹凤眼。
陈景明喉结又滚了滚,最后用力地闭上眼,转身,厉声喊人。“阿斌阿高!”
“陈少。”两个保镖畏畏缩缩地走近前。“陈少有什么吩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