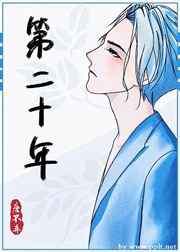陈景明叼着他总是暴躁不肯说真话的唇,含混不清地答他。“这辈子、下辈子,所有的以后,我都是你的。”
在这样温柔款款的情话后,陈景明才轻声地笑着续了句。“要淦,也只能是淦. 你。”
*
郝春再一次沉沉睡去,这一次他睡的昏天黑地完全不知今夕何夕。
睁开眼,是刺目的亮光。
有盏灯打在他眼皮上,是医院专用的那种灯。手脚被束缚,他躺在一张移动的金属床上。
郝春立即挣扎。“艹,这是哪儿?快把老子放开!”
一张陌生的年轻男人的脸放大在他眼前。郝春定了定神,才发现这人全身笼罩在白色防护服内,手里还拿着一管注射器。
昔日被强行按在床头注射的记忆瞬间回笼。
“滚开!”
郝春拼命蹬脚,想要脱离束缚脚腕的皮革带子。
“嘘,安静。”那个陌生男人的脸看起来有种莫名亢奋,他推着注射器对郝春道:“陈少刚走出去一会儿,你要是不放心我单独给你做检查,可以等陈少回来再继续。但我建议咱们不要中断!郝先生你知不知道你是我接手的最有趣的一个案例?你体内混杂着多种药物残留,但你居然能靠意志力坚持了二十年,有趣,太有趣了!”
郝春他妈觉得这一点儿也不有趣。他奋力仰起下颌,怒骂道:“你丫让陈景明滚进来!”
他才不要被当做一个怪物,更不要被人绑在金属床上做实验。
“我可不敢命令陈少。”陌生男人笑了。“陈少在华国产业不多,但他在这里……嗯也就勉强算是这个吧?”
陌生男人松开注射器,戴着薄皮手套的左手比了个“3”。
郝春皱眉冷笑。“OK?他算哪门子OK?OK棒吗?”
门无声无息地滑开,阿斌探了个头,估计恰巧听见这句,立刻又把脑袋缩回去了。
―“陈少,郝先生醒了。”
郝春与握着注射器的男人同时转头看向门外。
大约几秒,又或许更快,一抹鲜艳至极的朱红色长衣袭入郝春眼眸。这明亮的色泽竟然刺的他眼球微微有些痛,忍不住要落泪了。
三十五岁的陈景明穿着古代华国才有的朱红色新郎倌喜服长袍走进门,依然利落的平头,五官俊美宛若一尊玉佛。
―“阿春!”
“你……你……”郝春支吾了两次,仓惶掉开头,沙哑着嗓子故意嘲笑道:“你穿成这样做什么?又不是去唱戏。”
陈景明脸色不变,也不管旁边拿着注射器的Tommy一脸看笑话模样,薄唇微翘,静静地答道:“裁缝量身定做的喜服刚送过来,我出去试衣了。阿春,你觉得我穿这套好不好看?”
陈景明穿朱红色喜服好不好看?
郝春眼底到底还是涌出了泪。他俩曾经探讨过未来,十五岁的陈景明信誓旦旦,对他说,阿春,男孩子也可以一辈子。二十五岁的陈景明俯身带笑问他,阿春,你想要个什么样的结婚戒指?
那次他没要戒指。再后来,他们就分手了,因为一个可笑的谎言。
郝春觉得自己当初相信那个谎言的样子很可笑。十年后,陈景明与钱瘪三同时出现在他眼前,只不过是一句轻飘飘的――阿春,当年他骗你。郝春就信了。
甚至没要求更多的来龙去脉。
二十年,他总是这样无条件地信任着陈景明。
所以当年为什么他会相信是陈景明撞残了钱瘪三,还傻傻地要献身给钱瘪三,以便“拯救”陈景明呢?陈景明压根不需要他拯救,那场车祸,本来也就是个谎言。
他该早就知道的。他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陈景明罢了。
“阿春,”陈景明俯身,正在温柔亲吻他的脸颊。“我穿这身好看吗?”
郝春曾经幻想过,假如真的有一天他们两个人结婚,陈景明该穿什么衣服?陈景明穿什么都好看,所以婚礼那天陈景明该穿什么样的衣服最好看,他想了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眼下陈景明就穿给他看。
郝春别扭地将脸转开,陈景明却锲而不舍,执着地亲吻他唇角,呢喃低语。“你也有一套,咱俩都是新郎倌儿,衣服款式包括刺绣都一模一样。”
陈景明说完缓缓起身,抬袖给他看。朱红色长衣以祥云纹封了箭袖,袖口颤巍巍缀着颗弹珠大小的珍珠。
“你从小喜欢弹珠。”陈景明微抿薄唇,顿了顿才道:“所以我特地让人缀了这种海珍珠。”
也是,弹珠总是上不得台面。
郝春赫赫地干笑。“你怎么晓得老子喜欢弹珠?”
陈景明垂眸,眸光深处死死地锁住郝春。“你说过的。你说过,会找个水晶瓶把我和你的弹珠都放进去。”
那是……很久很久之前的,从前。
郝春倒从没想过,陈景明居然都还能记得。他艰难地笑了声。“陈景明?”
“嗯。”
“咱俩真的要结婚了?”
“真的,”陈景明薄唇翘了翘。“就在月底,还剩二十一天。”
郝春沉默着。他沉默了很久,想像过去那样抬手在陈景明肩头捶一拳,却发现自己双手双脚都被缚着。他忽然转作恼怒。“那你丫还把老子锁着干啥?”
“只是给你做份例行检查。”陈景明解释道:“婚前需要有检查报告书。”
郝春瞪着眼,不甘地、咻咻地喘着气。“老子是个不折不扣的疯子,你还要与老子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