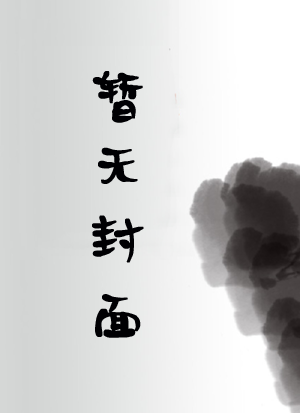第六章 群体选择
第六章 群体选择
生物学家审视了近5亿年发生在陆地上的生物演化,试图找到高级动物社会出现的证据。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知识来更好地来理解人类。但是,一个极为难解的遗传之谜给他们造成了障碍。
这个谜团包含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在上文已经谈到过,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里已经意识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虽然具体细节还有待厘清。这个难题就是,如果社会中的众多个体不再繁殖,那么高级社会怎么还能演化?说得通俗一点,利他主义是怎么出现的?达尔文提出的解决办法,在今天已经发展成了群体选择理论。该理论认为,只要它们的牺牲能为群体带来足够的利益,群体内的某些成员就会缩减自身的生命,或者抑制自身的繁殖,或者两者都做,以便本群体能与其他群体更好地竞争。于是,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利他主义基因就会在群体内传播开来。群体成员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会加速利他主义基因的传播,但不是利他主义传播的原动力。密切的亲缘关系往往是在利他主义传播之后出现,而非之前。群体遗传学的多个模型表明,在一个群体里,即使平均只有一个可以遗传利他性的个体,无论其成员之间是否有亲缘关系,整个群体的数量都会因此上升。
这种认识于是引出了第二个难题。为什么真社会性——典型特征是基于利他主义的劳动分工——在演化史上如此罕见?这个问题的答案必定存在于真社会性出现所需要的一个先决条件里:一个母亲或者小群体在一个设防的巢穴里一步步地抚养幼儿长大。在大自然里,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并没有产生真社会性。所以,更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是,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最后一步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抑制性因素,我们就可以解决关于真社会性起源之谜的第二部分。
我相信答案在于,最后一步牵涉了生物学固有的巨大困难。试想,有一个较小的群落,其中包括了一位母亲(或许还有一位帮忙的父亲)及其刚刚成年的一群后代。普通的生命循环就到此为止了。当雌性后代与母亲分开,独自生活的时候,新的生命循环也就开始了。母亲或者死去,或者再养育新的后代;与此同时,后代开始交配、筑起新巢,成为新母亲。
现在,假设出现了一个缺失突变,可能只是单个碱基的改变,使得这个小家庭不再分家(缺失突变较为常见,它会使其他突变无效,在遗传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我们知道,如果一群成年雌性动物在实验室里被关在一起,第一个进来而且已经受孕的雌性动物,即母亲,会成为首领,并开始产卵,其他雌性则转为工职。
因此,一旦初步适应就绪,包括筑好一个设防的巢穴并开始渐进式地抚育幼儿,这个群体离真社会性就只差一步了。从原则上来讲,最后一步不算困难。不过,虽然这种进步看起来容易,在自然界里却鲜有发生。为什么?一种解释是,虽然单个基因或少数几个基因的突变就可以引起真社会性群落的出现,但余下的全部基因组仍然适应于独居生活。后代里的雌性,作为新出现的工职者,也许会本能地待在群体里,但是余下的基因组却仍然决定了它们更适应单打独斗的生活。它们还没有准备好彼此交流,或者分工协作,完成筑巢、哺育、觅食的任务。而一旦有了这样的累赘,那些还未做出改变的群体,既无法有效地与那些独居的同类竞争,也无法与其他群落竞争,结果就是,它们无法成功演化成真社会性物种。
关于哪些遗传突变会导致真社会性的演化,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详尽的记录。2015年,由伊利诺伊大学的凯伦·M.卡费姆(Karen M. Kapheim)和吉恩·M. 鲁宾逊(Gene M.Robinson)领衔的包括52位研究者在内的一个国际合作团队,研究了10个蜜蜂物种的基因组,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演化阶段的多个独立支系。这些物种的社会化程度高低不一,最低的是独居物种,最高的是复杂的真社会性物种。研究发现,每一个代表性物种都有其遗传演化的独特路径,但是,所有实现社会性的物种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基本模式。随着社会合作渐趋复杂,自然选择也更为松弛,于是它们都出现了更多的中性演化,与此同时,转座元件(transposable element)的数量和多样性也有所减少。我承认,这个问题的专业性较强。如果用尽可能通俗的语言来说,大意就是,高级的社会组织与基因网络(gene network)复杂性的增加有关,进而影响了社会行为。高级社会行为的演化,的确需要遗传程序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昆虫学家迈克尔·V. 布莱恩(Michael V. Brian)和我,各自独立发现了蚂蚁幼虫发育成工蚁和蚁后的复杂机制,这为蚂蚁的真社会性提供了证据。布莱恩研究的是一个欧洲物种,皱红蚁(Myrmica ruginodis)。他发现每个幼虫都有潜力发育成蚁后——有巨大的身体、翅膀和完全发育的卵巢;或者发育成工蚁——身体较小,没有翅膀,不可生育。这里有一个体形大小的阈值,即幼虫命运的“决定点”,幼虫在此之后必须要完成生长,或者变态为蚁后,或者变态为工蚁。布莱恩发现,决定皱红蚁成为蚁后还是工蚁的关键环境因素,事实上是一系列要素的组合,包括孵化出这些幼虫的卵的大小,生长到“决定点”时幼虫的个头大小,蚁群里的蚁后是否还健在,蚁后的年龄几何,以及该幼体是否经历过冬季的严寒并在翌年春天快速生长。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为蚁群提供了大量的童贞蚁后(virgin queen),它们会在日后天气温暖时的婚飞(nuptial flight)大典上,飞出蚁穴,正式宣告登基。每只蚁后都有机会交配,并建立属于它自己的新蚁群。
多年之后,在2002年,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的埃哈卜·阿布哈夫(Ehab Abouheif)及其合作伙伴,在研究蚂蚁的基因组时,发现蚂蚁产生有翼蚁后的能力取决于雌性是否携带某些被修饰的基因。这些影响蚂蚁发育到成体阶段的基因网络,在有翼的蚁后体内是保存着的,但在无翼的工蚁等级中却被扰乱了。简言之,这些工蚁失去了一项潜在的遗传天赋。
现在,许多信息都已尘埃落定。在1953年,我曾经测量过世界上49个属的蚂蚁,它们的工蚁里都包括不止一种亚等级(subcaste),即工蚁又可以分成次要工蚁和主要工蚁,后者有时也被叫作兵蚁(soldier)。许多物种还有介于中间状态的工蚁(中间工蚁),少数几个物种还有个头更大的第三种等级,叫作超级兵蚁(supermajor)。在高级社会组织的形成过程中,新增的亚等级不仅要在幼虫发育的过程中增加一两个额外的决定点,而且要在蚁群发展的不同阶段,对不同等级个体的相对数量进行调控。这种调控,就好比是人类社会里的职业分工,以及对不同行业人数进行的文化调控。
于是,就出现了蚂蚁帝国与人类帝国。
要获得必要的遗传变化,并克服独处基因组带来的障碍,唯一的途径是群体选择,因为只有群体选择才足以产生基于基因的利他主义、劳动分工和群体内成员之间的合作。这种更高水平的自然选择已经得到了翔实的记录,而且在蚂蚁和其他社会性昆虫里可以直接观察到。这种自然选择不仅出现在蚁群形成的过程中,也出现在与其他成熟的蚁群竞争时。冲突可能会因为直接的身体接触而爆发,最终结果是一方撤退或者彻底溃败(如果要发明一个术语,可以叫“红蚁大屠杀”)。不过,蚁群之间的竞争,并不一定会导致斗争或者掠食。它也可能会导致一方抢占新的觅食地点,驱赶或者消灭竞争对手,或者更高效地寻获筑巢材料与食物。理论与实验研究已经证实,所有这些出现在蚁群层次的可遗传行为,主要依赖蚁群的生长速度和成熟蚁群的规模,而这两种因素又都依赖于受遗传决定的、群体层次的表型。假定其他方面一致,那么仅仅是参与竞争的工蚁数量,就会对蚁群的代谢和生长速率产生深刻的影响。工蚁越多,蚁群生长越快,就能产生更多的蚁后和雄蚁,成熟之后的蚁群规模也更大。这种群体层次的关系,类似于个体层次的体重与生理特征的代谢标度律(metabolic scaling law)。数学模型表明,在昆虫群落的竞争式生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因素,可能是奠基蚁后(founding queen)的初始繁殖能力。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群体遗传学根据检验过的原则界定群体选择的进程,人们又是如何通过这个进程正确地解释社会演化的。这值得我强调一番:无论是群体层次的性状,还是个体层次的性状,选择的单位都是基因。基因规定了性状。自然选择决定了哪些基因表现得更好或更差,但是自然选择的靶标是由基因规定的性状。一个群体内的个体,与其他成员竞争食物、配偶和地位,就是在个体层次参与自然选择。个体与群体内其他成员互动,并通过等级制度、领导、服从或合作来形成更高级的组织,就是在群体层次参与自然选择。利他主义的代价越高,对于个体生产和繁殖上的损失越多,那么这对整个群体的益处也必须越大。演化生物学家大卫·S. 威尔逊(David S. Wilson,不是我的亲戚)精练地总结过这两种层次上的选择规律:在群体内部,自私的个体胜过利他的个体;在群体之间,利他个体组成的群体胜过自私个体组成的群体。
近年来,通过研究自然条件下的真实例子,群体选择的发生过程已经得到阐明。我们不妨从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狼群说起,它们为我们理解生态学和社会生物学提供了极好的教材。最近,明尼苏达大学的基拉·A. 卡西迪(Kira A. Cassidy)和她的同事们发现,当群体发生领地冲突时,数量大的群体(平均有9.4只狼),会战胜数量小的群体(平均有5.8只狼)。此外,成年雄性比例高的群体也更有可能击败成年雄性比例低的群体。最后,如果一个群体里有6岁或者更老的狼(在黄石公园,狼的平均寿命是4岁),无论是什么性别,都会带来更大的优势。
接下来,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无脊椎动物,在它们身上我们可以见证最为多样的群体选择的发生。一个尤其令人震撼的例子来自沃尔特·R. 钦克尔(Walter R. Tschinkel)。在其经典著作《火蚁》(The Fire Ants,2006)里,他详细考察了入侵红火蚁(Solenopsis invicta)里蚁后的合作与斗争。在婚飞大典和空中受精之后,单只蚁后经常聚集成群,数目达十只或更多,它们共同筑起一个小小的巢穴,然后协力抚养第一批后代。这种不寻常的行为显然是由群体选择驱动的。生活在一个竞争无比激烈乃至生死攸关的世界里,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蚁后能够繁育出规模足够大的蚁群,培养出新的蚁后后代。野外研究已经表明,每个蚁群的规模对它的生存至关重要,对于非常年轻的蚁群而言,情况显然更是如此。在实验室里,相比单打独斗的蚁后,一群彼此合作的蚁后,平均而言,孵育出的工蚁更多,繁殖速度也更快。
一旦火工蚁成熟,它们就开始逐个清除蚁后,将其肢解,或者蜇死,直到最后留下一只蚁后。它们甚至也不放过自己的生母。最后的胜利者,可以通过其独特的信息素被区别开来。它的繁殖力最强,因此也最有能力促进整个蚁群的快速生长。工蚁无力承担起支持失败者带来的损失,即使这意味着它们的生母也得死去。在这个例子里,群体选择无疑战胜了个体选择。
在世界范围内,蚂蚁表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物种数目超过1.5万,这使得它们成为理想的研究对象,因为通过对不同的蚂蚁物种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分辨出社会演化的必备因素。归根结底,该领域探讨的核心问题有三个:(1)是谁或是什么控制着蚁群中的工蚁数量?(2)这分别是如何实现的?(3)这应归因于自然选择中的哪种力量?
快速DNA测序技术使得研究者可以更方便地针对整个蚁群进行实验,并分析其中的社会因素。这些工作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群体选择的认识,因为它才是影响昆虫社会演化的“看不见的手”。比如,在蚁群里有一种现象叫巡警(policing):工蚁会惩罚那些与蚁后竞争产卵的同胞,有时甚至会处决它们。在过去,巡警现象往往是通过广义适合度(inclusive fitness)理论来解释的,它依据的是工蚁之间的亲缘关系。许多人认为,从原则上讲,试图篡权者与巡警之间的亲缘关系越远,它们受到的惩罚也就越重。不过,同样的结果也可以通过篡权者与整体蚁群的气味差异得到解释。洛克菲勒大学的塞拉菲诺·泰赛奥(Serafino Teseo)、丹尼尔·克罗瑙尔(Daniel Kronauer)和他们的同事最近证明,蚁群效率的提高可以为巡警现象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他们发现,来自热带的毕氏粗角猛蚁(Cerapachys biroi),虽然是孤雌生殖产生的单克隆群体,即所有工蚁的遗传基因是完全一致的,但仍然有巡警现象。要解释该现象,我们需要求助于生物学的另外一个领域,如下所述。在蚁群的生命周期里,生长与调控是受幼虫诱导的。在生命周期的某些环节,成体接收到这些不成熟的幼虫发出的信号,卵巢于是停止工作。那些没有对信号做出响应的个体,由于破坏了蚁群的生命周期,会受到惩罚甚至被处决。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实验,研究者把两个不同的粗角猛蚁群放到一起,一个是典型的单克隆群体,另一个则是实验室里由两种不同的遗传背景(它们有不同的父母)混合而成的杂合蚁群。结果表明,单克隆蚁群胜过了杂合蚁群,原因显然是杂合蚁群里出现了许多不工作、只产卵的个体。这些雌性的行为扰乱了蚁群正常的繁殖周期,因此降低了整体的生长效率。
日本琉球大学的土畑重人和辻和希独立进行了一个类似的研究,他们使用的是另一个单克隆蚂蚁物种——刻纹棱胸切叶蚁(Pristomyrmex punctatus),并得到了类似的结果。该物种没有蚁后,所有的工蚁都参与产卵,并抚育后代长大。与没有蚁后的粗角猛蚁群体一样,产卵不会对这种蚂蚁的个体带来什么好处。所有未成熟个体的遗传基因都是一样的,所有后代都在奉行平等主义的社会里长大。每一只工蚁都是潜在的母亲,同时也是所有其他母亲的拷贝。在野外,蚁群会被来自其他蚁穴的具有不同遗传背景的工蚁渗透。这些外来的工蚁会作弊:它们会比本蚁穴的蚂蚁产下更多的卵,而且逃避劳动。在实验室里,作弊的工蚁总体上产生了更多后代。但如果一个群体里全都是作弊者,那么它们都无法留下任何后代。
我们能从这个奇怪的现象里总结出什么呢?亲缘关系在刻纹棱胸切叶蚁里的重要性仅限于:单克隆蚁群中的工蚁母亲能够识别出来自其他蚁群的蚂蚁,知道谁是外来移民。当作弊者入侵另一个蚁群的蚁穴时,它们就好像是社会的寄生虫,巧取豪夺另一个物种的劳动成果。鸟类中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就是杜鹃鸟,它们会把蛋偷偷下到其他鸟类的巢里。
2001年,亚利桑那大学的帕特里克·阿博特(Patrick Abbot)及其同事首次报告了在真社会性蚜虫里也有类似的现象。他们研究的这些物种会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群落,甚至会形成士兵等级。它们也是单克隆群体,因此社会等级不是由亲缘关系塑造的。其中,至少有一个物种(学名Pemphigus obesinymphae),它的群落并不总是纯种的单克隆,而是常常混进其他群落入侵者的后代。这些入侵者就像是寄生虫,它们自己不去承担守卫家园的危险任务;相反,它们会改变自己的生理特征,自顾自地繁殖后代。
社会生物学研究融合了博物学与遗传学,在其发展史上,研究者不断地从社会性生物的生命周期里发现这些令人惊讶的新规律,而且发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其中最引人注目、最富教益的是社会性黄蜂中的排队繁殖(reproductive queue)现象,这是由拉加文德拉·加德卡尔(Raghavendra Gadagkar)及其同事发现的,他们来自位于印度班加罗尔的印度国家科学院。研究者发现,阔边铃腹胡蜂(Ropalidia marginata)的群落虽然从外部看来社会组织关系很简单,但实际上有一套复杂的合作规则。一个铃腹胡蜂群落里的所有工蜂,从生理上而言,都可以繁殖后代,然而它们都臣服于在任的蜂后。在这个例子里,统治者并不是攻击性最强的个体,也不是优势等级(dominance hierarchy)的首领。尽管如此,蜂后仍然在蜂群里独揽了产卵权。可以说,铃腹胡蜂处于一种仁慈专制(benevolent autocracy)的社会中。一旦蜂后被移除,其中一个工蜂就会暂时地对其他同胞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几乎没有其他工蜂会挑战它的这些表演。一旦稳定下来,新的蜂后重新变得温和,表现出母仪天下的气质。它的卵巢开始发育,并准备产卵。于是,它成了独一无二的生殖母体。如果它死去或者被研究者移出蜂群,很快就有另外一只工蜂填补上来,对新工作似乎驾轻就熟。当这个继任者离开,又会有新的工蜂上位,以此类推,有条不紊。蜂群好像是沿着(在人类看来)神秘的法定继承人顺序,和平地进行权力交接。
研究发现,每一只新任蜂后跟其他工蜂的亲缘关系都不是最近的;事实上,它往往是最年长的那一只。整个过程似乎是由调停人信息素(peacemaker pheromone)参与完成的。因此,王室的继承顺序也就体现了一种群体层次的适应。这套秩序几乎避免了一切暴力的、毁灭性的冲突。它同时也降低了蜂群内部陷于无政府状态和被外来胡蜂篡权上位的风险。理论上来说,铃腹胡蜂群可以是永生的,不过,由于环境的变迁,它们实际上活不了很久。
另外,从一支独立起源的较为原始的真社会性黄蜂那里,人们也发现了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自然选择,它可能也是在群体层次安静地发挥着作用。有一项研究发现,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19个这样的物种里,单独活动的蜂后,无论是在蜂巢内还是在外觅食,都面临着很高的风险。研究者监测多个研究样本后发现,38%~100%的奠基蜂后(foundresses)在第一批后代孵化出来之前会死于非命。在另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在至少两个黄蜂物种里,Liostenogaster fralineata和Eustenogaster fraterna,一旦奠基蜂后死去,那些失去首领的助手工蜂(helpers),无论它们与蜂后是否有亲缘关系都会继续抚育原蜂后留下的后代,直至后者成熟。与此同时,这些助手也开始产卵,留下自己的后代。于是,通过真社会性的延续,它们就为所有的合作者创造出了一种“上了保险”般的优势。
随着研究者对动物社会的探索日益深入,社会生物学家们也发现了更多的演化路径,其中一些非常惊人,甚至可以说有点怪诞。有些种类的蜘蛛就具备这样的奇异现象。研究真社会性的科学家,一度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发现具有真社会性的蜘蛛。目前人们知道,起码在两种独立演化起源的物种里,社会性蜘蛛会分享同一张巨大的蛛网,但是这些物种里并没有出现专职繁殖和专职工作的等级。
不过,这些共享一张网的蜘蛛,的确会表现出“性格”差异,而这明显是由群体选择维系的。这种现象出现在阿内蛛属(Anelosimus)里。这种蜘蛛广泛分布在世界各地,并且具有丰富的地区多样性。它们属于姬蛛科(Theridiidae),这个科里还包括黑寡妇蜘蛛。像它们臭名昭著的远亲那样,这类蜘蛛的腹部往往有色彩鲜艳的图案。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会形成蛛群的物种:上千只饥肠辘辘又通力合作的母蜘蛛,悬挂在一张巨大的蛛网上,这简直就是蜘蛛恐惧症患者的噩梦。来自匹兹堡大学的乔纳森·N. 普鲁伊特(Jonathan N.Pruitt)和他的合作者发现,在新世界物种栉足蛛(Anelosimus studiosus)形成的蛛群里,母蜘蛛包括两种不同“性格”的群体。第一种更富侵略性,会积极参与捕获猎物、搭建蛛网、保卫蛛群;第二种则相对温顺,主要参与照顾幼蛛,包括保护大个的球形卵块。更富侵略性的母蜘蛛能更有效地捕获食物或驱逐入侵者,而更温顺的母蜘蛛则更擅长照顾许多幼蛛。它们的性格差异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遗传差异引起的,不过,这两种蜘蛛仍然相处得比较和谐。
图7 一群社会性蜘蛛(栉足蛛)捕捉到了一只大甲虫,开始分享食物,图中同时展示了两种“性格”的蜘蛛:远处的负责捕猎,近处的照顾球形卵块
群体选择指的是自然选择作用于那些规定了社会性状的等位基因(同一个基因的不同形式)。那些被自然选择青睐的社会性状,牵涉到群体内的个体间的互动,包括群体最初的形成过程。当由同一个物种组成的不同群体竞争的时候,它们成员的基因就会受到筛选,自然选择就驱动着社会演化向上或向下发展。通过博物学观察和实验室研究,众多研究者对这个过程做了详尽的记录。
使用栉足蛛进行科学研究的优势在于,研究者可以从自然界中的特定地点收集蜘蛛个体,并按照不同的性格比例重新组合蛛群,然后把新的蛛群留在原地,或者放在环境不同的其他地点,再来观察它们会如何适应。这样,普鲁伊特和他的同事就能考察群体选择的出现过程。结果是正面的:无论是在原始地点,还是在新的地点,人造蛛群内的侵略性个体与温顺个体的相对比例,在两代之后都变得跟自然状态下一致。
最后,在白蚁和它们可能的直系祖先身上,我们终于有机会直接观察到群体选择的效果:跨越了重重障碍,迈进彻底的真社会性。
该研究领域内的专家普遍同意,白蚁是蟑螂的后裔。演化生物学家则纠正说,这两个密切相关的昆虫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尽管如此,由于它们的演化发生顺序非常接近,我认为可以说白蚁就是社会性的蟑螂。
在现存的各种蟑螂中,与白蚁最接近的是隐尾蠊属(Cryptocercus),其体形较大,靠吃木头为生,分布在北美洲、俄罗斯东部和中国西部。它们的外表很像马达加斯加嘶鸣蟑螂(Gromphadorhina),经常被用于实验室研究,也经常在好莱坞恐怖电影中作为吓唬人的“害虫”出镜。
隐尾蠊在蟑螂之中属于个头比较大的。它们的避险法不是火速逃离天敌,就像我们在厨房里常见到的“小强”那样,而是依赖于它们厚厚的几丁质盔甲的被动保护。它们携带着厚重的外骨骼,前段身体像一面盾牌,脚上有刺毛,走路的节奏也颇有派头。它们把家安在死去的树干或树枝里,并一直守卫着它。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克里斯蒂娜·纳勒帕(Christine Nalepa),最近综合了解剖学与遗传学的证据,证明隐尾蠊与白蚁在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方面有相似性。她指出,与现代的白蚁类似,这些蟑螂也依赖着其肠道内的特化细菌或其他微生物。这些共生菌能消化朽木里的纤维素,并与昆虫宿主分享其分解产物。此外,隐尾蠊和白蚁都会把分解之后的木质成分从肛门排出来,其中一部分用于喂养它们的幼虫。
隐尾蠊的群体类似于白蚁社会,事实上都必须把肠道内消化木头的共生菌群传给下一代。隐尾蠊会组成典型的家庭,父母照顾孩子,直到孩子长大成熟,也成为父母。白蚁,作为统治昆虫世界的物种之一,也有家庭,但是性质完全不同。大多数白蚁的后代并不会成为父母;相反,它们会成为工蚁,来帮助父母和其他姊妹工蚁。换言之,它们组成了一个不断生长的群体。于是,复杂度最高的社会组织——真社会性群体存在的条件出现了。其中的个体被捆绑在一起,组成单一的生殖单元。在隐尾蠊群体里,社会生活主要是由个体层次的选择塑造的;白蚁群落则更上一层楼,组成了主要由群体选择塑造的复杂社会。
这就引出了一个多年来困扰着社会生物学的重大争论。它起源于英国生物学家约翰·伯顿·桑德森·霍尔丹(J. B. S.Haldane)。在20世纪50年代,他设计并发表了一个思想实验。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设想后来被称为亲缘选择的情境时,用下面这个思想实验阐述了他的想法。假设你看到一个人溺水了,如果要救他,你自己就有10%的可能会淹死。让我们假定,你体内规定了社会行为的基因完全主宰了你。如果这个溺水的人是一个陌生人,那就不值得冒着10%失去生命(以及体内全部基因)的危险去救他。即使你成功了,你的基因也不会因为你的冒险而受益。不过,如果这个溺水的人是你的兄弟,他体内有一半的基因跟你的一样,这种情况下,就值得冒着10%失去自身基因的危险去救人了。换言之,从基因的角度来看,在基于自然选择的演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权衡清楚再去救人。
在设想这个情境时,霍尔丹意识到了亲缘选择有可能演化出利他主义行为,继而产生像蚂蚁与人类群体里的真社会性,而且它依赖于施惠与受惠者之间密切的亲缘关系。亲缘关系越近,它们共享的基因就越多,它们自己就有更多的基因可能传给下一代。有一个关于霍尔丹的疑似杜撰的说法:“他愿意为他的八个表兄弟或两个亲兄弟献出生命。”
1964年,英国的遗传学家威廉·D. 汉密尔顿(William D.Hamilton)提出,亲缘选择可能是真社会性起源的一个关键因素。他提出了亲缘选择的一个公式,来表明即使一个性状不利于普通的个体选择,但只要它给群体内其他成员带来的收益(记为B),乘以成员之间的亲密程度(记为R),大于自己所付出的成本(记为C),这个性状就会在群体里保留下来。于是就有了所谓的“汉密尔顿法则”(Hamilton's Rule),记为BR-C>0,它描述了真正的利他主义能够演化所需满足的条件。
像在物理学里那样,以一个公式来表达社会演化中的一个复杂的进程,看起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然,在今天看来,可能不算什么了),这为“一般性汉密尔顿法则”(HRG)带来了非同寻常的关注度,也促进了它的传播,而且在今天的社会生物学与演化理论的入门课程里依然有人会提到它。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逐渐认识到了这个理论的致命弱点。数学家和受过数学训练的演化生物学家,越来越坚定地拒斥一般性汉密尔顿法则。他们认为作为一个科学论断,这个法则既不准确,也说不上有用。比如,马丁·A. 诺瓦克(Martin A. Nowak)、亚历克斯·麦卡沃伊(Alex McAvoy)、本杰明·艾伦(Benjamin Allen)和我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
对一般性汉密尔顿法则的数学探索揭示出三个令人震惊的事实。第一,从逻辑上说,一般性汉密尔顿法则无法在任何情况下做出任何预测,因为我们无法提前知道收益(B)和成本(C)。它们依赖于有待预测的数据。在实验开始之前,效益和成本都是未知的,因此,我们也无法得知汉密尔顿法则会做出何种预测。一旦实验结束,一般性汉密尔顿法则做出事后总结,得出收益和成本的数值:如果关心的性状增加了,那么BR-C就为正值;反之,如果关心的性状减少了,那么BR-C就为负值。但是,这些所谓的“预测”仅仅是对已经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重新组合而已,而且数据里已经包含了一项性状是增加还是减少的信息。特别是,收益与成本参数取决于性状平均值的变化。
第二,一般性汉密尔顿法则做出的仅仅是事后回顾,并不是基于成员之间的亲密程度或者种群结构的其他方面的。对汉密尔顿法则的一种常见解释是,亲密程度(R)量化了种群结构,而收益和成本刻画了一项性状的性质。但是推导表明,这种解释是错的。全部三项数值,亲密程度、收益和成本,都是种群结构的函数,而BR-C的总值函数却独立于种群结构。这是因为在计算BR-C时,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都彼此抵消了。
第三,对于一般性汉密尔顿法则,我们无法设计出任何实验来进行检验(或证伪)。所有可输入的数据,无论它们是来自生物学还是其他领域,总是与一般性汉密尔顿法则吻合。这种吻合反映的不是自然选择的后果,而只是陈述了在多元线性回归(multivariate linear regression)中斜率之间的关系。在统计学领域,这种关系早在1897年就已经为人所知了。
汉密尔顿提出的另一个抽象概念——他称之为“广义适合度”——则更加空洞。该概念将汉密尔顿法则的应用范围从个体之间扩展到群落全体成员,表示整体在多大程度上受益于所有的互动。虽然有几位尽职尽责的“广义适合理论家”,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学派,为“广义适合度”辩护,但他们从未在真实世界里测量过它,哪怕在假想情境里它也未能成功。
我承认,也有可能是批评广义适合度理论及应用的人——包括我和其他几人——犯了错,未来有一天,也许会有人测量出或至少间接地估测出广义适合度。在那种情况下,汉密尔顿对亲缘选择的发展将会被证明是对社会生物学的一大贡献。但是,就目前来说,要推进对社会起源的理解,我们还是必须依赖传统(也是迄今为止最为有趣的)方式,即通过野外调查和实验室探索,从大量的数据里披沙拣金,最后做出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