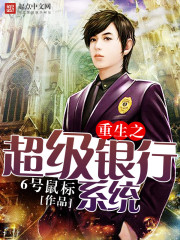“别说你没有时间拔箭,单说即便有机会拔掉,群敌环伺的当口,随着不停杀敌,伤口不断出血,就算箭伤在不要紧的地方,失血过多也要死人哪!”
承暄皱着鼻子宠溺地将承晔两腮向中间一挤,“还不如让断箭留在身体里,先这么堵上那伤口。”
未被折断的一支蓝羽箭深深没入心口,她的躯体在这最后一击之下痛楚挣扎出狰狞的弧度。往日清丽的面部苍白得几近透明,失去生气的面孔惨白脆弱得如同即将消融的雪花,仿佛眨眼之际便要消失了。
承晔双腿忽然一个趔趄,胸口剧烈抽痛起来。
大哥他,最后也是这样吗?
那英武清隽,坐在马背上会发光的兄长,在人生最后一刻竟是这样离世的吗?
他的兄长和阿小的父亲身上中了二十七箭,每一箭都刺入同样的血脉和骨肉,被同袍之箭刺入身体,会有多痛?
“晔儿,站好!”
林世蕃目中惊恸,伸手拦住承晔。
他这才意识到阿小正紧紧抓住他的手臂,他能感受到阿小的手掌在剧烈发抖,也终于明白阿小为什么自铁勒王帐回去之后便满面杀意。
江禀义挣了几下,看世蕃向他点了点头,便冲到柴堆旁跪坐了下去。
他口里发不出声音,只张大了嘴巴无声地呜咽着,令所有看见的人都从喉咙痛到心里。
承晔抓住胸口上的衣襟,拼命遏制越来越困难的呼吸,竭力想让空气自口中进入胸口。
世蕃迎着铁勒王投来的疑惑的目光,微微点头说道:
“曲姑娘是我这护卫的亲人。”
铁勒王眼中的哀色更沉了几分,拉着身旁的世子走到禀义身前深深躬身一揖。
铁勒王世子又哽咽着向江禀义跪下叩拜道:
“曲姑娘有大勇大义,先生请受晚辈一拜。”
禀义在女儿的搀扶下站起身向铁勒王父子回礼。
此时静默着的王帐侍卫在一声令下以土奚律语齐声祝祷着,用手中的火把缓缓点燃了柴床。
铁勒王父子则站在棺木旁,将曲伊人生前的衣物配饰一件件地放入棺椁之中――她尸身损毁严重,只能火葬,棺椁之内只能留下骨灰和衣冠。
当铁勒王捧着最后一顶珠冠颤巍巍地放入棺椁之内时,承晔分明看见有眼泪顺着他眼角的纹路流过苍老干涸的下颌,滴入棺椁之中。
帐外换防的护卫已报了亥时,帐内的几人仍然如木雕泥塑般一动不动。
“呵……”林世蕃深深地吐了一口浊气,胸口的压抑有了些微的舒缓。
“禀义,那曲姑娘到底是你什么人?”
“是我妹子。”
好似预料到众人的反应,江禀义艰难地咧了咧嘴权当微笑,眼圈却又红了起来。
“确实是我妹子,我今生只当她是我亲妹子。”
“林大人应是知道的,我本是厄骨朵部的人,从前的厄骨朵部,是受突伦奴役的下等人,地位之卑贱,连牲畜也不如。”
禀义又抹了一把眼泪,沙哑着嗓子接着说道:
“那时为了震慑厄骨朵人,突伦的贵族们还想出了一个办法,做‘人祭’,每逢有打仗或围猎之事,他们便要拿厄骨朵人先做‘人祭’。”
“‘人祭’是什么?”
小禀义轻抚着父亲背心,却忍不住出口问道。
“在厄骨朵部中选出一名奴隶,以铁锥凿破头顶,注入赤汞,使其皮肉分离。剥下人皮,绘以图腾,做祝祷祭祀之用,这便是‘人祭’。”
座中的所有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小禀义更是惊得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突伦本是极北雪域中的一支游牧部落,直到几十年前部落中出了一名军事天才乌木云邦,率领族中骑兵一气统一了朔北十姓部落才得以建国。
但其毕竟久居极北蛮荒之地,民族开化晚,是以贵族们仍以蓄奴为乐,蓄养的奴隶数量成为其身份地位的象征。
直到近十几年,一则受到大宸汉文化的影响,二则奴隶中也多有能人奇士帮助主子建功立业,是以对奴隶的残杀之事少了些。
以江禀义的年纪推算,他的少年时代正是残杀奴隶的风气最为兴盛之时。
“有一年我们服侍的突伦人俘虏了一群大宸难民,因为俘虏人多耽误了回家的行程,大雪下过之后有些难民便倒下了。她和她奶奶被丢在雪窝里,我娘见她们可怜,偷偷把她们藏在自己帐里,这才救下她们祖孙俩。她们感念这恩情,说要做牛做马服侍我娘。”
“后来有一年围猎,那突伦人选了我娘做‘人祭’,最后来捉人时她奶奶顶替我娘去了。再后来我娘也死了,卫帅带着怀远军将我们从突伦人手里解救出来……再后来我到了土奚律,她也跟过来,自己去铁勒王帐做了歌女,当我的暗线。她一直不记得自己名字,只知道姓曲……”
“何必要拼死去护铁勒王一家呢?遇到了危险应该找爹爹去救啊。”
小禀义不停地抹眼泪,话里带着浓浓的哭腔。
“她是知义感恩的人,想来是为了报答铁勒王对她的好罢。”
阿小想起昨夜带着小世子离开之时,曲伊人满脸凄苦和不详的神色,大约那时她便要一心赴死了。
“她可能真的心里仰慕铁勒王老爷子罢。”
小禀义目色柔柔的,仿佛看向极远的地方。
承晔心中一动,想起铁勒王落入棺木中的那滴泪。
即便是身为细作,铁勒王将阖家老小托付与她,是将她当做战友同袍了,所以她才会“为知己者死”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