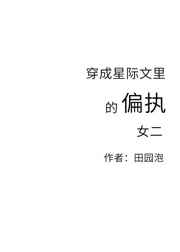光亮映照的圆圈中心,有一男一女两个……人?鬼?
他们穿着夸张的戏服,面上却是狰狞的面具,女子坐在一架单皮鼓前,一手握鼓槌,另一手拿着一只檀板,那男子青衫书生打扮,戴着龙头面具,站在女子身畔。
周正心下一阵焦虑,装神弄鬼的。
你们是什么人?
他想开口问,此时才发现张开口只有气流从喉中涌出,他发不出声音。
光亮中的两人发觉他的动静看过来,那女子手上一动,檀板声响。
她声音柔媚婉转,如同在唱戏一般拉长尾音说道:
“啊,书生,那位老爷醒了――”
光亮中的男子身形未动,也如同唱戏念白一般回应道:
“啊,小姐,如此我们就为他唱那一出戏来――”
女子接口唱白,“这出戏名叫做什么?”
男子道,“叫做富家翁误堪鸳鸯谱,薄命女偏逢薄情郎――”
呸!
看这男女二人一番做作,周正心火上涌。
他环顾四周发觉此地空间很小,烛光映照下可看见一门一窗。
他几步走到门边正要开门,却发现那木门纹丝不动,可能是在外锁死了。又跑到窗边使劲推拉,发觉窗户外好像被加固了一层,完全推不开。
这时才知是被人禁锢在此,强迫自己看这一男一阳怪气地做戏。
“咿,书生,这老爷不爱听戏呀――”那女子一咏三叹。
“因为啊,这戏里讲的是老爷的故事呀――”
周正皱眉,放下在窗上使力的两只手看向他们,方才说的意思是,戏里讲的是他的故事?
什么乱七八糟的。
周正心内冷笑,也不焦虑急躁,静静看着光亮里的男女。
那女子轻敲檀板,却是男子先说道:
“小生家道中落,幼时丧父,慈母心酸,五岁识字,十岁能文,十七岁上便赴京赶考而来……”
“哎呀呀,如何是好,银钱不够,小生进不了京城了!”
周正有些恍惚,进京会试是太久远的事,现在想来恍如隔世,好像自己真的把本就不多的盘缠弄丢了,一连十几日饥寒交加,险些就要死在异乡道旁……
一阵急鼓声催,仿佛敲在心上,周正想起那男子方才所说的戏名,忽地心跳加速。
女声柔婉天真,她轻叹一声,如梦似幻,“奴家翠眉,本是……”
翠眉如同一道闪电,裹着惊雷炸响在耳中,周正全身一颤,身子靠着墙瘫软下来。
他们知道翠眉啊。
“我的爹爹救回书生,奴看着他呀……”
光亮中戴着面具的女子纤手半遮面,似是娇羞,与前世记忆里的影子重叠。
而与此同时,心头也如遭钝器击打,疼得直不起腰。
“书生,奴将这银子送你上京赶考――”
“谢小姐。”
“书生,若是你金榜题名,可要记得奴家呀――”
“小生若此番得中,誓要迎娶翠眉为妻,此誓天地为证――”
周正眼前出现一个俏丽身影,女孩下巴尖尖,黛眉微蹙,她说:
“便是此次未中,也要记得回来,再过三年,周公子也必定能中。”
男子声音陡然升高,“我今高中,且回家寻翠眉来――”
“呜呜,骤逢祸患,奴的爹爹去了呀,怜命苦一人守家业,可是周郎,为何恩将仇报来害我?”
“你,你,你与那贼夫,凌霸乡民,鱼肉百姓。我,我,我乃是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有罪当诛!”
“冤枉啊――”女声凄厉号哭,“是刁仆欺我,毒害我爹爹,污奴家清白,又谋夺奴家钱财……”
周正额前冷汗涔涔,面上神情变得狰狞扭曲,口中呜呜连声。
真相不是这样,是他们污蔑!
他中进士之后第一时间回去找翠眉,得知她已嫁人去了延县。他自己想尽一切办法谋得外任,三年后如愿做了延县县令,仍想要寻找机会求娶翠眉,谁知她在当地已是臭名昭着。
满城都在议论她德行有亏,私通家仆,气死生父,在延县境内纵仆伤人,恶意涨租逼死佃农,那佃户走投无路到县衙击鼓喊冤,自己亲手审理,桩桩件件证据确凿,他无法徇私。
若说有一点点私心,便是那时已被她在外的恶名吓怕了,再也没有求娶的心思。不久后便由母亲安排,与家乡的一位郎中之女结亲,再也不敢记起前尘旧事。
光亮中的女子声音幽微如鬼魂,“周郎断了糊涂官司,娶了娇妻,得了万民伞,从此好风借力直上青云,周郎当得好官呀――”
那男子不再唱作念白,他透过面具看向周正所在的方向,沉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