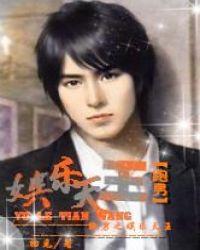赫城的发病人数还在增多,每天都有被抬来的村民,每天也有得不到救治而丧命的村民。
所谓医者仁心,吕安平的情绪是最先崩溃的。他在太医院里做太医,平日里也不过是给娘娘们号号脉,诊治这西京王公贵族们的头疼脑热,这到了赫城,一下子面对的可是数百个濒死之人。
营帐外几里地的小山坡上,呼延良找到了一个人跑出来的吕安平。
“再向南十余公里,便是与南齐的边界。”呼延良悄无声息地靠近过去,坐到了吕安平的旁边。
“我知道。”
“你若是想跑,也该往北,齐裕在边界部署了重兵,给的指示便是不允许有东西活着经此进入南齐。”
“齐裕是?”吕安平并不认得。
“南齐摄政王。”
吕安平笑了一下:“”
[太困了,今晚痛经了,明天再见吧……]
得到。”
又过了几日,贺兰敏之来来回回数趟,却仍无任何发现,呼延禹看着便也明白了,既然敏之狠不下心来,这个坏人把他来做。今日晚上,便选了她侍寝。看得出来,为了见他,贺兰敏之打扮了许久,呼延禹呼吸间皆是极重的酒气,湿乎乎地喷在敏之纤细白嫩的脖颈上。贺兰敏之缠住他,动情地吻上去,眼睛闭着,睫毛一颤一颤。
贺兰府这个女儿养得真的很好,呼延禹看着贺兰敏之,不止一次在心里这样想。敏之天真可爱,一举一动都极富少女的美好。就算后来嫁入王府,哪怕男欢女爱之事早有经历,可每每侍寝,呼延禹还是被她这种从内而外的少女纯真所吸引。她那么美好,就像方才迎接初春的花,怎么可以,止步于自己这片即将枯竭的土壤。
一场欢爱之后,贺兰敏之红着脸躺在他身上,看着呼延禹这就要起身下床,敏之知道他要做什么,便急急地抓住他的手。
呼延禹一愣,“做什么?”呼延禹不愿意要子嗣,起初府里的女人多是烟花女子,烟花女子常年用香,本就再难生育,呼延禹便也不担心。唯独这贺兰敏之,呼延禹最是担心,于是每次侍寝之后都要亲眼看她服下避子汤才安心。
“王爷,臣妾不想喝那避子汤了”贺兰敏之拽着他的手,求着情,“这避子汤着
说不明白的。
许是她大小就在本王身边长大,本王早就习惯身后有个小丫头跟着了。哪些日子若是没了她在身边陪着,便不适应。又或许是不知她哪一个抬眸,哪一个回首,恰好望进了呼延良心里,从此这人在心里住下了,便容不下其他人了。说不明白的。
许是她大小就在本王身边长大,本王早就习惯身后有个小丫头跟着了。哪些日子若是没了她在身边陪着,便不适应。又或许是不知她哪一个抬眸,哪一个回首,恰好望进了呼延良心里,从此这人在心里住下了,便容不下其他人了。
太困了,拜拜了,也没人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