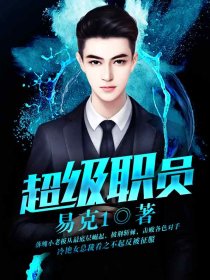李循矩回乡陪老父过年,才回京不多久就被皇帝抓差,整天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武令媺想见他都得提前预约。啧。
不过忙碌些也是好事,总比整天无所事事要强。武令媺从同福店里打包五菜一汤去送餐,李循矩和他家老爹李士廷吃不算少。
书院在二月十五开学,不过这会儿家在外地的学子已经到了不少。武令媺微服进门,也没惊动太多人,很快就到了李循矩的小院外面。
金生水去叫门,等了好久都不见有人应声。不对呀,书院的门房明明说李学士父子俩刚回来没多久。武令媺心里纳闷,等了一会儿,又让金生水提高了嗓门喊人,这才听见门里有脚步声响起。
来者是个清瘦文弱的四旬男子,一瞧他的面容,有眼睛的人便能知道他与李循矩之间定然有很近的亲戚关系。这位便是李循矩的父亲,李士廷。
李士廷的妻子是明辉贵嫔的堂姨,他算起来是武令媺祖父辈的人物。不过此人深受家学熏陶,行事务求符合身份尊卑,可不像李循矩那么放松地能以亲戚身份和武令媺相处。
一见外面久候的人是玉松公主,李士廷立刻跪倒,毕恭毕敬磕头请安:“下官樟县学政李士廷,拜见公主殿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几年过去,他也升官了。
武令媺苦笑不已,赶紧指挥金生水把李士廷给搀起来。她不敢以“姨祖父”的头衔相称,否则会把李士廷吓得叩首请罪不绝。让他去当皇帝陛下的姨丈,再给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
“李大人,我给您和小舅带了饭菜,你们还没吃吧?”武令媺当先在前往院子里走。李士廷微微弯着腰,小步跟在她身后。
“多谢公主殿下赐菜,下官和犬子感激不尽。”李士廷满脸惶恐。眼看到了里屋门口,他又抢先上前打起挡风帘,恭声道,“殿下请进。”
真是不自在啊,好怀念在这间小院里无拘无束的时候。武令媺暗自叹气。当看见李循矩规规矩矩垂手低头站在门边。她干脆叹出声音来。
这样可没办法好好说话,武令媺干笑几声道:“李大人,我与小舅有些话要谈。您不妨先用膳。”
李士廷立马点头道:“下官遵命,请殿下随意。”离开之前,他不忘了给儿子递去一个饱含警告的眼神,满篇都是“谨守规矩”这四个大字。
瞧见李士廷的身影消失于左侧厢房内。武令媺吁气的同时,也听到身后如释重负的吐气声。她转身同情地看着李循矩说:“小舅。你都被姨祖父管瘦了。”
确实,此时李循矩的脸色真不好。说是苍白嘛,武令媺又觉得还泛着点儿受了惊吓的青色。总之很不好。
板起脸,李循矩上手在武令媺额头轻轻敲落。低声斥道:“如此贫嘴,成何体统!”又扯扯嘴角算是笑了,“快进来吧。”
舅甥二人在桌旁分宾主落坐。李循矩面前摆着的都是他爱吃的菜,武令媺只啜饮香茶作陪。彼此时间都宝贵。也顾不得食不言了,李循矩咽下一口菜说:“祥王问题不少。”
“祥王府的奢华仅次于禄王府,但禄王那时建府是因军功由父皇特旨建造的。”武令媺对此并不惊讶,不屑地说,“欲壑难填,我瞧着四皇兄的腰越来越粗,想来是胃口一年比一年大的缘故。”
“好几年的帐都对不上,今天上午户部皮尚书已经主动进宫向皇上请罪去了。”李循矩脸色沉凝,皱眉放下筷子,“皮尚书仗着有祥王这个女婿,以前在部里一手遮天。这回被查出许多事来,他可真恨我入骨。”
武令媺颇担忧地说:“我先前最怕他们对你不利,才拨了内卫给你。从现在父皇的决心来看,即便没有你,也会有旁人去接这个差事。你的安全问题不大,倒是那些经年旧帐要保管好。虽然他们不大敢动大主意,但小手段必有。”
李循矩素来温和的眼里闪过几分厉色。他这几天的日子相当不好过。苦头不能白吃,他一定会替陛下替大周肃清这些国之巨贪!“你不必担心,陛下也派了人在我身边注意着。至于那些旧帐……”他翘起嘴角笑起来,“我自有主张。”
小舅向来是个有主意的,更不是真如表面所示那般温良无害。武令媺很庆幸这个帮手挺给力,眼珠转了转,她忽然笑眯眯道:“我今天去了同福总店。小草虽然没问,但我知道她挺记挂你的。”
不自在地咳嗽两声,李循矩重新慢条斯理吃菜,硬撑着就是不接这个话头。武令媺也没有再逗他,又闲谈了几句便离开,她还得去康王府瞧瞧。
将公主外甥女送走,李循矩的脸色立刻垮掉。就像积压着数百上千年的郁闷忧愁也似,硬生生让他瞧起来满脸的沧桑。李士廷从厢房冒出来,将院门关严实,扯着李循矩进了内间书房,打算继续方才的无声谈话。
这次回乡过年,对李循矩来说,最大的惊喜就是他的父亲李士廷终于答应离开家乡,随他进京安身立命。从此以后,父子二人就算是在京里重新开始新生活。
原本李循矩打算搬出鸿博书院,买套小院子居住。可李士廷不肯。李循矩知道父亲的心事。他们李家在京里原先是有一座住宅的,父亲大约想着把那座老宅盘回来。
但事情谈何容易。李循矩的祖父就任钦天监正使时犯了事儿,家产被抄,那座老宅早就被变卖出去变成别人家的房子。人家若是执意不卖,他们便无可奈何。
其实,早在李循矩正名为玉松公主唯一有血缘关系的母家亲人时,李家老宅的房契就由主人毕恭毕敬地送到了武令媺手里。不过武令媺拒绝了那人的好意,她认为这种深具意义的老宅还是要李循矩自己凭本事去买回来的好。
后来说起这事儿,李循矩对武令媺的做法表示赞成。他还罢了,从来没有在老宅里住过,想着的也就只是用自己赚的钱将老宅买回来。可是对李士廷而言,老宅还象征着——清白!李正使的清白!所以买宅之事不能等闲视之。
户部的差事太紧太重要,这些天李循矩都是天不亮就出门,半夜才回家。不要说陪父亲吃饭,父子俩就连面都难见上。今日中午他能回家,是李士廷亲自去户部“请”的他。
李循矩便知道父亲肯定是有十万火急的事儿要告诉自己,否则他绝不会跑去户部。回家铺开纸张,李士廷刚写到“为父今日去了老宅,与玄鹤令的持有人见了面”,就听得外面有敲门声音。父子俩吓得不轻,手忙脚乱收拾了东西才去开门。
现下把不速之客送走,方才的话题必须要进行下去。瞧着李士廷落在纸上的那一行行字,李循矩的脸色越来越白,呼吸更急促起来。
“玄鹤令已经出现,你有何打算?”李士廷如是写道,“祖父临终前的遗命,你还记不记得?!”
李循矩接过笔,在纸上写道:“孩儿不敢忘记祖父遗命!不知持令之人有何吩咐?”他很紧张,这些字写得潦草零乱。
“你想办法让玉松公主在皇帝陛下面前告泰王恶状,若能证明武赟嗣的吉兆加身是假的就更好。”李士廷看了儿子一眼,继续挥笔平静书写,“我知你与公主感情深厚,但你莫要忘了祖父的冤情。并且玄鹤令的主人对我李氏满门有救命之恩,当倾力报答!”
李循矩面露忿然激切之色,奋笔疾书:“报恩的方式有很多种!且以孩儿日后成就,未必不能替祖父洗冤,何必假手于他人?玉松公主深受陛下疼爱,若是她得知祖父的冤情,也不会袖手旁观。孩儿不愿意她涉险。若她与泰王交恶,日后泰王继承皇位,她该如何自处?”
用力推开李循矩,李士廷愤怒地瞪了他一眼,大声喝斥:“你虽然是公主的舅舅,但更是臣子,怎能不分尊卑上下?”手里扯过一张纸,飞快写道,“当年那事太大,玉松公主只是公主,于事无益!泰王今次必将受和王牵连,势必会降低他在皇帝陛下心里的地位。他想争夺储君,难。”
胸膛剧烈起伏,李循矩沉声开口道:“父亲的教诲,孩儿谨记于心。”手下写道,“祖父究竟因为什么犯案?父亲为何还不肯告诉孩儿?请恕孩儿不孝,若不能得知当年之事的真相,孩儿不能安心!孩儿想与持令那人见面,可能伤及公主之事,孩儿绝不去做!且孩儿……不愿做他人手中傀儡!”
他扔笔于地下,直挺挺跪倒在地,倔强地盯着李士廷。李士廷低头瞧着这个自小便主意大的出色儿子,无奈低叹道:“我要问过才行。”
李循矩大喜过望,向李士廷磕下头去,朗声道:“请父亲在家中安坐,孩儿要去户部办差了。”
“你切莫辜负陛下厚望,用心办事!”李士廷叮嘱几句,送李循矩出了院门。关上门后,他怔怔立在院中良久,这才拖着沉重步伐回屋。
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李士廷以为那枚令牌永远不会出现。却没想到,他还是迎来了这份沉重的责任。他是个孝子,是知恩义的人。父亲临终前的遗命他从来没有忘记。但他也是个疼爱孩子的父亲,如果有可能,他情愿承担这一切的人是他自己,而不是他的孩子。(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