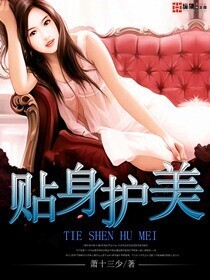“不是我!我再说最后一次,这件事与我无关,我也根本不知道有马车撞人的事。”
秦继博说得义正言辞,而刘添珩只当他说的是屁话!什么叫与他无关,也根本不知道有马车撞人的事?他的意思就是他们联合小乞儿在诬陷他咯?
这种事刘添珩从来只是想想,可从未做过!
“秦继博!你别再装了!这件事就是你做的!你撞了人就跑!不就是怕撞死了人,付不起责任!”
“你口出胡言!分明是你,还有那宋清松,雇了这么一个小乞儿来诬蔑我!”
......
宋红韵看着互相指责的两人,十分的头疼。不过他们两人,一个认为是秦继博担不起后果,一个认为是刘添珩挖陷阱冤枉自己。
总之都没扯上小乞儿的事。究其原因,还是身份问题。秦继博和刘添珩都不相信一个小乞儿会胆子如此大,去冤枉丞相之子,就不怕自己小命给折腾没了?
这时代,官官相护,平民出事尚且顾忌对方的身份,可能根本就不会去报官,更别说是小乞儿这样最底层的人。
能跟踪人,还指着对方说是对方的马车撞了自己,背后没人怎么可能?这是秦继博很合理的猜想。
“够了!”巡城御史硬着头皮打断了两个少年的争吵。
秦继博和刘添珩虽然是停下了,却是面色不善的瞪着对方,如不是顾及场合和身份,恐怕早就冲上去咬死对方!
巡城御史看向宋红韵,问,“这小乞儿被马车撞确有其事吧?”
宋红韵点头,“嗯,这小乞儿是送去国子监附近的医馆,大人您去查,很多人都知道这小乞儿被马车撞的事。”
“那你见到撞你的人么?”这句是问的小乞儿。
小乞儿虽自小便流浪在京城,一直是靠乞讨为生,未见过什么大场面,也少和达官贵人接触。可在鬼门关走过一次后,心性什么的都有了大大提升,以十分稳的气息道:“没有,我只是看见那马车上的牌子,和他马车上的牌子一模一样。”
“就是说,你只看见了马车上的牌子。”巡城御史在纸上记录了什么,又抬了眼,问:“那除了你,还有没有其他人看见?”
小乞儿似乎心里已经知道答案,眼神黯淡了几分。
“没有。”
“太不公平!”
宋红韵看着气愤不已的刘添珩,抬筷夹了一片竹笋放在嘴里,细嚼,一片清香。
语气也如那竹笋,淡淡的,“冷静。”
刘添珩双手捏紧成拳,瞪着宋红韵,“冷静?!我怎么能冷静,明明那撞人的就是秦继博,他怎么能什么事都没有?!没有赔偿,甚至连道歉都没有?”
“你有证据?”
“明明小乞儿都说了他看见秦继博那马车上的牌子,和撞他的牌子一模一样!”
宋红韵又夹了一片竹笋,真如认真品尝的食客,“除了这个呢?”
刘添珩哑然。
“巡城御史不是说了么,小乞儿是被马车撞的人,也只有他一个人看见车牌子,根本就不能证明撞人的就是秦继博。”
刘添珩憋了半天,还是气不过,“那就这样让秦继博逍遥法外了?!”
“不然?”宋红韵看着头发梢都满是怒气的刘添珩,道:“莫非你还要冲去把秦继博打一顿?”
刘添珩“哼”了一声,“要是秦继博不告我,我早就去揍他一顿了!”
哟,这小子还挺聪明的!
“快吃菜,一会儿菜凉了。”
“哎。”刘添珩叹了一口气,却不知道再叹什么。
这次的事件就是阶级社会导致的恶果。小乞儿是底层的人,对很多国子监的学子来说,是或有或无的东西。将之视为草芥。
所以撞了不在意,躺在地上生死不知也不在意。你瞧要是刘添珩躺地上,多的是人赶上去给他做人工呼吸。对了,这时还没人工呼吸。
总之,阶级概念太深,深入每一个人的心,别说现在,就是再往后。二十一世纪,依旧有这样想法的人,有发生类似的事。
宋红韵阅历深,早将这些看透,深知她一个人是改变不了这个世界的。她只能‘原谅’很多人,也原谅无力的自己。
只是,心还是有所不甘,她是御史的公子,是国子监的学子,日后更可能是朝廷官员。她将有能力,也有想法去改变一些。
莫非这次穿越就是给她一次能改变的机会?那她有没有能力去改变,改变这个时代?
宋红韵敛下眼,嘴里的竹笋一下失了味道,面对一桌子的好菜,有食不知味。
翌日,柳延茗从刘添珩口中知道这件事后,脸上半分情绪没有。没有惊讶,没有愤怒,没有无力感,甚至连一点理所当然都没有。
宋红韵暗叹,柳延茗果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又或者,柳延茗比她更清楚这个阶级社会的残酷和无奈。最开始,他不就马车和她说过这件事吗?
想她一个几十岁的老阿姨,到头来还没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儿看得透,还真是有愧有愧。
但瞧一旁还一脸我很生气的刘添珩,她突然又觉着心里有了安慰。
“对了。”
最擅长补刀的柳延茗出声了,宋刘都紧张的看着他,“今天有音律课,你们都做了准备没有?”
宋红韵还不明这个做准备是什么,一阵哀嚎如魔音灌耳。
“什么?!天呐!”
清风拂面,头上的桃花树骚动,桃花一瓣瓣飘落,一瓣落在前方同窗的肩上,一瓣落在面前的古琴上。
宋红韵轻轻拂去琴头的花瓣,重新看向前方的夫子,教学音律课的秦夫子。
或许专攻音律方面的缘故,秦夫子虽长得只算作清秀,却自有一番气质和风骨,令人流连。
古琴是国子监给学子专配的,确保每一把都一样,当然,学子家里也是交了钱的。
约莫在一刻钟前,他们抬了桌子凳子,拿了琴,摆在教室外面的桃花树下,学习弹琴。
因为秦夫子是一个讲究意境之人,说今日天气如此好,就在外面教学,不愿进那方方正正的教室,束缚了心。
不得不说,搞艺术的当真是任性无比。
古琴是古时最热门的乐器,以及文人最推崇的艺术技能,从琴棋书画,琴排第一位就知道了。
且古琴、古筝还有琵琶,以前都是男子所弹,只是后面青楼女子为了谋生,习了这等乐器,渐渐女子才多了弹琴之人。
不过越往后,会古琴的人倒真是女子更多。但真论,这古琴,还真男子能弹出起气势和感觉来。
“宫、商、角、徵、羽......你们已学了一段日子,现在先自己练习一下,等会儿我再教你们曲子。”秦夫子安排着任务。
底下学子应着,“是,夫子。”
然后说不出什么声音,大家都各自弹奏起来。绝对不好听,但也不难听。
秦夫子应是长期泡在房里研究琴术,皮肤极白,加上那一袭白衣,明明晃晃,有些刺眼的站在了宋红韵的侧旁。
“你是宋清松?”
宋红韵被这一声问,吓得心肝儿都颤了一下,“是,夫子。”难道宋文瀚大兄弟连音律课的夫子都打点了?
“你刚入学吧?”
“是,夫子。”宋红韵还是规规矩矩的回着。
“之前学过琴吗?”
总算是问到了正事,宋红韵心里松了一口气。似乎不是宋文瀚,而是一般夫子怕新入学的学生跟不上进度,所以来循例问一句。
回忆宋红韵的记忆,回忆小说的情节......“嗯,学生有学过。”
“你简单弹来我听听。”
简单弹来听听,就是秦夫子想看看宋红韵手法如何,对音调掌握的能力,基础是否打好。
而宋红韵,倒真是没怕的,因为她自小学习古琴,曾拿过十级,如不是因为家庭经济问题,真会一直弹下去。
但就算如此,平日心情甚好时,也会搬出快积灰的古琴来弹上一两曲,不至于多生疏。
“好。”宋红韵点头,起势,勾弹。
古琴演奏时,你的五官和四肢的形态动作,都有一定的规范。就是你的精神、思想,甚至呼吸都不能散漫粗野,如此才能达到一个妙境。
尤其是在初学的时候,必须打好基础,再习练纯熟,以免日久习惯成性,难以更改。
宋红韵的基础打得极好,当时教她古琴的老师十分喜欢她,有拿关门弟子那般教,对她极其苛刻。一个动作都不能错,一个呼吸都不能乱。常在琴前,一坐便是几个小时。而那时才几岁的宋红韵也真的熬下来。
最初时的确是很艰苦,也很难熬,但往后宋红韵便感觉到基础打好的好处,其他与她一起学的人,和她的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当宋红韵弹古琴时,一旁看着的秦夫子,眼睛有一亮。
好,好苗子!
虽然秦夫子说是简单弹弹,但宋红韵摸上琴弦时便感觉到一股熟悉,心静下......大指按弦,食指弹弦,左右手指取势。
她就像回到古琴老师每每给她补课的午后,斜斜的阳光打进,漂亮的橙色,粒尘在空中舞蹈。一旁有尊敬的老师听她弹琴,而她,认真努力,不敢有一丝放松。
就像处于一个心境中,一切都忽视,宋红韵弹了一曲每次开始练习前,总会弹的曲子。虽简单,却极其考验基础。
等宋红韵一按弦结束时,眼中还有未抽离的沉迷。
直到秦夫子出声,“好,很好。”
她才回神,微微低头,道:“学子不才。”
秦夫子问,“你是否常弹琴,我见你功底甚好,不知师承为何?”
哦?打听老师了?不过她还真不大记得教宋清松古琴的夫子是谁,那都是几年前的事。
且基础教过后,宋清松因为身子的缘故,就很少弹琴,废力气,所以宋红韵只道:“是家父请的启蒙夫子,只教了学生入门。”
“哦?”
宋红韵能听出秦夫子的语气略带惊喜,“那你还会弹何曲子,弹来我听听。”
纳尼......宋红韵愣了愣,夫子,您这个要求就有些过了哈!
这儿上课呢,让我弹曲子给你听? 国子监女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