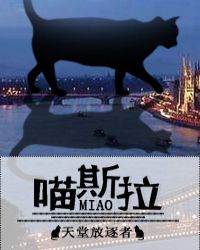十月初六,庚子日。
妇息在寝宫中独处了一晚,满怀悲愤。
没有人应答她的呼喊,在天明之后,一个不认识的宫人默默送来朝食,对她的问话听若未闻,被她逼问得急了,竟挣脱她,仓皇逃走,带得妇息跌落在地也不顾。
好容易捱到午后,妇息终于等到了子敛的到来。
“大王!”妇息见是子敛进来,盈盈跪下,低声叫了一声。
与大王——现在该叫帝小辛了——接任王宫时一样,子颂全盘接受了帝盘庚的后宫,子敛也一样会接手帝小辛的后宫。
从昨日起,妇息已不再是大商的王后,而是子敛后宫中一名普通的妇人。
王后将会是那个不爱作声的妇微了。妇息咬咬下唇,无声叹息。
“起来吧。”子敛脱了锦里革面的赤舄,仅着布袜走了进来。
宫人看到大王进来,连忙跪倒在地。
“你们都出去吧。”大王淡淡说道。
宫人听到吩咐,一礼告退。
寝宫中只剩子敛和妇息。妇息幽幽道:“大王身系天下,已经忙碌一日,还要来看……”
“脱掉衣裳!”子敛没等她说完,打断她的话,语气中有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除了生母,继位的儿子可以全盘接受父亲的妻妾,是为烝;弟弟继位,可以接纳兄长的妻妾,是为报。烝婚、报婚作为免于财产分割的手段,不独王室这么做,在民间更是常见。
子敛接手王宫,妇息知道自己会成为新王的女人,只是没想到,子敛竟如此简单直接,没有任何多余的话。
妇息觉得屈辱,在子敛审视眼光下,忍住泪水,脸上尽量不露出悲喜。
若是现在还能被大王的炽热眼神这般注视,一切会有什么不一样呢?妇息心中想道。大王已经不在了,巫亘给画儿的毒酒没有毒死画儿,却毒死了大王。
曾经的爱侣,却一心想要毒死她唯一的儿子,她觉得给巫亘的那一记耳光还不够解恨。
子敛走到她的面前,伸开双手。妇息楞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低头给子敛宽衣……
“难怪帝小辛如此疼你爱你,食髓知味,换了我只怕也是如此。”子敛从她身上起来,穿好衣裳,脸上仍是难以捉摸的淡笑。
子敛从床榻边走出几步,端坐在案几后面,看着还慵懒躺在床上的妇息:“如此姿容姝丽,柔美、娇媚、妖魅,悉得其妙,难怪子见也被你迷住,最终行差踏错。”
后面这句吓得妇息从被子里面腾地坐起,像看着神怪一样看着子敛:“你……你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子敛似乎带着戏谑地笑看着她,门窗紧闭,油灯昏暗,她看不真切。
“不!我不知道。”自从得知是巫亘害死了大王,妇息对之前想方设法要置之于死地的子敛反而并不憎恨,只是觉得天不假其便,让子画永远失去了王位承继的权力。
“你和子见多次在复庙中偷会,你以为没人能知道?”子敛由之前淡淡的语气,变得阴冷而森然,“你以为你鼓动子见意欲谋害于我的事没人知道?!”
“连一向不问细事的小辛都知道了你和子见的事,你以为还有谁会不知道?”
子敛一连串的反问,让她无言以对,也无颜以对,心中只想着:“大王也知道了吗?大王也知道了吗?”
妇息扯起被子捂住脸,嘤嘤地哭了起来。
子敛也不说话,等妇息的抽泣声变小,才接着说,语气又变回惯常的淡然:“一切原本都好好的,一切原本都应该好好的,却因为你的贪念被弄糟了。”
妇息抬起头,看着端坐在案几后面,斜斜地对着她的子敛。这个男子,才从激情中脱身,却波澜不惊,表情平静。
妇息几乎可以肯定,子敛现在的平静是装出来的,因为她听出子敛的话中带有深深地恨意。
“小辛本可以好好地做他的大王,虽然他算不得英明睿智的王,但大商在他的手中,没有变得更糟,拓疆不足,守成也艰难,但至少邛、羌、犬、土、彭诸国,无力进攻中国。如此局面之下,小辛完全可以做一个太平之主,和你,或是和那个顾方进贡来的小女子享受床笫之欢,远好过现在孤寂地躺在地下。”
子敛不是一个多言之人,但妇息惊讶地发现原来子敛原来也有话多的时候。
“子见本来也可以好好的,安心做他的多马亚,以他的武功,也许还能在对敌之时立下更多的战功,不会有那么多事,不会去试图用如此拙劣的方法来加害于我。子成……”子敛说道子成时,顿了一下。“子成原本也能可以好好的做他的王子,当一个王都纨绔,虽不会有大出息,但与人无争,一样可以在醉生梦死中慢慢老去!都是因为你的贪念……”
“不!我没有杀子成!”妇息几乎要喊出来。
“我知道你没杀子成,但子成因你的贪念而死。”子敛仍言辞缓缓,听不出喜怒。“子成是我叫人杀的。”
“你……?你疯了!”
虎毒不食子,而子敛居然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妇息觉得自己快要疯狂了——或者是这世间的人全都疯狂了!
“不,是你疯了!”子敛突然厉声道。“若不是你发疯似地想要让子画为小王,若不是你发疯似地想着要进复庙,怎么会有后来的这些事?”
“原来一切都是你!原来……”妇息身子发抖,两手紧紧的抓住被子的边沿,喃喃道。
“不错,都是我!”子敛站起来,走到床榻边,俯视着她,眼光中透着疯狂的炽热:
“三十日前,我在自己的府上刺杀了自己,不为别的,就是要试探长老们的动向。我想过,长老们商议时,若支持大王居多,我就死,我会真的杀死我自己。”
子敛顿了顿,接着说:“我不怕死,我要的是大商的平安。但长老们的犹豫更让我害怕!”
“你怕什么?”子敛的狂热让妇息感到害怕,身子竟止不住微微颤抖。
“帝阳甲结束九世之乱后,曾对我们兄弟三人说过,九世之乱中,没有定见的人、摇摆难安的人最可怕。”子敛目光一下变得遥远,似是想起久远的事,忽然目光一敛,瞬间变得狠厉:
“你知道九世之乱中,我商族多少好儿男死在同胞的戈矛之下吗!你知道若是打乱自阳甲、盘庚二位先王立下的规制,还会有多少商族的儿男会死在自己的同胞手中!?”
“我叫人杀了子成,只是让大……小辛知道,若是立子画为小王,引来的只会是兄弟反目,骨肉相残。”子敛呼吸急促,妇息低着头也能听到子敛说话时的喘息。“小辛收到我发出的讯息了,以为子成死于你手,但他舍不得你,只好对我说,我们始终是兄弟,并将子画送到战场上去,离开王都,以此来表达他的诚意。”
“在昨日以前,我一直很遗憾郑达没能查出真相来。这世间所有发生过的事都是真相,谁说一定都会被人知道呢。比如今早的鸟儿欢快的叫唤,谁能一定知道是因为昨晚一场欢快的交酉已,抑或是因为今早的几只肥美虫子?”
子敛看着躺在床榻之上的妇息,口中说着轻佻的话,眼中却全无轻佻之意,反倒有不易察觉的沉重:“但现在我很遗憾郑达查出了真相,所有的真相。”
“今天我叫人去找他却没找着,他离开了,我很遗憾。山泉清澈,出山了却会变得浑浊。郑达赤诚,是我见过的成人世界中最后的一捧清泉。作为弼人府主事,他见过世间太多污浊,却始终保有赤子之心。说实话,我很羡慕他,很羡慕!”
子敛看向屋梁上的雕花,雷纹卷曲反复,愈盯视愈炫目,他的目光再次变得遥远,或者说是空洞:
“我曾经也是清澈的山泉,可是从我‘刺杀’自己的那天起,那天是壬申日吧,从那时候起,我就很讨厌自己。”
妇息抬头望着子敛因扭曲而显得狰狞的面目,心中害怕:“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他告诉我这些,该不会是因为要杀死我?
妇息越想越怕,身子抖得越发厉害。
右相收回目光,也转回被思绪带偏了的话题,不再说郑达:“但小辛却没想到我会有怎样的顾虑!若真是你策划了这些,你难道会因此收手?而他……他却心疼你,舍不得把你推出来!他甚至选择不去过问!”
“原来你杀死自己的儿子,却藏有如此多的后手,你是逼大王……”妇息不敢相信的看着子敛。
“若是事情仅止于此,哪怕小辛不去追究你,我也不会有后面的行动,就不会有后来的事了,偏偏你不!作为子画成为大王路上的拦路石,你对我是必除之而后快,所以你又愚蠢地去勾结子见来谋刺于我!”子敛眼中射出仇恨的光,刺得妇息不敢对视。
“我不想死,也不能死!所以我只能反击。”
“除掉我,你的下一个目标一定会是子见,因为他本身也是子画登极路上的拦路石。我甚至能够猜到,你除去子见的借口就是图谋大位,谋刺右相。”
妇息无语。这正是她当时内心的想法。
“一个愚蠢的人,找到一个笨拙的人,却想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怎么可能!”子敛语带轻蔑。“若非我高看你,以为你会放手,我怎么会无端端杀掉子成!若非你的愚蠢,怎么会害死子见的性命,又让小辛的性命白白死掉!”
“子见几次想要谋害我,他必须得死,那是我对你的警告,只是没想到你也要动手灭口,倒让我身上少背负一个杀子侄的罪名了。”子敛说道这里,像是突然想起什么,兴之所至的随口一言,问道:
“对了,妇息,你一定很纳闷派去杀子见房中小奴的人为什么一直没有向你回报,对吗?”
妇息抬头惊愕地看向子敛,带着不可思议的表情,这是她最大的隐秘,知道的只有妇操一人。
“因为那小奴是我的人,你要她毒杀子见,她得到消息就来见我,我知道,以你的性子,她一定得死,但我知道郑达很喜欢那名小奴,舍不得让她便死,只好杀了你派去杀她的人。”
右相起身来回踱了几步,然后又坐了回去:“昨天郑达问我这些的时候,我没有告诉他真相,因为真相太残酷,他会受不了。我告诉你这些,只是因为我觉得你该知道真相,知道自己有多么愚蠢!”
“真相太残酷,所以你要告诉我真相?”妇息口中喃喃念道,不知子敛为何这么说。
子敛的话中带着愤怒和淡淡的哀伤:“这世间的真相远比人们所能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要复杂得多,也阴暗得多。所以,我没有告诉郑达真相。”
子敛顿了顿:“最好永远不要追问真相。郑达以为他得知了真相,心灰意冷带着那名小奴出了王都。我不知道他会去哪儿,我只愿那名小奴足够聪明,不要告诉郑达真相,让他对人世绝望。”
“我给了那名小奴不少货贝,免得郑达带她离开时两手空空。他们已远走高飞,过他们自己的日子去了。你原本能好好的过日子,也该好好的过,但你太贪心。”
子敛想起兄长死去时的惨状,续道:“贪欲是这世间最毒的毒药。就像是大漠中饥渴的旅人,看到一汪泉水,明知有毒,也忍不住要喝一口。妇息,你中了贪欲的毒,我也是。”
“这毒药不比乌头,片刻间就会让人毙命。”
他的兄长,那个而今应该叫小辛的人,死的样子很难看,上吐下泻:
“事实上,颂并不贪,颂在这世间迷恋的只有美色,与子见一样。害死他的不是贪念,是欲念。你也会死的,死于你的贪念!”
妇息咬牙,恶毒说道:“难道你就不是这样?难道你就没有贪念,就不会死于你的贪念?”
“是啊!”子敛长叹一声,“活了这么多年,我终于抛弃了自己一直坚守的,成了自己不喜欢的人。你说的对,我也会死,也许同样死于贪念,但你会死在我前面。正是因为你,我才成了这样的人,成了郑达厌恶的人。他离我而去的时候,他的眼神中分明有不屑,有轻蔑。”
子敛的目光和语气中消散了狠厉,竟有虚弱:“说实话,我很心痛。我本不该这样的。在这一点上,我还不如颂。”
听子敛说起大王,想到大王死时的惨状,妇息又哭了起来。
这一刻,妇息才惊觉,原来这世间最爱她的就是大王,而大王在时,她习以为常,却忽视了那才是她最该珍惜的。
“那日,若非巫亘替我动手,我也会动手的。”子敛阴阴笑了一声。“若我一直被动防着你们,总有一天,会因为一个闪失,丢掉自己的性命。所以,那日我已经安排了射手,瞄着小辛。只是巫亘替我动手了,倒算是免了我弑兄的恶名。”
“你知道我安排的射手是谁?”子敛当然知道妇息猜不出,问了后,自己又答道:“是寒嬉一心想要杀掉的计五,射术神乎其技,我所见的人中无有出其右者。”
“你该知晓我因何对你说这些。”子敛负手踱了几步,“我只是想告诉你,你若愚笨,便不该有贪念;你若有贪念,便不该如此愚笨!”
“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这话,妇息听得出子敛是咬着牙说的。
妇息冷笑:“你一直就想动手,我的存在,不过给你动手的理由罢了。”
子敛指尖在案几上轻敲,半晌言道:“也许你说得对,但是一切都发生了,这,并不重要!”
“所以呢,”右相大人,不,是大王,枯瘦的手指在案几上轮番轻敲,不知是得意还是因为在思考什么:
“所以,你得死。!”
妇息掀开被子,赤身朝子敛扑过去,却终于不敢上前,隔着案几,张牙舞爪对子敛大喝:“你之所以成为你,不是因为我,不是因为其他人,其他事,你成为这样,因为你就是你,你心底就是这样的人!”
“也许吧。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究竟怎样才是对的。但我知道,我总不能白白让你算计死!”右相不理妇息虚张声势的质问,站在窗口,屋外的光投进来,映出背影很寂寥:
“这一点上,我还不如我的好哥哥,颂至少做了他想做的人。”
她知道,子敛和她说这些,必不会留她再活,除开大王,她现在唯一可足珍惜的,只有子画。妇息一念至此,声气忽然弱了下来,赤身跪在地上,叩头不止:
“大王,求大王放过画儿,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没做!”
“我从没想过要对子画怎么样。”子敛转身,似笑非笑看着妇息,“难道你没发现吗?子画对我很亲近,远超他的父亲,不,现在应该叫他‘小辛’了。”
子画素来敬仰子敛,与他亲近。
想到自己的儿子竟可能被眼前这个人抢走,妇息从心底冒出一股寒意,起身指着子敛的鼻子大声喝骂:“你卑鄙!”
“卑鄙?”右相冷笑,“你叫猛父引诱阿广杀我的时候,可有想到这个词?”
妇息愣住。
利用右相的亲卫刺杀右相,这个主意是猛父提出的,妇息从点头准许那一刻起,便被勾起心魔,一步步走向深渊。
子敛不再说话,他今天已经说得够多了。
他整了整衣裳,朝门口走去,手搭在门栓上,犹豫了一下,回头看着妇息,对她说:“我不愿多造杀孽,不然也不会以子成之死来唤醒小辛。你可以见子画最后一面,你若真愿子画以后能过得快活,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总该知道的。”
子敛叹一声气,开门走了出去。
一会儿,寝宫中进来几名宫人,妇息一看,居然没有一个是她认识的。 王都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