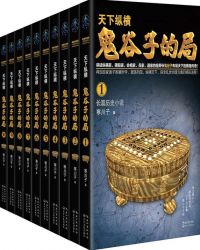“是呀,是呀,贤侄说的是!”子启的话音尚未落地,彭君、射皋君连声应和。
王叔没有说话。
一阵长长的沉默之后,王叔抬头,看向子启:“贤侄,你去一趟靳大人府上。”
“做啥?”
“咱这生意,靳夫人出有本金,今朝结账,她没来。你与彭叔算一下,将她的利钱结了,送她府上!”
“二哥,咋结哩?”彭君小声。
“三倍利!”
“这……”彭君吧咂一下嘴皮子,“满打满算,搭上人工,我们才赚两倍利,其他人只结一倍,我们这却给她结三倍,净赔不说,若是漏出风去,咋个解说呢?”
“算账去吧。”王叔眼睛闭上。
于靳尚来说,自昨日凌晨被怀王叫走,直到此时回家,一连十二个时辰,每一个时辰都是熬过来的。
左徒这个席位,无论如何排序,都该是他靳尚的。自十六岁那年当上太子侍卫直至今日,一晃竟是二十来年,即使没建功勋,苦劳也是该的。可它……偏就在眨眼之间,也在他最不经意之间,轻轻飘飘地就到了他屈平的屁股下面。他屈平有何能耐?不就是能写几首诗赋吗?什么长策短策,完全都是胡闹!
靳尚越想越是郁闷。后晌,屈平请他入府议事,没议多久,他就头疼欲裂,额上沁汗,极是难受。屈平急了,请来医师诊脉,医师说他虚火攻心,开出几剂去火的药,让他回府煎服。
靳尚提上药包,驱车回府。
家宰迎上,靳尚将草药扔他怀里,要他煎熬,转身走向寝处。这辰光,他什么也不想,只想美美实实地睡上一觉。他晓得为啥头疼,因为昨夜里他自个儿折腾一宵,根本就没有睡。
天尚不黑。
靳尚走进内室,边走边脱官袍。
响声惊动室内,一阵凌乱过后,一人噌地跳起,啪地关上什么,一屁股坐在上面,待看到是靳尚,方才长长地吁出一气,连拍胸口:“哎哟我的娘耶,你这是要吓死人哩!”
是他夫人。
“咦,”靳尚将官袍脱下,挂在衣冠架上,走到榻边,在榻沿上坐下,看向她,“大白天的,你不在外面招呼家事,守在这儿做啥?”
“嘘——”靳夫人打个手势,指指屁股下面。
靳尚看过去,是只精美的礼箱。
“哪儿来的?”靳尚盯住箱子。
“天老爷送来的!”靳夫人压抑不住兴奋,“夫君,你猜,箱中盛着何物?”
“丝绸?”靳尚踢掉靴子,躺到榻上,拉被角盖住肚子。
“不是。”
“珠玉?”
“不是。”
“猜不出了。”
“哎呀,瞧你笨的。本夫人提示一个,黄颜色!”
“不会是金子吧?”
“哎呀夫君,你真是灵光哩。再猜猜有多少?本夫人先提示一下!”靳夫人伸出三个指头。
“三锾?”
“不是。”
“三十锾?”
“不是。”
“总不会是三百锾吧?”
“哎呀夫君,你真是灵光哩!”靳夫人啪地打开箱盖,“夫君请看,黄澄澄的,方才我正在数哩!”
天哪,是三百锾金!一锾为足金六两,三百锾就是足金一千八百两!
靳尚噌地从榻上跳起,一步跳到箱前,看向箱中,果是一箱黄金,一锾一块,码得满满的。
“哪里来的?”靳尚屏住呼吸,盯住她。
“本夫人赚来的呀!”靳夫人不无自豪,“甭以为就你会赚钱,是不?”
“你……”靳尚高度紧张,“怎么赚来的?”
“本夫人将咱家中的余钱投作本金,这些只是利金,本金还没收回来呢!”
“利金?三百锾?”靳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顷,盯住她,“多少本金?”
“一百锾。”
“一百锾?利金三百锾?”靳尚闭会儿目,“放进去多久?”
“三个月,一个月净赚一百!”靳夫人压低声音,“夫君,你再猜猜本夫人是投给谁了?”
“谁?”
“王叔呀!”靳夫人压住兴奋,“三个月前,王叔夫人寻到我,向我讲起一笔生意,稳赚不赔,问我要不要投点儿。王叔的生意,谁能傻到不做?本夫人二话没说,就让家宰盘查账目,将所有的外账全收回来,刚好凑够一百锾,亲手交给王叔夫人了。嘿,我还担惊受怕呢,一直没敢对你讲,没想到才三个来月,就赚这么多!”
“唉,”靳尚长叹一声,“夫人哪,你……”摇头,“赚这三百锾不打紧,可就把你的夫君拖进坑里了!”
“啊?”靳夫人震惊,“啥坑?”
“说给你,你也不懂,唉!”靳尚复叹一声,退回榻边,咚地躺下,拉过被子,蒙头盖上。
将三百锾金送给靳夫人之后,子启憋着一口闷气,径直回府,从府宰口中得知,有人在客堂候他多时了。
子启大步走进客堂。
闻声迎出的是车卫秦。
子启晓得车卫秦是为何而来,硬着头皮见完礼节,拱手笑道:“上次见面,一晃竟是月余,芈启方才还在与王叔他们念叨车兄,说要得空寻访车兄呢,车兄可就来了!”
“谢公子挂念,”车卫秦回礼,“在下早说来拜望公子并王叔的,可公子晓得,要将那些犁头运到咸阳,真还不是个易事,方方面面都得安排呢。好不容易脱出身,在下紧忙赶来。”指向一侧,“公子请看,在下为公子并诸位王叔带来什么了?”
子启这才看清堂中靠柱处摆着四只箱子,箱盖上打着封条。
子启晓得箱中是何物,却作不知,看向车卫秦。
“前番那四万张犁头,张相国并几位王室公子尽皆验过,赞说货真价实,正好用于秋耕。公子晓得,关中多种冬麦,寒露之前,秦国最大的农事是耕地,老秦人为此不知吃过多少苦呢。今年得了这些犁头,老秦人可以松口气了。”车卫秦指着箱子,“箱中之物是第二批三万张犁头的一半费用,另外一半,在下使人送射皋君府上了,主要是为避嫌。”
“货还没送呢,怎能收款呢?”
“我也是这说,是於城君一定让送。”车卫秦摇头,“唉,於城君是性情中人,不晓得生意是怎么做的,只觉得与公子与几位王叔投缘。前些日大王出兵征伐,驻守於城的魏将军出于不得已,在淅水与景将军起场冲突。尽管是出于无奈,但毕竟是有所得罪。於城君怕公子与几位王叔心生不快,定要在下先付款,后验货,好让几位王叔定心。於城君向来一言九鼎,在下不敢有违呢!”从袖中摸出一册,“箱中之物,详细账目皆在此册,公子可让下人拆箱验证,万一缺斤短两,或货色不纯,在下再行补偿。”双手呈送账册。
“谢於城君,谢车公子信任!”子启接过,置于案上,拱手谢过,做出一个苦脸,长叹一声,“唉!”
“启公子何以长叹?”
“车兄啊,”子启复叹一声,苦笑,“这几箱东西怕是还得麻烦你再带回去!”
“哦?”车卫秦惊愕。
“车兄请看这个!”子启缓缓掏出王命诏令。
“呵呵呵呵,”车卫秦读过,将诏命递还,笑过几声,“这个诏书,於城君已经料到了!”
“哦?”该到子启惊愕了。
“不瞒公子,”车卫秦压低声音,“於城君之所以预先送出这几箱东西,就是想到大王会出这个诏命。”
“可诏命一出,生意是没办法做的!”
“哈哈哈哈,”车卫秦笑道,“看来公子是没有读过《易》啊!”
“此话怎讲?”
“什么叫《易》呢?易就是变。什么是变呢?变就是通。变则通,不变则不通。自古迄今,上有王命,下有变通,这是万古之理。”
“这……”子启眼睛眨巴几下,“怎么个变通?”
“敢问公子,大楚的关是怎么禁的?”
“是关卡里禁的!”
“公子交货时,不走关卡不就得了!”
“这……凡是大道,都有关卡,不走关卡如何能行?”
“大道设了关卡,小路呢?旱路设有关卡,水路呢?在这大楚地盘,依公子的身价、才智,公子若想做什么,有谁能拦?又有谁敢拦?何况还有王叔,还有那么多的大楚封君,常言说,法不责众,无论是谁,都不会傻到断绝所有人的财路,是不?”车卫秦压低声音,“就公子所知,秦法严酷不?可公子也都看到了,来与公子做犁头生意、闷头发大财的都是什么人?皆是王亲,像在下这样的,尽管是功臣后人,也只能是个跑腿干活的料,人家赚大箱银子,在下也就是赚点儿血汗铜钱。所有这些,你以为秦王他不知道?他清楚得很,他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他不能不闭呀!因为这些人中,哪一个都与他秦王连着筋、通着气、和着血呢!”
“那……”子启怔了下,“启却听说,秦法不容情,连太子犯禁,也都……”顿住。
“哈哈哈哈,”车卫秦又是一番长笑,“这你也信?什么叫法?法是王颁的。王可颁法,自然也可断法。再说,王的法是哪儿来的?是大臣拟写的。哪一个臣能蠢到写出一个连自己也一并在禁的法吗?不可能。哪一个王能颁一个连他的家人违禁也要杀头的法吗?不可能。自古迄今,所有的法都是颁给百姓看的,都是吓唬百姓用的!譬如说当年太子犯禁的事,你以为是真的惩罚?是先君做给天下人看的!刑嬴虔的鼻,割太子的发,杖公孙贾的屁股,都是商量好的,为的就是做给天下人看看,让他们守法!秦国的事你也都看到了。秦法是商君搞的,先王在时,商君难道就没有违法过?可商君受过刑吗?执商君法的所有人受过刑吗?没有。商君之死是在先王崩天之后,商君功高震主,叛乱谋变,方今秦王才杀他!”
车卫秦一番大论彻底震慑了公子启。
“受教了!”子启抱拳,看向四只箱子,“在下相信公子,箱中之物,在下暂且收下,量数就不必验了,公子莫要多付就是!”
“哈哈哈哈,”车卫秦畅笑几声,“在下不是於城君哟,付多一锾,就得自赔一锾哟!”
二人说笑几句,天色已晚。子启要安排宴席,被卫车秦拦住。
“启公子,”车卫秦笑道,“在下此来,一是履於城君之命,二是还想与公子搭伙做个买卖。”
“这个好哩,”子启鼓掌,“芈启别无他好,只对赚钱的事有兴致!”倾身,“什么买卖?”
“公子若有雅兴,就随在下走一遭!”车卫秦拱手邀道。
子启召来府宰,将账册并四只箱子交付他登记入库,跳上车卫秦的辎车,随他来到郊外一个隐秘处所。
迎接二人的是天香。
宴席没上多久,车卫秦借故走开。天香施展本领,将子启勾了个神魂颠倒,喝了个酩酊大醉。
半梦半醒之中,子启领教了天香的房中绝技,惊为天人。
翌日晨起,用早膳时,车卫秦来了,带着秋果作陪。
用完早膳,天香、秋果携手离开。
“启公子,”车卫秦盯住他,笑道,“昨晚睡得好不?”
“啧啧啧!”子启连声赞道,“这女人简直是个天人!”压低声,“不瞒你说,在下也算是阅女不少,可此女这等功夫,在下真还没有历过呢,真叫个妙不可言哪!”
“哈哈哈哈,”车卫秦笑道,“公子是个识货人哪。”凑近他,压低声,“公子可知一个叫天竺国的地方吗?”
子启摇头。
“那个国里的女人,擅长房中之术,叫六十四艺,艺艺惊人。昨日陪公子的叫天香,幼年流落西戎,遇到一个从天竺国来的巫人,得学此艺,公子昨夜体验,不过是区区几艺而已。待咱这个生意立起来,公子就可体验所有技艺,在下保管公子欲仙欲死呢!”
“天香就是天竺国的香了?”
“正是。”
“啧啧,”子启赞道,“怪道她这般厉害!”
“不只是她一个呢!”车卫秦应道,“天香手下有几十名女子,个个皆知六十四艺!只要公子有此意向,你我合力在郢都立个香楼,保管生意好做!”
“成!”子启伸手。
二人紧紧握手。
“早膳你带来的女子,又是何人?”子启问道。
“公子相中了?”
“呵呵,”子启笑了,“这倒不是。只是车兄带来之人,想必都是不一般的!”
“公子眼毒啊!”车卫秦竖起拇指,“此女将是我们香楼的第一品!”
“哦?”子启惊道,“她有何艺?”
“应该没有艺吧。”
“啊?”子启愕然,“没有艺,为何是香楼的第一品?”
“因为她是一个人的义女!”
“谁的?”
“苏秦!”
子启两眼大睁。
“她还两次救过一个人的命!”
“救过谁?”
“苏秦!”
子启长吸一口气。
“她还生活在一个人的身边不下十年!”
“不会又是苏秦吧?”
“让公子料中了。”
“那……她是不是与苏秦……那个……”子启顿住,目光征询。
“苏秦是她义父!”车卫秦一口否决。
子启又吸一口长气。
“让此女做香楼的招牌,公子以为如何?”
“不可!”子启急道。
“哦?”
“这是个奇女,本公子收了!”
车卫秦鼓掌。
接后数日,子启让出一栋位于郢都核心区的奢华客馆,被车卫秦作价入股。前后不过旬日,此楼就被车卫秦使人装饰一新,门首大匾上,“品香楼”三个用脂粉涂色的大字赫然夺目。
华都丽日,艳阳高照。
一堆爆竹响过,鼓乐声中,以天香为首的众香粉黛登场,品香楼正式开张。楼里楼外,结灯结彩,管弦乐中,佳丽竞技。远在门外三十步处,就可嗅到一股又一股扑鼻而至的西域异香,窥见到各色各样的俏脸隐现,玉体弄姿。
在子启等公子的高调宣扬下,不消数日,满郢都的富家公子、达官贵人大多晓得此楼了,离楼百多步的拴马场也渐次闹猛起来。
接到子启的紧急指令,昭鼠不敢怠慢,将他的宝贝陶壶小心翼翼地做了防震包装,昼夜兼程,一路颠簸地赶到郢都,未进家门,直接入见。
子启审过陶壶,赞扬几句,指壶道:“昭大人,这只老壶本公子借用几日,你甭心疼哟!”
“这……”昭鼠怔了。
“是王叔要借!”子启笑道,“本公子才不稀罕你的这个破壶呢!”
昭鼠两手抱头,良久,抬头:“敢问鄂君,王叔欲借几日?”
“咦?”子启眼睛睁圆,“王叔借几日,你问我,我哪能晓得哩?这破壶真要是让王叔看上了,该是它的福气才是!即使你白送给我,拿它撒尿我还嫌难看哩!”
昭鼠吧咂一下嘴唇,缓缓站起,拱手:“公子若是无事,下官这就回家了!赶路太急,有点儿不舒服呢。”
喜欢鬼谷子的局请大家收藏:(321553.xyz)鬼谷子的局艾草文学阅读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