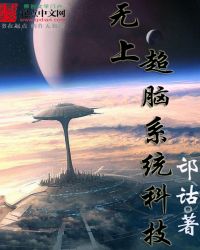王叔用牛车载了我们四五天,目的地却始终遥遥无期。
“我们要去哪啊,师父……”我坐在颠簸的牛车上,抹了一把汗水。
我曾问过他,既然他是道士,为什么那些人却叫他白先生,而不是直接叫白道士。
他笑了笑,这样说道:这个年代了,谁还信什么道士不道士,一听就跟神棍似的。
白先生这几天下来,也不似第一眼看见他那般仙风道骨了。
纯白的袍子沾染了不少泥渍,多了几分烟火味,他抬眼看去,“不远了,前面就是云水了,小丫头,再忍一忍!”
我口干舌燥,点了点头,“嗯,我相信师父……”
其实我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也不怕白先生把我卖了,反正现在我孤苦伶仃一个人。
白先生果然没有骗我,又过了个把小时,牛车终于进了省城,这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我做梦也没见过。
进城之后,白先生带我来到一个在二楼的简陋出租屋。
房子不大,摆设的也简单,应该是师父以前自己住的地方。
“小小,你自己去看一下,想要哪间做卧室。”白师父把随身的行囊放下,示意我选房间。
客厅左右分别是一间小卧室,推门进去,也不过一张单人床和写字桌。
“不用选,师父想住哪间就住哪间,剩下的给我就好了!”我表示受宠若惊,即使是这么简单的房间,对我而言也是很奢侈的。
白先生转身,“那你就来这间吧,我记得前不久买过个收音机……我经常会不在家,你要照顾好自己。”
果然,另一间的角落摆着一个红壳子的收音机,白先生让我在这间住下了。
我喜滋滋地坐在床上,欣赏着自己的小窝。
我突然想起什么,掏出口袋里的蓝色香包,白先生给我的,用来收纳外婆的头发。
我捧着香包,自言自语道:“外婆,你看,现在我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咧。可惜你和妈妈没住过……”
我抱着香包,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以后得几天,果然如白先生所说,白天他是连人影都看不见的。
有时候我忍不住问他,到底去干什么了,他只是笑而不语。
有时候他不回家,我一个人很害怕,早早地捂进被子里。
可是,被子也挡不住那阵痛苦的呻吟声传来,萦绕在我耳边久久不散。
那声音很凄惨,一阵高过一阵……我那时候还不懂那是什么声音,所以觉得怪吓人的。
听声音的方向,似乎就是那个在我们出租屋前面的发廊传来的。
我害怕的同时又很好奇,可是白先生让我晚上不要出门,我非常听他的话。
我瑟瑟发抖地趴在被子里,慢慢睡过去了。
模模糊糊中,我感到有一双冰凉的手攀上我的脖子,朝我耳朵吹着冷气,又凉又痒。
我不适地扭了扭身子,却被那双手按住,“别动,你迟早要成为我的夫人。”
虽然在一片黑暗中看不见这个人的脸,但这道声音对我来说就太熟悉了,我小声又害怕地问:“凌清……是你吗?”
“你猜呢,嗯?”他的尾音微微上扬,带着魅惑和迷醉。
冰凉的唇瓣落在我的脖子上,轻轻地掠过,小心翼翼烙下一个又一个的印记。
“不要、别这样……”我感觉身体内像有火山要喷发一样,很热,很难受。
“你不喜欢吗?”他咬着我的耳朵,低沉的嗓音循环在我耳际,冰凉的指尖却沿着我的脖子慢慢下滑。
冰凉的嘴唇轻轻地与我的唇瓣印在了一起,我忘了该怎么呼吸,慌乱极了…… 尸夫有约